基本介紹
- 本名:王仲聞
- 字號:字行
- 出生時間:1901
- 去世時間:1969
人物生平,主要著作,社會評價,
人物生平
長相酷似靜安先生,已故的沈玉成先生首次見到他時,曾取《觀堂集林》中那張相片來印證,非常傳神地說“子之於父,如明翻宋本,唐臨晉帖”。令人感慨的是,時不過三十年,我們現在卻只能從靜安先生的遺像來緬想幼安先生的模樣了。
王先生幼承家學,但中學畢業即入郵局工作。解放初期供職於北京地安門郵局。1957年因參與創辦同人刊物《藝文志》而成為右派,遭開除。後經由徐調孚先生推薦,被愛才若渴的中華書局金燦然總經理請到中華,成為一位不在編的臨時編輯,一直工作到寫下那封給文學組之信的那個時候。
王先生精熟唐宋文獻,以“宋人”自詡。尤長於詞學,其著述除前已述及的三書外,還有《渚山堂詞話·詞品》點校(署名王幼安)、《詩人玉屑》點校。他用力最勤、真正代表他學術水平的還有兩部書稿:一是《唐五代詞》,文革中遺失,其前言後記倖存於檔案中,經程毅中先生整理,已經發表。二是《讀詞識小》,約20萬言。錢鐘書先生曾受中華書局之請看過全稿,稱“這是一部奇書,一定要快出版”。但就在中華決定出版並已完成了審讀加工的時候,因為與《全宋詞》署名同樣的原因而暫停付印。文革中遺失。現在我們從《全宋詞》的審讀加工記錄中,可以約略看到《讀詞識小》的影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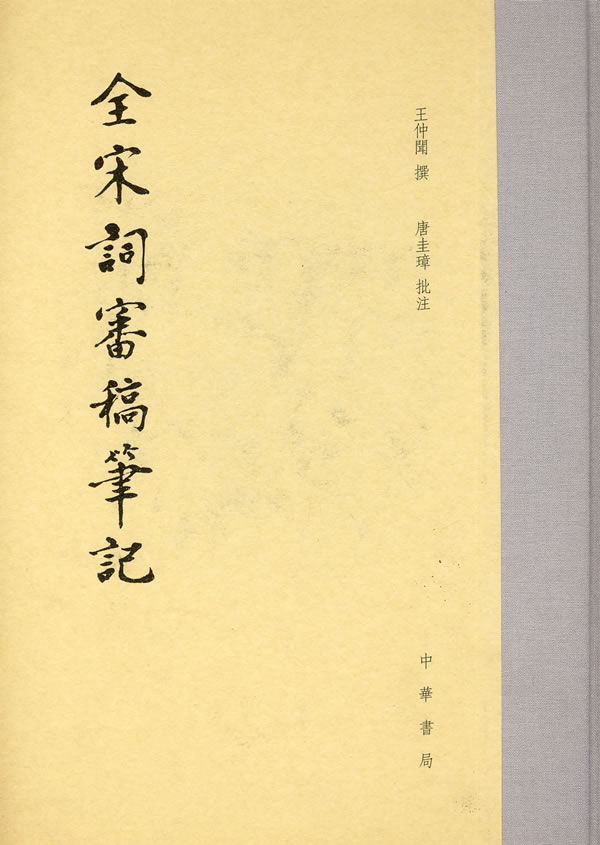 全宋詞審稿筆記
全宋詞審稿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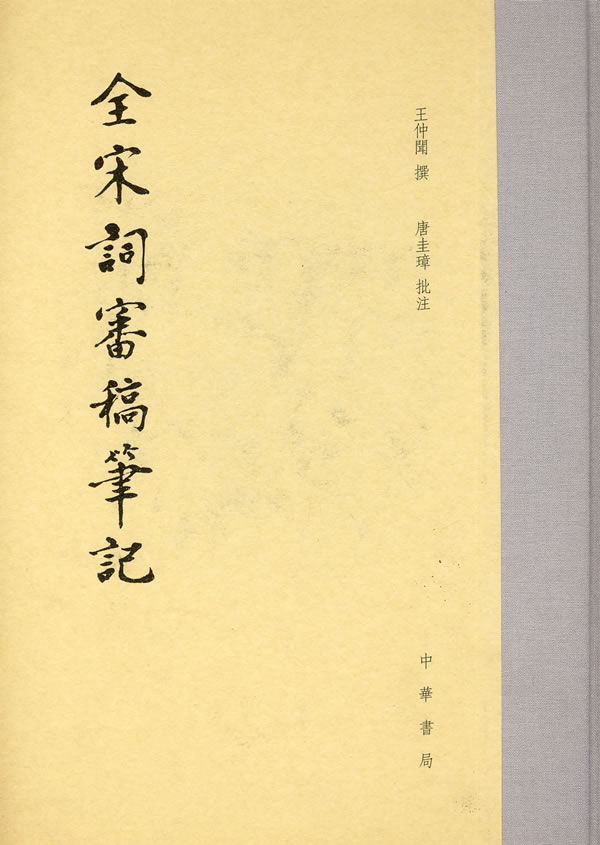 全宋詞審稿筆記
全宋詞審稿筆記一九〇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 一歲
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 四歲
三月,弟貞明生。
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 五歲
祖父王廼譽去世。
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 六歲
七月,母親莫氏因產褥熱過世。
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 七歲
氏所出。 《全宋詞》王仲聞校訂
《全宋詞》王仲聞校訂
 《全宋詞》王仲聞校訂
《全宋詞》王仲聞校訂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 十歲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 十二歲
十二月,妹東明生。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 十四歲
三月,隨繼母返回海寧,就讀海寧第一國小。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 十五歲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 十八歲
五月,北京發生五四運動,波及全國。任育才公學學生會副會長,被校方開除,此後被推舉為全國學生聯合會出版社代表。在離校學生會所開辦的免費學校中任髙級班國文教員。十一月九日父親王國維致羅振玉函謂“次兒等學校事,因值孔子誕辰,學生要求放假一日,午後遂不往,因之斥退四人。表面如此,實際因夏間之學生會次兒因資格被舉為副會長,此次開除殆因此故”。
十月,應考郵局郵務員,未取。
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 十九歲
三月,入上海郵局為郵務生。長妹東明後來追述:‘我們這一代中,二哥天賦最髙,也最愛古籍與詩詞,如以他的資質與興趣,能追隨父親繼續鑽研國學,日久必有成就。而父親無視他的愛好與秉賦,竟讓他進入郵局,以獲得較佳的獨立生活工作,當是以自己親身經歷到的寶貴經驗為鑑’(《先嚴王公國維為子女所鋪的路》)。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 二十歲
年初通過甄試,升等為郵務員。
十一月四日父親王國維致長兄潛明函:“(髙明姻事)本擬明年下半年,而聞陳宅姑娘又入海寧學堂,恐沾染習氣,故汝母意欲於上半年辦喜事。”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 二十一歲
與陳慎初結婚。子女成年者三男(慶新、慶同、慶山),二女(令年、令三)。
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 二十二歲
五月,王國維入京任清遜室南書房行走。
八月繼母、弟妹等入京。
是年自吳興里遷住新閘路甄慶里。
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 二十五歲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 二十六歲
七月,與諸弟同具名編次《王忠愨公哀輓録》,天津羅氏貽安堂彙刊。
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 二十七歲
是年在《郵聲》雜誌發表詩作《己丑除夕贈家兄》、《丁卯展前詩愴然有作即用舊韻》。此後若干年仍有詩詞在《郵聲》刊出。
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 三十歲
調入上海郵政總局。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 三十一歲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 三十二歲
是年林大椿輯《唐五代詞》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 三十六歲
一九四〇年(民國二十九年) 三十九歲
七月,參加為期二周的郵政秘密監察人員培訓班,為解放後“歷史問題”所從來。
唐圭璋《全宋詞》三百卷,成稿於一九三七年,是年由國立編譯館出版。其“緣起”有“王仲聞等辨訛”致謝語。唐圭璋先生在《自傳及著作簡述》中回憶:‘“初編此書的時候,就承精於目録版本之學的王仲聞幫助蒐集資料,校訂真偽,商討善本、足本問題。”
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 四十歲
升任副郵務長。
一九四二年(民國三十一年) 四十一歲
郵政總局遷往重慶,住南岸南桷埡。
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 四十四歲
冬,隨郵政總局還都南京,住建業村。
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 四十六歲
是年在《現代郵政》雜誌發表《尹師魯水調歌頭》、《劉仲方六州歌頭》、《李後主佚詞》等多篇《讀詞雜記》。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 四十八歲
一九五〇年 四十九歲
是年鎮反運動中,其有關部門結論竟為“曾經受過特務訓練,態度不老實,撤職登記”。
一九五一年 五十歲
在郵政部幹部審查活動中被定為“特務嫌疑”,從事豎電線桿等懲罰性體力勞動。
一九五三年 五十二歲
屢次對人民出版社出版物提出書面意見,受到關注,該社王子野、范用擬將其調入任職未果。
在《中國語文》第八期發表《統一譯名的迫切需要》。
一九五五年 五十四歲
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於是年初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夏承燾為是書所撰‘承教録’謂‘此書問世一年,屢荷四方讀者惠書督誨。惠州張鳳子先生,北京王仲聞先生,皆未嘗奉手請益,乃承費日力為細校再過,各舉謬誤多處,盛意尤可感激’。
是年郵局肅反運動小組審查結論“不是反革命分子”。
一九五六年 五十五歲
七月二十二日,在《光明日報》發表《關於李煜詞的考證問題》。
十二月十九日,夏承燾復接得王函,謂‘“著有《南唐二主詞校訂》、《陽春集校訂》,又有《唐五代詞校輯》,收敦煌曲子、《樂府詩集》之近代曲辭及易靜《兵要望江南》等,需兩年完稿。又欲輯一詞抄,收《全芳備祖》、《壽親養老新書》、《通用啟札截江綱》、《翰墨大全》、《永樂大典》以及宋元方誌譜錄中之辭彙為一書。又有《宋元詞話抄》,積稿盈尺,無精力完成”。
一九五七年 五十六歲
三月九日,夏承燾入京開會,與相見,謂之“樸質篤厚,想見靜安先生”。
四月三日,《讀唐宋詞論叢》、《論〈尊前集〉之選輯時代》二文寄達夏承燾,定《尊前集》當編於北宋,不能早於仁宗,晚於神宗。夏次日日記謂‘“君治學細心踏實,自愧不如”。同月夏承燾《唐宋詞論叢》之《承教録》中述及,計舉正二十事。是月,標點本《唐才子傳》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六月,《南唐二主詞校訂》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以明萬曆庚申呂遠墨華齋本為主,參考王國維《南唐二主詞校勘記》,李璟、李煜詞作歷來真贗雜陳,文字多訛,是書據所見各本互校,並以各種選本、筆記、詩話、詞話及互見各詞之總集、別集參校,“綜合舊說,間參新見”。
是年欲調往蘭州大學,夏承燾又推薦入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皆未果。又擬辦同人刊物《藝文志》。在“反右”運動中,受到不公正的處理,被追究“歷史反革命”問題,口頭通知:是右派但不宣布;不交地方監督,強制退職。在南海艇隊工作的次子王慶同、在武漢測繪學院就讀的三子王慶山,均被劃為“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 五十七歲
三月,《詩人玉屑》點校本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五月,寄夏承燾《李易安集》目。
十二月十三日,有函致夏承燾,謂《李清照集》尚未脫稿,《全宋詞》中間題不少。
是年清華大學因校內基建,通知將王國維墓遷出。
一九五九年 五十八歲
四月十一日,夏承燾入京,往訪,告知所輯《唐五代詞》將由中華書局出版。
六月,唐圭璋完成《全宋詞》初步修訂,交稿中華書局。並建議由王仲聞任責任編輯。此後‘六載辛勤,全力以赴’(唐圭璋先生語)。是年受中華書局邀為《全唐詩》斷句和審稿,得酬金180元。
是年起至一九六一年冬每月寫思想匯報交中華書局和派出所。
一九六〇年 五十九歲
是年由不定期前來書局改為全日上班。繼續修訂《全宋詞》,自二百○四卷本《翰墨全書》書輯出佚詞三百十五首。
一九六一年 六十歲
六月三日,夏承燾日記載來函,謂近為《全宋詞》補詞一千六百首,改正補充小傳三四百人,舉出錯誤不下三四千處,今年尚不能出書。
十月,《讀杜心解》標點本由中華書局出版,為主要整理者。
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於是年出版,屢引其說。
一九六二年 六十一歲
上年《李清照集校注》完稿,輯詞、詩、文為三卷,附録《李清照事跡編年》暨《李清照著作考》。元旦撰成《後記》,致謝學人包括夏承燾、黃盛璋、鄧之誠。
一九六三年 六十二歲
四月,《李清照事跡作品雜考》刊載於《文史》第二輯。
一九六四年 六十三歲
五月,《全宋詞》新版基本完成修訂,以中華書局編輯部名義撰寫《出版說明》。前言由唐圭璋、王仲聞同撰。
是年《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杜甫卷》由中華書局出版,署“華文軒”名。
是年《李清照集校注》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排成紙型,但未能出版。
是年,羅繼祖入京參加校點二十四史,與相過從。羅氏《海甯王氏後人“文革”後所遭遇》記》稱:“我識高明丈即於一九六四年在北京翠微路參與中華書局校點廿四史時。丈對詞學造詣精深,局中正重校唐圭璋《全宋詞》,經丈核訂,舉證若干,讀者嘆服。公退接談,公私並進,覺與乃翁風範不遠。為言先兄不祿,嫂氏尚在盛年,宜再嫁。其說甚是”。
一九六五年 六十四歲
六月,新版《全宋詞》出版。全書録入詞人一千三百三十餘家,詞作一萬九千九百餘首,另有殘篇五百三十餘首。凡三百七十餘萬字,引用書目多達五百四十二種。
一九六六年 六十五歲
九月二十三日,中華書局在文化大革命受到直接衝擊,被清退。二十五日致函文學組,交代未盡事宜。時《唐五代詞新編》已基本成稿,在運動中遺失。
一九六七年 六十七歲
家居。仍廢寢忘食,專意從事著述。
一九六九年 六十八歲
一月十九日提交的交代材料稱“我在中華書局工作時,曾準備寫若干稿子,有的已寫了一部分,有的已接近完成。自領導通知我以後我寫的東西不能再出版以後,我已以一部分捐獻國家,已蒙接受。將來這類東西不知有用沒用。我準備寫完它,決不因我的東西不能出版就撒手不幹了”、“已寫好部分約有一百餘萬字”。
是年冬,因“朱(學范)、谷(春藩)特務集團”案牽連,被特偵組隔離審查。
十一月十二日,服毒自殺。子女均在外地,身後文稿、圖書散失殆盡。後來發還者僅舊版王國維集一部。
一九七〇年
二月,夫人陳慎初於海寧鄉間去世,終年七十一歲。
一九七九年
三月,郵政部平反“朱(學范)、谷(春藩)特務集團”案。
十月,《李清照集校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學者稱“博大精深”、“古籍整理之典範”。唐圭璋在得知出版訊息後,通過出版社聯繫到王氏後人,以申弔慰。
一九八○年
一月二十二日,叔父王國華在台灣去世。
六月二十五日,趙萬里在北京去世。
一九八一年
九月,《夷堅志》校點本由中華書局出版。生前曾任此書編輯,並自《永樂大典》中輯出軼文。
是年,《文學遺產》第一期刊載岳國鈞《玉中之瑕——談〈李清照集校注〉的注釋》。
一九八六年
五月,前中華書局同事沈玉成作《自稱“宋朝人”的王仲聞先生》。收入中華書局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回憶中華書局—1912-1987》。
五月十一日,夏承燾在北京逝世。
一九八七年
二月二十日,《唐五代詞新編前言》刊載於《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第一七一期。編者按稱‘“中可以看出他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嚴謹的態度、嚴密的方法,對我們研究唐五代詞以及整理古籍工作都不無借鑑意議”。《前言》為生前未成著述《唐五代詞新編》僅存部分,由程毅中在中華書局檔案中發現。
曾參與編輯的《元詩選》初集、二集、三集分別於是年1月、7月、10月出版。
一九八八年
遺稿《長短句詞盛行之時代辨析》刊載於《文學遺產》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此文原為《唐五代詞新編後記》的部分未完稿,程毅中在中華書局檔案中發現。
一九九○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唐圭璋於南京去世,終年九十歲。
一九九九年
一月,中華書局《全宋詞》簡體字版補署“王仲聞參訂”。
四月,中華書局徐俊撰文《王仲聞——一位不應被遺忘的學者》,刊載於《書品》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二〇〇二年
二〇〇九年
九月,《全宋詞審稿筆記》由中華書局雙色影印出版,署王仲聞撰、唐圭璋批註,計五十萬字。劉尚榮先生以中華書局編輯部名義所撰前言,對二位學者的治學和合作均予髙度評價。
主要著作
王仲聞,王國維先生次子。名高明,以字行,曾用筆名王學初、王幼安。早年中學肄業後即遵父命入郵局,先後在上海、南京、重慶、北京工作,積年累遷為副處長。斯時自述稱“服膺孔子學說”,專長為“舊文學中之詞學”、業餘愛好“研究詞章,瀏覽各種有關古書”,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前,無學術著作發表,曾輯《宋詞長編》,未刊。
五十年代初將所藏王國維遺稿、書札捐送北京圖書館。
一九五九年進入中華書局為“臨時編輯”,先後參與《全唐詩》、《全宋文》、《元詩選》的編輯工作,有《南唐二主詞校訂》、《李清照集校注》《全宋詞審稿筆記》等著述行世,在並世同人中以博聞強識稱,於唐宋文獻尤有篤好深詣。一九六九年文革中受迫害棄世,遺稿、藏書等多已散失。
茲據本人檔案、學術著作、中華書局審稿紀録、友朋回憶文章等材料撰作生平著述簡表,以為世人了解其行實、治學、交遊之助。譜中時日俱依公曆,所記年歲按虛歲計。所涉人名,為省篇幅,均不加尊稱。右圖的《南唐二主詞校訂》,系南唐中主李璟、後主李煜撰;原書約成書於南宋,後世續有輯補,但均真偽雜陳,文字異同甚多。有鑒於此,王仲聞先生以明萬曆庚申呂遠墨華齋本為主,參考王國維《南唐二主詞校勘記》,搜羅各種版本及選本、筆記、詞話等以訂之;並將原書未收詞作的校勘辨偽、散見各書的二主詞評語和本事、各家序跋及有關考證資料等附編於後,成《南唐二主詞校訂》一書,於一九五七年六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此書之出版,可謂王仲聞先生就是南唐二主和後世研習南唐二主詞者及其他詩詞愛好者的絕大功臣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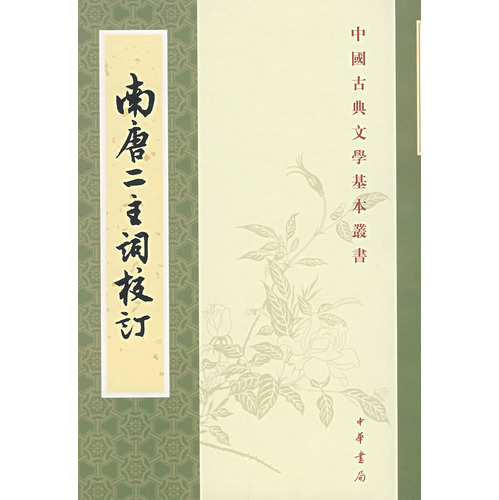 南唐二主詞校訂
南唐二主詞校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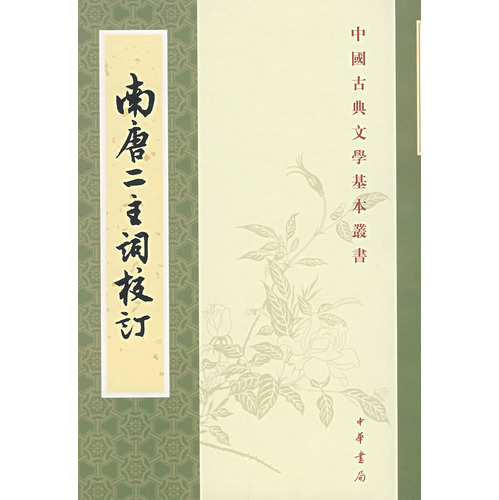 南唐二主詞校訂
南唐二主詞校訂社會評價
王仲聞:一位不應被忘卻的學者
徐 俊
予生也晚,王仲聞先生在我現在服務的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上班的時候,我還是個未開蒙的孩童。到了上大學,讀中文系,同學少年,於古代作品最鐘情於詞,“豪放”不論,單說“婉約”,無過於南唐後主李煜和易安居士李清照了。但那個時候讀書只知尋章摘句,手捧《南唐二主詞》與《李清照集》,哪裡懂得它校訂的精審、註解的翔實,更不理會兩書的整理者王仲聞為何許人了。
到中華書局工作後,先知道周振甫、楊伯峻先生這些熟悉的名字竟都是中華的同事,慢慢地又知道了一些故去的人,其中就有文革前擔任文學組組長的徐調孚先生和在文學組工作過的王仲聞先生。同事中的前輩經常地說起他們,比如關於王先生,中華版《全唐詩》點校本卷首的點校說明,寫於1959年4月,署名“王全”,前輩們告訴我們,“王全”者,王仲聞、傅璇琮二位先生也(浙江話“璇”、“全”音近,徐調孚先生代擬的署名)。中華版《全唐詩》是清編《全唐詩》的第一個整理本,王仲聞先生負責全稿的審訂,做了大量的工作。現在一些不法出版者將中華版改換標點版式,卻聲稱所據為揚州詩局本,實不知二者之間的區別在在皆是也。中華版文學類圖書中,不少部帙和難度都很大的書都經過王仲聞先生的加工,甚至由他直接承擔整理,如《元詩選》、《古典文學資料彙編》各卷,特別是王先生傾注了兩年時間全部精力參與修訂的《全宋詞》。
“文革”伊始,1966年9月25日,王仲聞先生在當面交代完所承擔工作後的第三天,又給文學組寫了下面這封信:
文學組:
前日依照電話來局並照你們提出的辦法,將經辦東西交代。覺得當時手續過於簡單。如文化大革命運動結束後,萬一其中有一種仍可考慮出版,則新接手之人不明經過,工作不免要麻煩一些。我想將各種稿件情況說明一下,請不要嫌我囉嗦:
(1)夷堅志:斷句已全部覆核改正。未辦完者,為補遺。補遺僅就《永樂大典》補了若干則。宋人書中還有,能憶及者有《方輿勝覽》、《景定建康志》、《鹹淳臨安志》等等,此外還有《異聞雜錄》、《清波雜誌》。以上僅僅是我平時讀書所知道的,不能完備。
(2)元詩選:大約已覆核了初、二兩集。有些有疑問(文字),未曾查各家集子;有些墨釘可以補,也沒有查。
(3)陸游集:原擬考慮作注,尚未決定,也沒有動手。
(5)唐五代詞:原來在編引用書目,沒有完成。目錄也沒有確定。內容取捨,我想從嚴,把一些偽作以及後人依託之神仙詞,或雖是詞而不能算作文學作品者,一律不收。今年學習緊張,沒有能夠提出來在組內討論。原稿還需要加工(主要是覆核作品之出處,原稿有錯誤),最好以《唐音統簽》參考,出自《全唐詩》者可以改為《唐音統簽》。原來我私人編了一張《唐五代詞人年表》,記得放在稿內供詞人小傳參考(生年卒年登第年大都可憑此表,不必另行搜羅),前日沒有見到。我手邊並沒有。小傳還沒有全部註明來源。
我還有一些自己的廢稿,一部分是《兵要望江南》里的詞,沒有抄過。因為想整個不收。現在也寄給你們。如其沒有什麼用處,將來退還我好了。
致
敬禮
王仲聞 66.9.25
在信封的背面,王先生工整地抄錄了毛主席語錄四行:“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現在讀這封信的感覺不免有些悲涼,“文革”沒有像王先生期望的那樣很快結束,而王先生卻在1969年離開了這個世界。
現在王先生信中提到的書稿有的已經出版,除了《唐五代詞》稿於文革後期遺失。但在中華書局的出版物上,沒有王仲聞的名字。他生前出版的《南唐二主詞校訂》和校注《蕙風詞話·人間詞話》(署名王幼安,與徐調孚合作),出版者都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李清照集校注》,1964年已經打好紙型,到1979年才由人文社正式出版(署名王學初)。王仲聞的名字已漸漸不為人所知。最近,中華書局出版了《全宋詞》的增訂簡體本,在該書的作者欄里鄭重地補上了“王仲聞參訂”的署名。
即使是專門研究詞學的人,對《全宋詞》四十年代的初印本和六十年代的修訂本之間的差異,也不會關注了。但要說及本世紀詞學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全宋詞》的修訂出版實為繞不開的大事,其本身的價值和對此後詞學研究的意義,同類書中有哪一本可以相比呢!
前後兩版的《全宋詞》可以說判若二書,當然其中唐圭璋先生作為編者貢獻最大,這也是唐先生詞學生涯中最重要的成果。另外從中華書局的書稿檔案中我們也不難看到王仲聞先生在修訂過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王先生的參與,《全宋詞》難臻如此完美之境。這裡從王、唐二先生往返商榷的原始記錄中隨手摘出兩則,以見一斑。以下是王先生的話:
《至元嘉禾志》卷三十一有吳潛《效東坡作醉翁操》一首,前有序云:“予甥法真禪師以子瞻內相所作《醉翁操》見寄,予以為未工也,倚其聲作之,寫呈法師,知可意否。謝山醉吟先生書。”此謝山醉吟先生,不知何人,不似吳潛自號。按陸放翁《入蜀記》卷一言本覺寺(為抵秀州上一日午後泊本覺寺,殆在嘉禾境內)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未工,故賦之。”元祐中人稱東坡為內相,南宋人無以此稱東坡者。(內相乃翰林學士之別稱,與內翰同,始於唐。)疑此詞乃郭功甫所作,非吳潛作。故彊村曾據《至元嘉禾志》錄履齋佚詞,而不及此首。謝山醉吟先生之稱,不見於《自號錄》,疑是功甫自號。
最後王先生問:“如先生同意此說,當補作郭功甫詞。”唐先生答云:“同意補作郭功甫詞。原來我看序與標題不合,曾懷疑過,但不能知何人之誤。”這是王先生在輯補佚詞、鑑別作者方面所做工作的例子。再看一則關於宋代另一位女詞人朱淑真的時代編次的例子:
朱淑真不知為何時人。《全宋詞》原編在卷151,在李石之後、劉學箕之前,似有問題。朱之時代至少在淳熙以前(其時朱早已死,此據魏端禮《斷腸詩集序》),而劉學箕則為慶元間人(有己未年所作詞,即慶元五年所作)。
唐先生答云:“知在淳熙以前,當據此提前。”關於朱淑真的時代,後來王先生續有所得,在另一則記錄中王先生說:
朱淑真為何時人,迄無有人考定。蕙風據詩集中“魏夫人”,定為曾布同時人,也不一定可恃,以曾布妻魏夫人以外,或另有其他魏夫人也。惟魏端禮編其遺集《斷腸集》乃在淳熙年間,可為朱卒於淳熙以前之鐵證。茲查《樂府雅詞》卷首“九重傳出”之集句《調笑》,內有“黃昏更下瀟瀟雨”句,殆即朱《蝶戀花》中“黃昏卻下瀟瀟雨”句。是朱雖未必與曾布同時,其為北宋人,殆無可疑。茲據編於北宋崇觀年後、宣政年前,雖無確據,或無大謬。
近幾年學術界對朱淑真的研究成果多了起來,其詩詞集也已有多種整理出版。關於她生活時代的考證雖有所深入,但南宋說、北宋說,仍然未成定說。我曾粗略地看過各家的舉證,竟沒有提到《樂府雅詞》集句《調笑》的,而這恰恰是《全宋詞》編次的依據。
像上面這樣的加工記錄,保存下來的約在千條左右,近十萬言。王先生將審讀加工中發現的問題逐一條列,寄請唐先生閱復,大凡全書體例、編次、詞人小傳、詞集版本、存佚互見、輯佚補缺等等,有關《全宋詞》的方方面面,無不涉及。徵引浩博翔實,態度謙虛審慎,讓我們這些後來者嘆服之外,唯有愧汗。在我們的作者之中,已很少見到如此精熟文獻的人;在我們的同行和同事中,又哪裡還有這樣為一本書的審讀投入如此多的學識、智慧和精力的人呢!《全宋詞》修訂出版前,中華書局與唐圭璋先生以及當時的南京師院黨委商定,採用“唐圭璋編,王仲聞訂補”的署名方式,唐先生欣然同意。但時不多久,“文武之道”弛而復張,文化部下達了某項條例,規定若干種人的名字不得見諸社會主義的出版物中。這樣,一位學者一生的積累和兩年的辛勤勞動,就如此這般地被一筆抹淨。在至今已經重印七次六萬餘冊的《全宋詞》中,一直沒有“王仲聞”三字的蹤影。這次簡體本的署名,可以說是還了歷史一個真實。
在前面這些傳之口耳、錄自檔案的文字之後,往下似應將一般個人履歷中不該遺漏的姓名字號生卒年裡作點歸納,好為現代學人“錄鬼簿”提供點素材。
王仲聞(1901-1969),名高明,以字行。筆名王學初、王幼安,據說都是為不得已避用真名而所取之號;台灣曾大量翻印其書,改其名為王次聰。浙江海寧人,王國維次子。長相酷似靜安先生,已故沈玉成先生首次見到他時,曾取《觀堂集林》中那張相片來印證,非常傳神地說“子之於父,如明翻宋本,唐臨晉帖”。令人感慨的是,時不過三十年,我們現在卻只能從靜安先生的遺像來緬想幼安先生的模樣了。王先生幼承家學,但中學畢業即入郵局工作。解放初期供職於北京地安門郵局。1957年因參與創辦同人刊物《藝文志》而成為右派,遭開除。後經由徐調孚先生推薦,被愛才若渴的中華書局金燦然總經理請到中華,成為一位不在編的臨時編輯,一直工作到寫下前面那封給文學組信的那個時候。王先生精熟唐宋文獻,以“宋人”自詡。尤長於詞學,其著述除前已述及的三書外,還有《渚山堂詞話·詞品》點校(署名王幼安)、《詩人玉屑》點校。他用力最勤、真正代表他學術水平的還有兩部書稿:一是《唐五代詞》,文革中遺失,其前言後記倖存於檔案中,經程毅中先生整理,已經發表。二是《讀詞識小》,約20萬言。錢鐘書先生曾受中華書局之請看過全稿,稱“這是一部奇書,一定要快出版”。但就在中華決定出版並已完成了審讀加工的時候,因為與《全宋詞》署名同樣的原因而暫停付印。文革中遺失。現在我們從《全宋詞》的審讀加工記錄中,可以約略看到《讀詞識小》的影子。
最後我想藉此機會許一個私願,以作本文的結束。但願這份凝聚了王仲聞先生學識和勞動的珍貴的審讀加工記錄有機會整理出版,一方面《全宋詞》中不少的結論,其所以然者,均保留其中,對詞學研究自有其本身的價值;另一方面,像王仲聞先生這樣的學者、這樣的編輯,大而言之對學術的貢獻、小而言之對中華書局的遺澤,實在是值得後人緬懷和追慕的,誰說不是呢?
1999.3.2.六里橋
自稱“宋朝人”的王仲聞先生
沈玉成
1960年春,我在門頭溝山區下放勞動一年之後回到東總布胡同中華書局.在辦公室坐下沒有幾天,就聽有人在閒談,說今天王仲聞要來。我並不知道王仲聞是何許人,所以並不在意。坐在對面的傅璇琮兄看我茫無所知,特意提醒我說:“他是王國維的兒子,在這裡搞《全宋詞》。”我這才有點吃驚,打起精神要看看這位先生究竟是什麼樣子,以彌補一點沒有見過王靜安先生的遺憾。過不多久,來了。是個老頭兒,身穿人字呢夾大衣,手提一個書包,步子挺輕健。進門以後就正襟危坐在徐調老的桌子邊,談了一些我不甚瞭然的事,接著就拿起書包走了。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長得很象他父親。為了印證,我還特地跑到圖書館找出《觀堂集林》中那張相片看了一下,果然子之於父,如明翻宋本,唐臨晉帖,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我的好奇心。
當時他大約是一星期來一趟,交幾本《全宋詞》,又取走幾本。每次來去匆匆,加之聽說他是丁酉同榜,於是乎我就很有戒心,沒有和他交談過一句話,以避嫌疑。約摸來過十趟八趟,有一天他又來了,神情頗為頹喪,告訴調老說:“我不能做了。街道上要我丁鄉勞動去唉。”調老一聽也傻了眼,說:“你不要忙。今天先回去,等我找領導反映一下。”過了幾天,一上班,調老就召集全室人員,以一種有節制的高興宣布:“從今天起,王仲聞就要來上班了。這個人政治上有問題,不過學問是很好的。大家業務上有問題可以問他。”從此,王仲聞先生就成了中華書局的“長期臨時工”,每天上下班。
關於王仲聞先生之所以來中華以及他的“政治問題”,開頭頗為神秘,尤其對我和璇琮兄這樣的人來說,更屬於不應該知道的範圍。只是後來跟王先生熟了,聽他自己講一點,又從調老和趙元珠同志情緒高興的時候聽說一點,這才了解一個梗概。情況大致是,這位先生1901年生人,名高明,以字行。幼年很調皮,靜安先生認為這個兒子沒有什麼出息,就在他中學畢業以後送他進了號稱“鐵飯碗”的郵局。在郵局因為工作認真,被提拔到郵檢部門工作。這個部門向由中統控制,與反動政治的關係較為緊密,凡是幹這一行的都要進一個什麼訓練班。於是這位王先生就和“特務”兩個字沾上了很難說清楚的關係。解放後,他被留用,作為一個普通職員在地安門郵局賣郵票。然而錐處囊中,王仲聞先生的價值由於他的《人間詞話校釋》而開始被人認識。也由此,他就有點不安分了,心裡老惦著做學問,1957年居然要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幾位同志辦一個同人刊物《藝文志》。當時凡是牽涉“同人刊物”四個字的人,統統被疏而不漏的天網打盡,成為右派。郵局對王仲聞本來就極不順眼,碰上這一案,乾跪一腳踢開。被開除以後,斷了經濟收入,可是人是要吃飯的,就免不了作些奔走。不知道由於什麼關係,他的情況竟然被愛才若渴的齊燕銘同志知道了,並推薦給了另一位愛才若渴的金燦然同志,這才把他找來審核《全唐詩》的標點。時隔不久,唐圭璋先生修訂《全宋詞》的工作完成,稿子交到中華書局。唐先生和王先生是舊交,唐先生在來信中提出,有些資料在南京看不到,希望王先生幫他在北京查找一下,同時儘可能地覆核全稿。其時《全唐詩》已經完成,王先生接著就搞《全宋詞》。街道要他下鄉勞動,調老一著急,跑去找金燦然同志。燦然同志當即讓人事部門告訴街道,這個人是我們的臨時工,不能下鄉。為名正言順起見,王仲聞先生就來到中華書局上班了。
中華書局敢於使用王仲聞,使我對燕銘、燦然、調孚同志增加了一層敬佩。尤其是燦然同志有一句樸素的名言:“他有這個能力,我們為什麼不讓他乾?”這個“他” 是泛指,不僅對王先生一個人,也包括了像我這樣能力不大而還肯乾點事情的人。明知要擔風險,可是出於對事業的責任感、對學術的尊重和對人的理解,他就是要那么乾。燦然同志在“文革”中的一條大罪是“招降納叛,重用牛鬼蛇神”,為此被迫作了不知多少次的認罪檢查。不過我想他口頭上可以認罪,心裡卻一定是異常坦然的。
還有一個小插曲也值得一提。王先生被“開除公職”,究竟是根據什麼罪狀,戴的什麼“帽子”,他自己也稀里糊塗。不過他一直以“右派分子”自居,開會自報政治家門,發言還很踴躍,然而往往文不對題。到1962年,有關的同志把他叫去,告訴他;“你不是右派分子,以後不要說了。”他這才如夢方醒,回到辦公室,告訴別人說:“我原來不是右派分子唉。”我們在竊笑之餘,又不免有點辛酸,原來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可以近似於玩笑式地處理!至於和“特務”的關係,至今仍然是一本糊塗賬。不過我當時確曾想過,找這么一個不知世事、只會念書的人當特務,這就無怪乎國民黨要完蛋了。時至今日,證之以“右派分子”的滑稽劇,這頂“特務”帽子從何處飛來,也不難想見。不知怎么搞的,每當我後來回憶起這件事,總要和“文革”中把我一位號稱“老夫子”的學長打成“五·一六”聯繫起來,因為我堅決相信,“五·一六”這個組織如果確實存在,哪怕中國人都死絕了,它也不會去找這么一位把高郵王氏父子奉為偶像的迂拙學者。
話說回來,王仲聞先生端坐在辦公室里,開頭震於他是“名父之子”和怵於他的政治身分,大家都敬而遠之.不過硬安上去的“政治”常常經不起“人情”的銷融。逐漸,大家發現這個人對人並無戒心,更無架子,還喜歡用他的海寧官話說幾句不很可笑的笑話,因此就熟悉起來,並尊稱為“王先生”,包括調老、趙元珠同志也都這樣稱呼。
當時我們剛從大學畢業不久,自以為見過世面,加上少不更事,都或多或少有些狂妄。對王先生,起初也認為他不過從小受到靜安先生的啟蒙薰陶,基礎厚實,但長期在郵局,學術上的成就不能很高。但是沒有多久,王先生深厚到令人吃驚的學力就把我們完全“鎮”住了。可以不誇大地說,凡是有關唐、宋兩代的文學史料,尤其是宋詞、宋人筆記,只要向他提出問題,無不應答如響。一句宋詞,他能告訴你詞牌、作者;一個宋人筆記的書名,他能告訴你作者、卷數、版本。他不但熟於宋朝,而且喜愛宋朝近於入迷。我們和他開玩笑,說他是“宋朝人”,他毫不以為忤,反而非常自得,以後就經常自稱“宋朝人”。對唐詩也同樣熟悉,有一次李思敬兄蒐集了一些有關標點的材料,有一句“滴露研朱點《周易》”,出處遍找不得,拿去問他。他拿起筆來就寫出了這首唐人律詩的全文。這首詩的作者既非名人,詩中也無佳句,從來沒有人提過,當時我們面面相覷,感到真虧他怎么記得的。後來從東總布搬到翠微路,他因為回家路遠,常常睡在四樓集體宿舍里,我和他晚上總一起在辦公室看書。有一次他看我在背《北征》和《韓碑》,就說:“我年輕時候也背過,現在不知道記得不記得了。我們一人背一句試試看。”我心裡不服氣,要他背上句,我背下句。試驗的結果,他竟是一句不差。時隔二十餘年,我自己很少再接觸過老杜和李義山,兩首長篇古詩也忘得差不多了,可是王先生和我對背這兩首詩的情景卻仍歷歷如昨。
王先生對經部和史部也很熟悉,《尚書》和《周易》可以隨口背誦。《辛亥革命烈士詩文選》的注釋,是一位中年學者做的,由於一無依傍,難度比較大,但成果可以稱得上平妥精當。發稿前請王先生通讀一遍,還是被他找出好幾處不易發現的問題。現在記得的,“太白”,旂名,原注引《國策》,當引《逸周書》;“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原注引《後漢書·張綱傳》,當引《漢書·孫寶傳》。這顯然是全憑記憶,因為工具書上所引出處都作《國策》和《後漢書》。
王先生在中華書局所付出勞動最多的工作無疑是《全宋詞》的訂補。自從唐先生交稿以後,王先生就接手這一工作。唐先生以一人之力,在解放前極為困難的條件下,鉤沉索隱,編纂了這一部有宋一代的詞總集;解放後又以更高的要求和更嚴肅的態度重新編定。這種獻身於學術的精神,可以與前此的嚴可均和後此的逯欽立先生鼎足而三,《全宋詞》也將永遠成為古籍整理史上的一塊豐碑。然而知也無涯,而個人的力量有限,唐先生的嚴肅和虛心正是在主動約請王先生為之訂補而得到了更完美的體現。據我所知,在王先生訂補期間,這兩位學者之間的書函往來一直不斷,商量切磋,無非都是為了把這部書出得更好。王先生沒有辜負老友的囑託,傾其全部心力足足工作了四年,幾乎踏破了北京圖書館的門檻,舉凡有關的總集、別集、史籍、方誌、類書、筆記、道藏、佛典,幾乎一網打盡,只要翻一下卷首所列的引用書目,任何人都會理解到需要花費多少日以繼夜的辛勤。王先生的勞動,補充了唐先生所不及見到或無法見到的不少材料,並且以他山之石的精神,和唐先生共同修訂了原稿中的若干考據結論。應當實事求是地說,新版《全宋詞》較之舊版的優勝之處,是唐、王兩位先生共同努力的結果。“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學術工作需要這樣真正的合作和切磋。學無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到達真理的終點。以唐、王兩位先生的學力和功力,在新版《全宋詞》之後,不是又有孔凡禮先生從《詩淵》中輯補了若干首沒有收入的宋詞么?這裡還需要再一次提到唐先生的嚴肅和虛心。在新版《全宋詞》問世後,唐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在文章和談話中提到王先生的貢獻。“文革”以後,還幾次向中華書局詢問王先生身後家裡有無困難,願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老輩風範,高情厚誼,確實令後學如我輩十分感動。
關於《全宋詞》的署名也有過一段波折。原先約請王先生修訂加工,當然不會考慮署名方式,可是當修訂接近完成,王先生對提高質量所付出的勞動已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編輯加工所能相比,再加上當時的政治形勢屬於“文武之道,一張一弛”中相對地“弛”的階段。於是就有人提出王先生應當署名的意見。按照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原則,而且王仲聞又不是什麼“右派分子”,所以燦然同志和調老經過反覆考慮,以文學組的名義向唐先生和南師黨委提出採用“唐圭璋編,王仲聞訂補”的署名方式。唐先生以他一貫的虛心與寬厚欣然同意,聽說南師有的同志不以為然,但唐先生既已表態,也就不好再說什麼了。然而時不多久,“文武之道”又弛而復張,文化部特意為此制定了一個什麼條例,大約類似於後來的“公安六條”,明確規定有若干種人的名字不得見於我們社會主義出版物的作者欄內。這樣,一位學者幾十年的辛勤積累並在四年的艱苦勞動中所體現的成果,嗚呼,就一筆抹得乾乾淨淨。我願意借這個機會向中華書局諸執事提一個衷心的希望,王仲聞先生的署名當時既經商定,現在撥亂反正已近十年,以後如果重版《全宋詞》,應該恢復這歷史的真實。
最後還要提到一件無法彌補的憾事。王先生在訂補《全宋詞》的過程中,曾寫下了大量宋詞考據的筆記。調老這位內行的老編輯,曾一再非正式地鼓勵他整理出來。大約經過一年時間,王先生利用晚上的業餘時間,終於整理出了二十餘萬字的《讀詞識小》。內容全部是有關作家生平、作品真偽、作品歸屬、詞牌、版本的考訂,其謹嚴和精審,和以往任何一種高水平的詞學考訂專著相比都毫無遜色。當時調老指定我當責任編輯,我雖然無力承擔這個責任,但按規定總得有這么一個人,非此即彼。好在大家心裡默契,書是高質量的,總要出,不過在發稿單上籤個名而已。我向調老建議,技術工作我可以做,學術質量我審查不了,最好請高人審讀,哪怕只是估一下價。這個高人,最合適的是錢鐘書先生。於是調老請冀勤同志專門走訪了錢先生,錢先生在百忙中擠出時間,很快讀完了全稿,讓冀勤同志帶口信回來說: “這是一部奇書,一定要快出版。”錢先生的評價不僅使王先生非常高興,也使編輯部加快動作。我連稿子都沒有通讀,就拿起紅筆邊讀邊加工,滿以為一遍讀完,發稿工作也隨之完成。殊不知事出意外,他在筆記中除了申述自己的意見外,還對當代的學者頗多譏評,即超出一般正常的學術批評之外的不夠心平氣和的語言。我理解他不能自已的心情,滿腹文章而蹭蹬一世,眼見和他水平近似或與他相差甚遠的都享名於學術界,他這位真正的“實力派”卻依然在中華書局當一名“長期臨時工”,牢騷溢於筆端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然而,為學術界的團結計、為當時政治形勢下王先生本人的利害計、也為我這個責任編輯的責任計,我都應當勸王先生刪去這些話。在反覆的勸喻之後,王先生同意刪去,但向調老提出就請沈玉成執筆。大約調老考慮到由我來做可以更徹底一點,於是採取這一方式,不過其時已經到 1964年了。當我的加工工作完成,那個文化部條例業已下達。在《全宋詞》上署名尚且不可,焉能出版專著?王先生本人的心情自不必說,我們也同樣不好受。調老這位忠厚長者最後表示,稿子先放一放。意思很明白,想等風頭過去、張而復弛的時候再出。誰想得到,當時的風力還不過是比青萍之末稍稍強一點,兩年之後的大災難才是真正的颱風。
大約在1965年,王先生見出版無望,就以修改為名把稿子要了回去。這真是一個不可挽回的失著。如果稿子存在中華;“文革”雖亂,存稿、檔案卻僥倖全部未遭毀損。《讀詞識小》在1966年隨著王先生出了中華書局大門,王先生被迫害致死,此稿就杳無蹤影。“文革”後,中華書局曾不止一次向他的家屬詢問稿子的下落,卻遍覓不得,看來是已經盪為煙雲了。
這是詞學研究領域中無可彌補的損失。王先生有校注詞話、詞集行世,但《全宋詞》的修訂卻是其畢生學力和心血之所萃,而這部《讀詞識小》又是把他所經手的考訂過程奉獻於學術界。就我讀後的印象而言,我要憑良心說,其材料的豐富、見解的深刻、結論的精確,在在都無愧於第一流的著作,無怪乎錢先生這樣淵博的學者也要譽為“奇書”。聽說“文革”中不乏這樣的事,一位學者死了,遺稿不知下落,過些時候又赫然問世,不過署名卻是另一個人。我倒真希望這部《讀詞識小》當時為一個雅賊挾之而去,今後不管用什麼名義和形式發表,我都決不置一辭,因為讓它留在人間總比歸於天上要好。這種想法自然近於荒唐,不過卻是我的真實心情。
王先生生前的健康情況很好,如果他今天還在世,雖然已過八十高齡,還應當是能做而且會愉快地去做不少事情的。幾年前編纂《全宋詩》的倡議一經提出,我和毅中、璇琮二兄就一再想到王先生,慨嘆再也找不到這樣的學者了。中華書局因為我當時和王先生接近較多,所以要我寫一點回憶。對王先生的學識,後學如我不足以窺其堂奧,不過就我所知道的這一鱗半爪,如果還不寫出來,我會永遠引為內疚。一位名聲很大的學者去世,會有許多紀念文章,即使是只得過學者一封信的人也會謬托知己,去寫什麼某某先生對自己的教導之類。王仲聞先生一生落寞,謝世以後沒有見到任何形式的紀念,因此寫了這些話,聊當心祭,也許算不得是辭費的。
1986年5月於文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