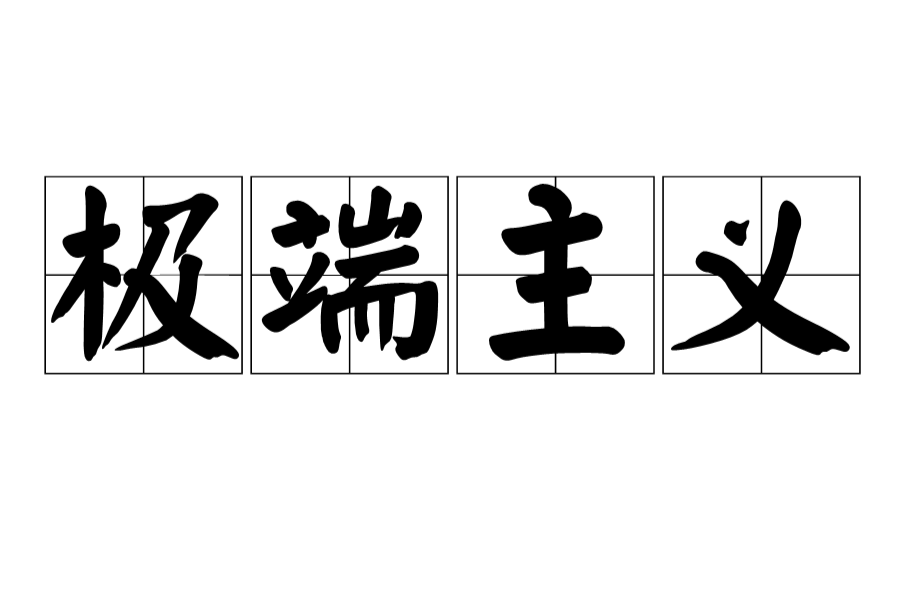綜述
極端主義(Extremism)的定義是:為了達到個人或者小部分人的某些目的,而不惜一切後果地採取極端的手段對公眾或政治領導集團進行威脅。極端主義的定義是指人們往往片面的而非全面的看待事物或行為,同時往往在處理事物時會通過偏激的方式來解決。
特點
極端主義者的特點:他們在做某件事情時,雖然明知道可能他們目前選擇的
解決問題的方法或方式不是最合適的解決問題方法或方式,但他們寧願就按已經選擇的方法或方式來解決問題也不願意多花些時間來想想有沒有更好解決問題的方法或方式。他們性格上嚴重偏執,對於他人的意見往往也不管好壞一律不聽,一旦出現不盡如人意的後果則要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所以,人類社會想要長久健康發展就必須杜絕極端主義,這也將是個全人類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勢力
所謂“三股勢力”,準確一點說,就是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國際恐怖勢力。“三股勢力”各自的表現形式雖有所不同,但本質並無根本不同。因此,他們從一開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沆瀣一氣,同流合污。他們以宗教極端面目出現,以“民族獨立”為幌子,一方面製造輿論,蠱惑人心,一方面大搞暴力恐怖活動,破壞社會安定。他們的根本目的就是製造混亂,在亂中推翻中亞各國的世俗政權,按照他們的“純粹教義”建立“純粹伊斯蘭政權”。
“
三股勢力”在中亞的出現絕非偶然,而是這一地區特定歷史、地域和人文條件的產物。在中亞居住著一百多個民族,這諸多民族、宗教、文化因素長期在這裡相互交匯與融合,又彼此撞擊與衝突。上個世紀,在直到一九九一年前蘇聯解體的七十年中,這裡一直包括在前蘇聯的版圖內,按主體民族的聚居情況劃分為
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烏茲別克斯坦、
土庫曼斯坦等五個加盟共和國。前蘇聯解體之後,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原有的主導思想體系和組織體系迅即瓦解。一時間,中亞地區出現一個巨大的“思想文化真空”。
中亞五國的主體民族都信奉
伊斯蘭教,而同五國相鄰的
中東地區又是世界伊斯蘭勢力最集中的地帶。獨立之初的中亞各國政府在一時惶惑之中,都不約而同地想利用伊斯蘭教來填補
前蘇聯解體留下的“思想文化真空”。包括一些國家元首在內的政府高官,帶頭到清真寺祈禱或赴
麥加朝覲。這為伊斯蘭勢力在中亞的復興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於是,伊斯蘭教宗教團體、清真寺數量和信教人數急劇增長。到一九九七年,哈薩克斯坦的宗教團體由獨立前的二十多個增加到一千一百八十個,清真寺由六十三座增加到四千多座。吉爾吉斯斯坦的
清真寺由獨立前的二十座增加到近兩千座。在
烏茲別克斯坦,宗教組織一下子冒出兩千零七個,清真寺由八十座猛增到一千八百一十六座。他們利用人們的宗教熱誠,散布有悖於宗教經典的異端邪說。他們超出正常宗教信仰,介入國家政治事務,甚至鼓吹髮動“聖戰”,“消滅異教徒”,企圖推翻世俗政權,建立“純伊斯蘭國家”。這樣,一個通常的宗教問題很快就轉化為一個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
現狀
癥結
中國民族問題的癥結,就在於我們在1949年建國後,參照前蘇聯史達林的
民族理論、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在中國進行了“民族識別”,客觀上把中國建成了一個“多民族共同體”。
這一結構使有些原來並不具有現代“民族意識”的“民族”精英開始接受這樣的意識並萌發潛在的“本族”願望。
“民族國家”的建立並成為新國際法的主權單元,始於西歐。西歐的民族主義運動,提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理念,並在各種力量角逐過程中建立了一系列“民族國家”。當時各“民族國家”內部包含的群體中也存在各種差異(血緣、語言/方言、歷史歸屬),但在“民族構建”過程中各群體都接受了新的“民族”概念、建立了共同的認同意識。
此後在其影響下塑建的政治實體,大多照此辦理,即在原有政治實體疆域範圍內,把各種不同的群體整合成一個現代的“民族”,在各群體中建立共同的政治認同和文化歷史認同,使各群體的所有成員都認同和忠誠於這個新的“民族”。受
西歐國家衝擊的東歐各國是這樣做的,由歐洲白人移民建立的新國家(如美國)是這樣做的,殖民地獨立後新建的國家(如印度)也是這樣做的。
1911年
辛亥革命後建立的中華民國,提倡“
五族共和”。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明確提出以“中華民族”作為“民族”單元來建立“民族國家”。
在上世紀初
沙皇俄國統治下的各群體,大多仍應屬於傳統封建部族,還沒有接受現代“民族”的政治意識和組織形式。在十月革命前,蘇聯共產黨為了早日推翻沙皇俄國反動統治,從發動革命和奪取政權鬥爭的需要出發,把沙皇俄國統治下的各部族都稱為“民族”並鼓勵和支持他們獨立建國。蘇聯在史達林領導下進行的“民族識別”工作和隨後的制度建設,是一種把
沙俄原來的傳統部族“政治化”的做法。在蘇聯的新體制下,各族接受了“民族”理念及其政治含義,“民族意識”不斷加強。同時,
前蘇聯憲法也為這些“民族”脫離蘇聯並成立獨立國家提供了法律依據。在
戈巴契夫不負責任的改革過程中,蘇聯原有的意識形態紐帶、經濟秩序、政治凝聚力都遭到破壞,於是那些已建立“加盟共和國”的“民族”因勢轉變為獨立的“民族國家”。之後,一些已建立“
自治共和國”的“民族”(如
車臣、
南奧塞梯等)仍在為獨立而戰。前蘇聯在民族理論工作和民族制度實踐中的經驗與教訓,我們應當仔細研究和借鑑。
在中央政府組織下,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先後“識別”出56個“民族”,這樣就在“民族”概念上出現了一個雙層結構——“中華民族”——56個“民族”。由於改革開放前中國人民很少有機會在國際事務中直接體會到“中國公民”的現實意義,而在國內生活中通過各種民族政策使少數民族身份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結果在客觀上把“中華民族”虛化和架空了。我們幾十年來一直在宣講馬列主義民族理論,介紹
史達林的“民族”定義,介紹
列寧的“
論民族自決權”,這樣宣講和教育的結果就使包括漢族在內的國民把對“民族”的認識定位於56個民族,而不是包含所有中國人的“中華民族”,並把現代政治觀念的“民族”意識介紹給了各“民族”的知識分子與民眾。
在“民族識別”工作完成後,政府為每個國民都確定了“民族成分”,這使中國各“民族”之間的人口邊界清晰化,而為各“民族”設立的“自治區域”則催生或加強了各族的“領土”意識,以“民族”整體為對象的各項優惠政策也使民眾的“民族意識”不斷強化。這就是在中國一些地區出現的民族關係問題和民族分裂思潮的國內思想政治基礎。這種“民族意識”主要體現在接受了“民族理論”教育的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和幹部當中,而接受教育較少的普通農牧民對國家和政府的忠誠情感還是十分純樸的。
出路
建國近60年來,中國的民族關係是比較和諧的。這與中國的基本國情(有2000多年歷史的
大一統國家和廣泛的族際融合、漢族占總人口的90%以上、漢族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占有明顯優勢、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扶助與優惠政策)及具體政策的實施效果相關。
在“
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過程中,中央政府和沿海各省在西部少數民族聚居區投入巨額資金,啟動了許多大項目,這些項目吸引了許多東部和中部的漢族勞動力來到西部,這使得漢族與西部少數民族之間的交流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
由於各級政府在漢族民眾中開展的民族知識與民族政策教育工作十分薄弱,這些來到西部地區的漢族企業家、管理人員和農民工們對西部少數民族的歷史、宗教、文化習俗缺乏了解,其中一些人因為當地少數民族漢語交流能力差和文化差異而對他們懷有偏見和不理解,這必然會導致部分少數民族成員感到不滿,再加上外部勢力的鼓動與支持,一些樸素和普通的文化差異問題、利益分配問題就會轉變為民族情緒,在複雜的國際政治背景下,極少數激進分子鋌而走險。
這些極端主義的活動有時以恐怖攻擊的形式出現,有時以街頭騷亂的形式出現,由於這些活動的對象針對固定的“民族”,很容易激發民族之間的相互不信任和感情隔閡。
09年的拉薩“3·14”事件和西藏、新疆等地發生的其他事件,雖然帶有一定程度的“民族”背景,但基本上是
群體治安事件和個別極端分子實施的恐怖攻擊事件。而隨後在北京、烏魯木齊等大城市和漢族地區發生的針對藏族、維吾爾族人員的整體性歧視行為(計程車拒載、旅店拒住、機場歧視性安檢等)卻反映出漢族整體性的大漢族主義態度,這是非常令人擔心的。這樣的態度使許多反對“3·14”事件和其他暴力行為的藏族和維吾爾族民眾非常傷心,也使漢族中的有識之士感到震驚。這充分暴露了自“文革”後政府在漢族地區缺乏民族知識、民族政策普及教育所造成的惡果。
以漢族民眾為對象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國情、民族知識教育和民族政策宣傳非常薄弱,漢族地區普通中國小教育中關於介紹我國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宗教習俗和我國民族政策的內容很少,甚至許多方面可以說是空白。這使得漢族民眾和青少年普遍缺乏關於我國少數民族的基本知識,在他們思考問題時有意無意地把“漢族”等同於“中華民族”。有些政府所屬文化部門關於“中國人”是“華夏子孫”和“龍的傳人”的片面宣傳在客觀上也加強了這一傾向。
黃帝崇拜是清末革命黨狹隘“排滿”的民族主義產物,許多少數民族對黃帝和龍圖騰並不認同,這些片面狹隘的宣傳有損於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加強,需要政府及時關注和糾正。
其他一些國家如美國和印度,國民中也存在許多不同的種族和族群、不同的宗教和語言群體,但是它們的“民族構建”目標就是把所有的群體建成一個共同的“民族”,而把這些群體稱為“
族群”。全體國民共同的核心認同是“民族”而非“族群”,強調的是國家憲法和國民的
公民權,而把種族、族群之間的差異主要看做是文化差異,不認為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權利。這可以看作是把族群“文化化”的思路。如美國的種族關係在歷史上一度非常糟糕,但是在強調種族平等、強調公民權的積極引導下,種族偏見和歧視逐步減弱,09年有黑人血統的
歐巴馬以絕對優勢當選總統,他的選舉口號是為全體美國國民謀利益,決不帶任何種族色彩。這樣的“文化化”思路也許值得我們思考。
正是在這樣的思考下,我在2004年提出把中國的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文化化”的思路,建議保留“中華民族”的概念,並在這一概念下重新開始“中華民族”的“民族構建”,以“中華民族”為核心認同建立一個全體中國人的“民族國家”,同時把56個“民族”改稱“族群”(簡稱××族),在這樣的
概念框架下強化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逐步淡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識。
只有這樣,才能加強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認同,共同凝聚起來,以一個民族即中華民族來面對和參與激烈的國際競爭。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依然保留了“部族國家”中傳統意識的群體,將會過渡轉變為現代“公民國家”的國民。這是一個漫長和需要足夠耐心的歷史發展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