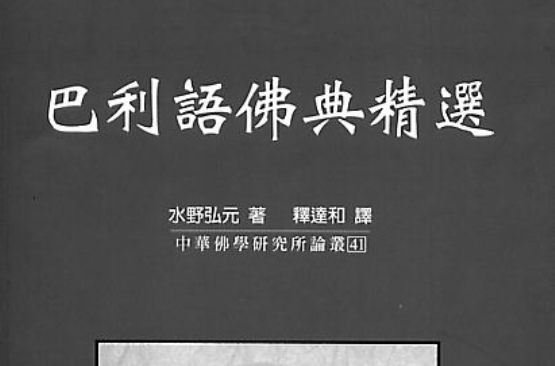現存
玆依律、經、論的順序,將現存的巴利佛典羅列如下︰
⑴律藏(Vinaya-pit!aka)︰
經分別(Sutta-vibhan%ga),又分波羅夷(Para^jika)、波逸提(Pacittiya)二種。
犍度(Khandhaka),又分大品(Maha^vagga)、小品(Cullavagga)二種。
⑵經藏(Sutta-pit!aka)︰
長部(Di^gha-nika^ya)。
中部(Majjhima-nika^ya)。
增支部(An%guttara-nika^ya)。
小部(Khuddaka-nika^ya)。
⑶論藏(Abhidhamma-pit!aka)︰
法聚論(Dhamma-san%gan!I)。
界論(Dhatu-katha^)。
人施設論(Puggala-pan~n~atti)。
論事論(Katha^-vatthu)。
雙對論(Yamaka-vatthu)。
發趣論(Pat!t!ha^na)。
此上所列,即巴利語佛典的核心內容──巴利三藏。除此之外,另有後起的重要文獻,包括對經典的注釋、教理綱要書、歷史書、史料等,總稱為‘藏外’典籍。
五至九世紀,錫蘭多次派遣僧尼到東南亞地區傳教,巴利三藏乃隨之傳入各國。目前在緬甸、
高棉、泰國、
寮國、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中國雲南省傣、布朗、德昂等民族地區的佛教圈,都有巴利系佛典流傳。依巴利佛典所使用的文字而言,計有
僧伽羅文、
泰文、緬甸文、
高棉文、寮文、三種傣文、天城體梵文、拉丁文等八種文字字母音譯的貝葉、紙寫及排印的
譯本。另有日文
譯本《南傳大藏經》六十五卷,以及巴利聖典協會出版的英譯本。
此外,緬甸在明頓(Mindon)王朝時期(1852~1877),曾召開第五次聖典結集會議,將巴利三藏聖典刻在石塊上。這些石塊尚存於曼德里古托多(Kuthadaw)。1956年,緬甸為紀念釋迦牟尼涅盤二千五百年,邀請高棉、
斯里蘭卡、印度、
寮國、
尼泊爾、巴基斯坦、泰國等國的比丘,舉行第六次唱誦結集會議,根據各種版本與第五次結集的校勘記,嚴密校勘巴利語三藏,印成迄今最完善的
巴利語系大藏經。
漢譯
巴利佛典迄清末為止,並未受到中國佛教界的重視。民國以來始稍受佛學界注意。至1992年為止,巴利佛學
要典之已被漢譯者,計有下列幾種︰
⑴《律藏》︰通妙譯。三冊。
⑵《長部》︰江煉百譯。
⑶《中部》︰芝峰譯。
⑷《小部》︰夏丏尊譯。
⑸《發趣論》︰范寄東譯。
⑹《大發趣論注》︰范寄東譯。
⑺《清淨道論》︰葉均譯。
⑻《阿毗達摩攝義論》等十餘部︰法舫等人譯。皆為篇幅較小的佛典。
這些漢譯佛典,自《律藏》以下,至《大發趣論》為止,皆轉譯自日本《南傳大藏經》中所收的日
譯本,且大多未曾全譯。譬如《長部》原有三十四經,漢譯僅有二十三經。《中部》共有一五二經,漢譯則僅五十經而已。其中,譯自巴利語原典者,有
葉均所譯的《清淨道論》,及法舫所譯的《阿毗達磨攝義論》(另有葉均
譯本,名為《攝阿毗達磨義論》),及其他若干小書。因此,巴利三藏之全部漢譯,仍有待學術界的努力。
◎附一︰無憂著〈巴利語文字簡況及其佛典〉(摘錄自《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巴利三藏典籍
上座部佛教各種文字的巴利三藏原典,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貝葉和仿貝葉的漆寫本或墨寫本,另一類是排印本。
貝葉本
或仿貝葉本
⒈貝葉寫本──錫蘭的僧伽羅文,高棉文、緬文、泰文和孟文字母等都有貝葉寫本的巴利文原典,其中保存得最完整的,根據現有的資料,恐怕要算泰國皇家圖書館所藏的拉瑪一世(1782~1809)和拉瑪三世(1824~1851)所修訂的皇室本貝葉三藏了。
拉瑪一世時修編的
泰文字母三藏典籍,開始於1788年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完成,前後共歷時五月,參加這一工作的共有二百三十名碩學長老和三十名皇家學者,全部三藏共有貝葉三千五百六十八筴,包括
律藏四十卷,經藏一百五十七卷,論藏五十六卷和巴利語詞遍三十五卷。這次編定的全藏還抄出了兩套副本作為僧侶考試和各寺院抄錄之用。後來在
拉瑪三世執政時,又由當時的皇族高僧瓦吉羅納那親王(即
拉瑪四世)先後兩次由錫蘭借來了巴利聖典七十卷作參考,修訂了
拉瑪一世本後,又抄錄出七部保存,其中的一部,據說裝幀得非常精緻。
⒉貝葉刻本──用針形筆把文字刺寫在貝葉上的佛經。這種刺寫本除了僧伽羅文外,還有中國傣族地區的西雙版納傣文,寮國和泰國北部的傣允及緬甸撣邦的景東一帶的貝葉佛具,也是屬於這一類型的。
⒊仿貝葉的漆寫本或墨寫本──緬甸的古巴利體字母佛典,大多是用墨漆寫在較貝葉略為寬大的紙質或銅質的紅漆描金的薄片上。中國德宏傣族地區因為不產貝葉,佛教徒所供誦的佛典都是構皮棉紙裝訂的墨寫本,西雙版納、臨滄和孟連等地,還有一些摺疊式的裱本;這些大小形式不同的寫本基本上和漢族地區的這一類型差不多。中國傣族地區的巴利語系佛典,從總目上看來,是包括了全部三藏的音譯及意譯各經在內的,而且還有著不少的其他藏外典籍。
排印本
現在已經編印出版的上座部三藏,共有以下的幾種︰
(一)巴利原典
⒈僧伽羅字母本,從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在錫蘭出版的佛典有長部、中部、相應部及增支部各經。佛涅盤二千五百年紀念時,錫蘭決定把全部巴利三藏譯為
僧伽羅語並與巴利三藏同時出版,現正在印刷中。
⒉泰文字母的排印本。屬於全藏的有兩種︰一為
拉瑪五世時1893年的曼谷版全藏,系根據
拉瑪三世時寫本修訂後付印的,共三十九卷,印刷了一千部,尚缺《小部經》中的〈本生〉、〈譬喻〉、〈天宮事〉、〈餓鬼事〉、〈長老偈〉、〈長老尼偈〉、〈諸佛譜系〉和〈所行藏〉各經。後來
拉瑪七世於1928年又印行了四十五卷的全藏一千五百部,並補排了
拉瑪五世曼谷版所缺的各經。此外,泰國還有把全部二萬四千頁的貝葉三藏縮編為一百零八筴,印刷在一千六百二十張貝葉上的簡本全藏及專為雨安居時念誦而編印的各經,共九十筴,以便在三個月的雨安居中每天誦完一筴。
⒊緬甸字母本。曾先後出版過包括
律藏、經藏中的《長部》各經和論藏的二十卷、二十一卷、三十八卷和三十九卷等四種版本。從1956年至1960年間又校勘了全部三藏,其後又印出了巴利和
緬甸語譯文的兩種版本的全藏,五十一卷本的註疏和十一卷本的解疏。
⒋印度的天城體梵文字母本。雖然,這部藏經遠在六十年前即已計畫編印,但最近幾年來才開始出書,現已印出包括經律部分的二十卷,還在陸續地編印中。
⒌英國巴利聖典協會版的拉丁字母本全部三藏六十五卷和註疏。
(二)譯文
除了緬甸語
譯本已在上面提到外,還有以下的幾種文字︰
⒈日本出版的《南傳大藏經》共六十五卷,系根據巴利聖典協會本譯出,未包括全部註疏在內,藏外部分只有︰《彌蘭王問經》、《島史》、《小史》、《清淨道論》、《一切善見律注序》、《攝阿毗達磨義論》及《阿育王石刻》等。
⒉中國的《普慧大藏經》中有從日譯《南傳大藏經》轉譯的部份,計有︰
⑴《本生經》只有譯出〈因緣總序〉和一
至一五0個本生故事兩卷。
⑵《長部》經典一至三十四各經共兩卷。
⑶《中部》經典的根本五十經一卷。
⑷《發趣論》一卷。
⒊英譯本。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先後出版的英譯上座部佛典,幾乎概括了全部三藏,收編在《東方聖書》和《佛教聖書》之內,此外還有各種不同的選
譯本或節譯本等。如《律藏》大小品即有三種不同的譯文。
⒋其它的歐洲文字,如德國、法國等的三藏零散譯文大約共在二十種左右。
⒌高棉王國於佛歷2472年(西元1928)起即組成三藏委員會,從事南傳佛典的柬語翻譯工作,經過僧俗學者十一年來的不懈努力,已在佛歷2482年(1938)完成了這項艱鉅的工作,共譯為一一0卷,現已出版六十七卷。
⒍中國的兩種傣文佛典譯文。都是貝葉或紙寫本,基本上包括了全部三藏各經在內。
⒎寮文字母的南傳三藏,不論是巴利原典或譯文可能還沒出版過。
◎附二︰Charles Eliot著·李榮熙譯《巴利系佛教史綱》第六章(摘錄)
巴利文經典最突出的特點,同時也是缺乏同情心的讀者最感厭倦的特點,就是單字、語句和整段文節的重複。這一部分是文法或至少是文體所產生的結果。巴利文造句法的簡單性以及很少使用從屬子句,導致了相同的片語有規則地並排平列,好像地板上的木板條一樣。用幾個
主詞,例如五蘊,來敘述某一件事時,很少發現有一個單獨句子包含一個複合的說明。一般說來,首先敘述第一蘊的事,然後再照樣重述其它各蘊。但是這種文句冗長的特性,另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在長時期中
三藏經典只以口授相傳。
三藏經典以口授的形式傳入錫蘭一百五十多年以後,於西元前二十年伐多伽摩尼王在位時,才第一次在錫蘭寫成文字。這一情況使我們無須懷疑經文的真實性。因為全部印度古代文學,不論是散文或者詩歌,都是以口授流傳下來的。甚至在今日,如果全部文稿和書籍都遺失了,大部分古代文學都能夠復原。佛教徒沒有像婆羅門那樣制訂詳細規則來保存和記憶他們的聖典,而且在佛教初期他們具有這樣的觀點,認為佛教教義不是需要背誦的符咒,而是應該理解和付諸實踐的原則。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努力背誦佛陀的言教,而且也許獲得成功,把這些言教變成最廣泛使用的方言。背誦整部吠陀經典以及附屬論文,即有關儀式、
韻律、文法和世系的附屬論文,這是當時常見的事(在印度現在仍能見到這一現象)。有這樣的記憶力,那是不難記住一系列說教中的要點的。佛陀逐日說法,大約有四十五年。他雖然有時談論特殊事情,但他無疑有一套講詞,經常重覆講用。由於他不斷地遷移地方,向新聽眾說法,所以不致有人反對這樣的重覆。在他的弟子中間有受過訓練的婆羅門信徒,在他逝世時必然有許多人,也許有幾百人,已經背熟了他的主要言論的概要。
但是一段說教不如一首詩或以某種記憶法編寫的材料那樣容易記憶。一個明顯的幫助記憶的方法,就是把說教分為若干標題,冠以數目,每一標題附帶某種顯著的短語,如果這些短語能夠重覆,那就更好。因為一個預定的公式在許多適當的地方出現,就能保證正確無誤。
巴利文經典令人生厭的機械性的重覆敘述,也可能一部分是由於僧伽羅人不願遺失外國傳教師傳授給他們的聖語,因為達到這種程度的重覆並不是印度文體的特點。這種情形在梵文佛經中不是像巴利文佛經那樣顯著,但是在耆那教文獻中卻非常明顯。適當的使用複述文體是《奧義書》的特色,我們在《奧義書》中發現有反覆敘述的公式,還有按照一個方式構成的連續片語,只有少數幾個字不同。
但是我仍然覺得重覆敘述不僅是說教記錄的特點,而且也是說教本身的特點。我們持有的版本,無疑地是把一段自由說教壓縮成為編有號碼的段落和重覆敘述的產品。佛陀所說的話一定比這些生硬的表格更為活潑柔軟得多。(中略)
三藏經典的可靠性必須用印度口授相傳的標準來予以判斷。它的最大缺點就是缺乏歷史感,這一點我們一再注意到了。印度史傳家忽視重要事件,他們記載的事情都是模糊不清,事情的規模和連貫性以及年代都不可查考。他們常常在很小的事實基礎上,或者根本沒有基礎,就建立起一個故事的結構。但是故事一般是很明顯的,所以過去歷史學家的困難不是在於被這些故事引入歧途,而是在於忽視故事中可能包含的真實因素。因為印度人具有良好的語言記憶力,所以他們的世系、帝王世系和地名一般說都是正確的,而且他們特別喜歡記憶人名表。他們在敘述學理方面也有真正興趣。如果佛陀被人曲解了,那倒不是因為缺乏傳達深奧思想的智慧和能力,而是因為對神學感興趣的人往往根據自己所愛好的見解來解釋教主的教義。
三藏經典說明了印度傳統的長處和弱點。歷史感的微弱性可以從《小品》關於提婆達多的行為的記述中看出來。《小品》的編者似乎不能對他所認為的重大事件作出清晰的記載。就是這部著作討論寺院規則時,則很豐富而明確,而且其中記載的言論具有真實可靠的風格。在佛教經典中,印度人記憶力的優點發揮了作用。歷史的連貫性是沒有問題的。在經典中我們只有一段導言,說明某些人物和地點的名稱,然後就是一段說教。我們從
律藏中知道,僧人們應當牢記這些事情,而這些事情正是他們能夠背誦的東西。我認為沒有理由懷疑在波羅奈所說的教法,以及《長阿含》第一篇中的重覆章節,是佛陀逝世以後不久公認為他的言論的巴利文版本。方言的變化沒有重大意義。阿育王的巴布魯敕文中記載說︰‘善法因此將久住於世。’據信這句話是引用語,而且很明確地十分接近《增一阿含》中的一段話。阿育王的原話是︰Saddhamma cilat hitikehasti,而巴利文則是︰Saddhammo ciratthi-tiko hoti。佛陀的語言和我們持有的典籍之間的差異,大致與此類似。在
巴利文、梵文和同類的
印度語言中,概念集中表現在單字上,而不是
漫衍在全句中。這一事實就減低了語言變化的重要性,增加了表達概念的便利。因此波羅奈說教中的主要字眼,即使作為一個沒有文法聯繫的字彙表,也是十分明確地表達了要旨。我可以同樣地構想,《長阿含》的早期經典中所記載的關於宗教生活的進程的那些重覆段節,都是佛陀本人言論的回聲。因為這些段節不僅具有古風而且還有雄辯與高尚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