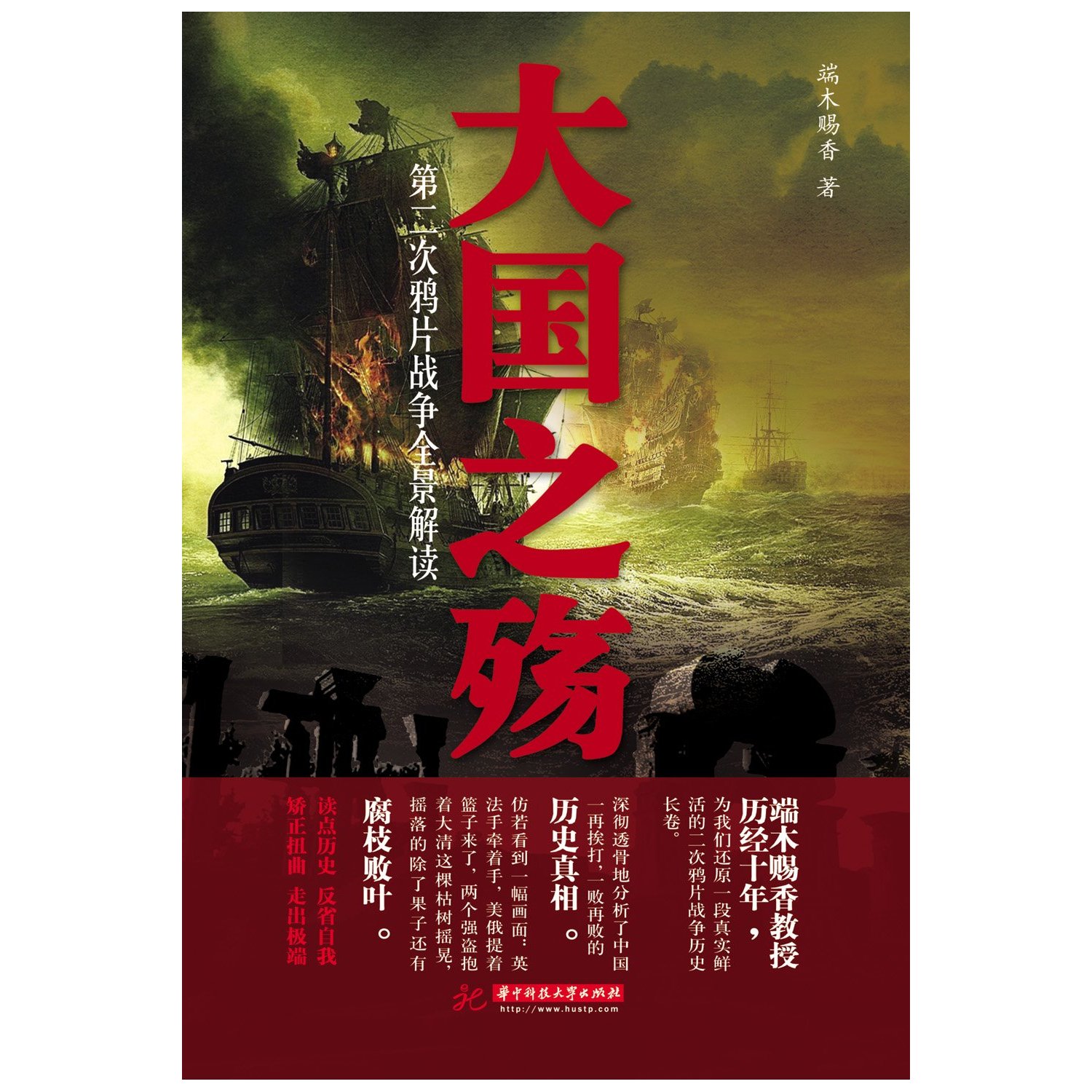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國近代史著作,講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起因、經程和結果,其中各方動態、心態寫得比較細膩生動,反映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所處的世界環境,國際形勢。
基本介紹
- 書名:大國之殤
- 又名:第二次鴉片戰爭全景解讀
- 作者:端木賜香
- ISBN:9787560995595
- 頁數:314
- 定價:39.80
- 出版社: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4-3-1
- 裝幀:平裝
內容簡述,作者簡介,目錄,序言,文摘,
內容簡述
著名歷史學教授端木賜香歷經十年研究,為我們揭開了一個真實鮮活的中國近代第二次鴉片戰爭歷史長卷。 真切透骨地全面解讀了中國在鴉片戰爭中一再挨打一敗再敗的歷史真相。讓我們仿佛看到這樣一幅畫面:英法手牽著手,美俄提著籃子來了,兩個強盜抱著大清這棵枯樹搖晃,搖落的除了果子還有枯枝敗葉。
作者簡介
端木賜香,原名李桂枝,畢業於河南大學歷史系,現任教於河南安陽師範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從事中國近代史與中國傳統文化批評研究多年。自稱平生要務:拆歷史的牆角,探文化的陷阱,還原歷史,奉獻常識。因其文風義理,章立凡先生稱其“歷史頑主”,鄢烈山先生贊其“仁義多情”。著有《有味的傳統文化課》《重讀晚清六十年(1851-1911)》《1840:大國之殤》《歷史不是哈哈鏡:真假袁世凱辨別》等。
目錄
自序 在一個地方跌倒,就在同一個地方再次跌倒! / 2
第一章 簽約,簽來了十年的休戰 / 4
條約簽訂了,中國進入了條約時代 / 4
條約雖然簽了,但俺們都是被逼的 / 12
英國傻佬:高興得過早了 / 16
廣州故事:俺最會說“不”了! / 18
福州故事:曲線愛國惹著了誰? / 27
第二章 科舉舉出個造反派,修約修出了戰爭派 / 36
洪秀全高考落榜,反了 / 36
外國聽說了拜上帝教,樂了 / 39
1854年:英國帶頭要修約 / 43
上海:華夷和平共處的模範根據地 / 49
1856年:美國帶頭要修約 / 52
第三章 英法聯手了,美俄提著籃子來了 / 54
亞羅號事件,巴夏禮惱了 / 54
廣州開打了,英國議會開吵了 / 56
馬賴事件,拿破崙三世不安了 / 61
英法聯手上樹,美俄提籃上場 / 64
——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全景解讀
第四章 廣州又開戰了,這回徹底玩完了 / 67
廣州:這回徹底玩完了 / 67
葉名琛:自號“海上蘇武” / 69
柏貴:綽號“匹克威克” / 71
廣東三紳:將團練進行到底 / 74
第五章 第一次大沽口之戰 / 76
大沽口:開戰了 / 76
鹹豐:廣東幹得咋樣了? / 78
天津:難產的條約 / 80
上海:難纏的修約 / 89
鹹豐:備戰備荒為悔約 / 100
第六章 換約換來了第二次大沽口之戰 / 104
俄國公使狡猾:最先換了約 / 104
英國公使:換約之前先換了一肚子氣 / 107
大沽口二次開戰:英法進了僧王的套? / 109
美國公使華若翰:就這樣被大清玩了一把 / 114
大沽之事傳出:傲慢倫敦與浪漫巴黎同時大嘩 / 118
第七章 第三次大沽口之戰 / 122
鹹豐:亢奮得有些過頭了 / 122
英法聯軍:第三次光臨大沽口 / 124
北塘天津:一古腦兒地陷落了 / 128
惠親王:著天津百姓對著夷人故作忿忿之勢! / 132
英明領導鹹豐:把談判使臣給我拿下 / 133
鹹豐想先跑,發下的紅頭檔案卻是親征 / 135
英法使者:在北京體驗中國特色的刑罰 / 138
蒙古騎兵:在京津之間體驗英法特色的騎兵戰術 / 139
第八章 英法聯軍進北京 / 144
大臣的弱智方略和鹹豐的領導先跑 / 144
北京同仁堂:牛啊羊啊,送給那親人鬼子兵 / 148
圓明園:愛新覺羅家的處女地,留守的卻是太監 / 149
奕訢:有困難,找俄國;額爾金:我放火,我有理 / 153
北京條約簽訂了,親王自尊受傷了 / 155
額爾金的疑心,鹹豐帝的心病 / 157
俄國調停,中國謝媒 / 160
第九章 盤點戰爭之後事 / 161
孟托班凱旋而歸,迎接他的是冷嘲熱諷 / 161
雨果流亡國外,大罵政府是強盜 / 163
額爾金:搬起自己的腳,砸別人的石頭 / 166
黃宗漢:俺的跨年度述職報告 / 168
戰爭結束了,歷史卻仍在重演 / 170
第一章 簽約,簽來了十年的休戰 / 4
條約簽訂了,中國進入了條約時代 / 4
條約雖然簽了,但俺們都是被逼的 / 12
英國傻佬:高興得過早了 / 16
廣州故事:俺最會說“不”了! / 18
福州故事:曲線愛國惹著了誰? / 27
第二章 科舉舉出個造反派,修約修出了戰爭派 / 36
洪秀全高考落榜,反了 / 36
外國聽說了拜上帝教,樂了 / 39
1854年:英國帶頭要修約 / 43
上海:華夷和平共處的模範根據地 / 49
1856年:美國帶頭要修約 / 52
第三章 英法聯手了,美俄提著籃子來了 / 54
亞羅號事件,巴夏禮惱了 / 54
廣州開打了,英國議會開吵了 / 56
馬賴事件,拿破崙三世不安了 / 61
英法聯手上樹,美俄提籃上場 / 64
——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全景解讀
第四章 廣州又開戰了,這回徹底玩完了 / 67
廣州:這回徹底玩完了 / 67
葉名琛:自號“海上蘇武” / 69
柏貴:綽號“匹克威克” / 71
廣東三紳:將團練進行到底 / 74
第五章 第一次大沽口之戰 / 76
大沽口:開戰了 / 76
鹹豐:廣東幹得咋樣了? / 78
天津:難產的條約 / 80
上海:難纏的修約 / 89
鹹豐:備戰備荒為悔約 / 100
第六章 換約換來了第二次大沽口之戰 / 104
俄國公使狡猾:最先換了約 / 104
英國公使:換約之前先換了一肚子氣 / 107
大沽口二次開戰:英法進了僧王的套? / 109
美國公使華若翰:就這樣被大清玩了一把 / 114
大沽之事傳出:傲慢倫敦與浪漫巴黎同時大嘩 / 118
第七章 第三次大沽口之戰 / 122
鹹豐:亢奮得有些過頭了 / 122
英法聯軍:第三次光臨大沽口 / 124
北塘天津:一古腦兒地陷落了 / 128
惠親王:著天津百姓對著夷人故作忿忿之勢! / 132
英明領導鹹豐:把談判使臣給我拿下 / 133
鹹豐想先跑,發下的紅頭檔案卻是親征 / 135
英法使者:在北京體驗中國特色的刑罰 / 138
蒙古騎兵:在京津之間體驗英法特色的騎兵戰術 / 139
第八章 英法聯軍進北京 / 144
大臣的弱智方略和鹹豐的領導先跑 / 144
北京同仁堂:牛啊羊啊,送給那親人鬼子兵 / 148
圓明園:愛新覺羅家的處女地,留守的卻是太監 / 149
奕訢:有困難,找俄國;額爾金:我放火,我有理 / 153
北京條約簽訂了,親王自尊受傷了 / 155
額爾金的疑心,鹹豐帝的心病 / 157
俄國調停,中國謝媒 / 160
第九章 盤點戰爭之後事 / 161
孟托班凱旋而歸,迎接他的是冷嘲熱諷 / 161
雨果流亡國外,大罵政府是強盜 / 163
額爾金:搬起自己的腳,砸別人的石頭 / 166
黃宗漢:俺的跨年度述職報告 / 168
戰爭結束了,歷史卻仍在重演 / 170
序言
自序
在一個地方跌倒,就在同一個地方再次跌倒!
拙著《那一次,我們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全景解讀》出版後,凱迪·貓眼看人上的網友反映:看得不夠過癮,什麼時候出版“第二次挨打”?
他們把我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簡稱為“第一次挨打”(也有戲稱為“一鴉”或者“一丫”的),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當然就是“第二次挨打”了(順理成章被戲稱為“二鴉”或者“二丫”)。
其實,寫“一鴉”的過程中我就有了寫“二鴉”的心思與準備,在網上跟他們開玩笑說:“二鴉”的名字我都想好了:《這一次,我們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全景解讀》。問題是貓眼網友比我要俏皮,回帖表示要跟我預訂以下幾本書:《那一次,我們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全景解讀》、《那一次,我們再挨打—中日甲午戰爭全景解讀》、《那一次,我們怎么還挨打—1國對8國戰爭全景解讀》……另一網友接碴說:最後那本書名字不對,應該是《那一次,我們怎么還挨打—1國對11國戰爭全景解讀》。目睹這些書名,滑稽與悲哀同時湧上心頭。
不得不承認,天朝畢竟是天朝,有著不一般的稟性。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天朝並沒有受到什麼觸動,被時人稱作“雨過忘雷”。總之,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十年時間,清政府白白浪費了,並等來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愣是在世界史上創造了這樣一種奇蹟-在一個地方跌倒,就在同一個地方再次跌倒!
雖然不是大清國的子民,對它的顢頇與挨打也用不著咋表示多情。但是,誰讓歷史中總有現實的影子,現實中總有歷史的遺傳信息呢?我們至今仍沒有走出歷史,又何能置身局外?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道光皇帝在羞憤與委屈中慘澹執政,死後把大清這艘帶漏的破船傳給了皇四子奕詝,年號鹹豐。學人習慣把鹹豐稱作苦命天子。苦不苦另當別論,這命本身很大程度上卻是他自找的,具體來講,是依仗儒術玩來的。當時道光在老四奕詝與老六奕訢之間選擇皇太子時,一直猶豫不決來著,中間經過了三次測試:
第一次,諸皇子校獵南苑,老六獲禽最多,老四卻未發一矢,問之,就把杜受田老師預先教的那套背出來了:“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乾天和。”杜老師不愧是山東大儒,深得儒術中的虛偽精髓,給老四編的這套話哄得道光樂開了花,說:“此真帝者之言!”
第二次,道光弄了兩個盒子,一個金制,一個木製,金制的雕著龍,金光閃閃的;木製的刻著麒麟,漆得油黑髮亮。道光讓兄弟兩個各挑一個。老四說:六弟先挑吧。老六聽了,好象沒聽過儒家炮製的孔融讓梨故事似的,下手就把金盒抓到了自己手裡。老六不知道,手裡抓獲的是金盒,屁股底下失去的卻是龍椅啊,最後只混個恭親王的名號。老六笨就笨在這裡,當皇帝都要三卻之呢,自己面對一個盒子就急得猴兒似的,不會虛偽害死人哪。估計跟他的老師、來自四川的卓秉恬教導無方有關!
第三次,道光生病時召二皇子入對以最後決定儲位。二皇子各請命於其師,卓秉恬對自己的學生說:“上如有所垂詢,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杜受田對自己的學生說:“阿哥如條陳時政,智識萬不敵六爺。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將不久於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誠而已。”
最終的結果大家都知道:當道光託付後事的時候,老六在一旁指點江山糞土當年萬戶候,好象在參加國際大專辯論賽似的。老四則在一旁撅著屁股只管哭,痛苦得那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於是乎,老四就當上皇帝了。水平可以啊,憑這套瞞和騙的儒術去對付中國四億愚民,夠了;可是用來對付西方世界,不夠用不說,它還招打哪!
《南京條約》簽訂後,西方本認為,中國進入條約時代了,只要按照條約來,平等會有的,生意也會有的。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發現遠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清政府依然一廂情願自作多情地把外國當進貢國看待。監修鹹豐朝《籌辦夷務始末》的清國大學士賈楨在給同治帝的進書表中云:“欽惟我文宗顯皇帝,仁義兼施,恩威並用,體天地好生之德,擴乾坤無外之模,率俾遍於蒼生,潤澤流於華裔。較之漢家盛德,呼韓向化而款關,唐室中興,回紇輸誠而助順,有其過之,無不及焉。而宵旴憂勤,猶恐中外子民未盡出水火而登衽席,如傷之隱,時切聖懷。”ꨁ清國大學士約相當於科學院院士吧,看他把天朝吹的,遠超漢唐不說,連全世界人民都心向北京了。清國的任務就是拯救全天下那三分之二-致命的多情!
其次,如果說道光是撫夷派的話,那么鹹豐則是剿夷派了,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強硬份子,以“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敬酒不吃吃罰酒”、“挨整磚不挨半截磚”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跟西方外交。這方面的典型代表乃是兩廣總督葉名琛。西方人的印象里,葉名琛是“一個表示死不交涉的代用詞”ꨂ。於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煙火依然是由廣東點起,一路燒到了天津,燒出了一個天津條約。如果第二次鴉片戰爭到此為止,那么英法聯軍進北京、火燒圓明園的事兒就不會發生。可是鹹豐又玩起了他那套坑蒙拐騙的儒術。他與僧格林沁合謀,在大沽口誘擊西方前來換約的人馬。當西方前來報復,雙方再次坐下談判時,他又指示談判大臣怡親王載垣扣押西方談判人員、虐殺西方俘虜。人家39個活的,被歸還的時候,卻只剩19個喘氣的。賣瓜的,世界上哪有這樣野蠻的政府?這樣野蠻的政府,中國人習慣了,西方人怎么能容忍?
鹹豐不按國際遊戲規則出牌,屢次玩失信與悔約,其理論支撐來自於儒家孔夫子的要盟不信-和約是你們強迫俺們簽的,俺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不予遵循。再說了,那和約條款打死也不能接受啊:公使駐京也就罷了,居然還要求中國皇帝親自接見;親自接見也就罷了,居然不執中國通行的三跪九叩之禮,鹹豐小臉拿不下來啊:全國人民都在我腳下匍伏著,他們中的一小撮才有資格在我面前下跪三次,且每次下跪後都得額頭貼地屁股朝天如是者三。周邊的朝鮮、越南、琉球使者都是這樣來的,就爾們西夷不跪,全國人民得知後,皇上的臉面何在?威風何在?當然了,臉面與威風的背後,藏著所謂的“禮”,即儒家的政治訴求,比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臣之禮;三從四德的婦人之禮;融四歲能讓梨的孝悌之禮;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中國中心之禮;懷柔遠人教化夷狄的夷夏有別之禮等等。老六恭親王奕訢雖然沒做成皇帝,但他在《禮可以為國論》的文章中強調:“辨上下而定民志者,禮也。上下之分既明,則威福之權皆出自上。君君臣臣,國本固矣”;“壞國者,必先去其禮”。ꨁ一句話,禮就是清政府的基本國策,延伸到叩頭上,叩頭就可以興國,不叩頭就足以亡國。於是我們看到的歷史情形就是,大清為保住一個儒家的叩頭之禮而導致英法聯軍進北京,為遵循儒家的要約不信而導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
理清了歷史的內在邏輯與發展線索後,誰還會否認,鹹豐這挨打的苦命不是他自找的?
他自找挨打也就罷了,問題是,放到歷史的長時段里,按著民族主義的情緒,他這種找打很讓當代國人難為情。因為按照正常的邏輯,爹挨了打,兒子該長記性呢。清國倒好,爹(道光)挨打,兒子(鹹豐)還挨打,子子孫孫竟永遠挨了下去。更讓人難為情的是,清國挨打,從中長記性的卻是鄰居日本。
眾所周知,小日本的閉關鎖國比大清的年頭還要早,開始於1636年(這時候大清還沒有入關呢)。當時的小日本跟未來的大清一個德行,實行單口貿易制度,僅開放一個長崎。而且,這貿易還限對象,僅限於中國、荷蘭、朝鮮、琉球等。站在文化交流的層面,按著社會學的概念,這種閉關鎖國政策簡直就叫近親結婚,所以小日本跟大清國是一樣的愚昧!
不過,愚昧也分境界的高低。1840年至1842年,中英發生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的訊息傳到日本,日本馬上睜開了一隻眼;1856年,中英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日本馬上睜開了另一隻眼。睜眼的結果,就是主動和西方各國簽約,門戶洞開,自由貿易,徹底開放,全面維新!相形之下,清國挨了兩次打,依然處於稀里糊塗半睡半醒中,扭扭捏捏地搞了個只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洋務運動,僅僅走向了傳統儒家理念上的同治中興,三十年後中日甲午戰起,日本全殲中國北洋海軍,既標顯日本維新之路的正確,又標顯中國洋務運動的後發劣勢。這個時候,清國才再次扭扭捏捏地走向光緒維新,問題是沒走三步就被慈禧使個絆子栽死了。恩格斯所嚮往的“親眼看到全亞洲新紀元的曝光”ꨁ和馬克思所幻想的“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ꨂ就這樣淪為歷史深處的囈語。
為什麼,中國沒有選擇日本的應對方式?
為什麼,中國的選擇只會招致一次又一次的挨打?
讓我們走進歷史的現場,去體味那再次挨打的痛楚吧!
文摘
第六章
換約換來了第二次大沽口之戰
俄國公使狡猾:最先換了約。俄國大大地狡猾,搶在英法之前率先和清國互換了天津和約。他們的換約使節是新任駐北京東正教會監護官彼羅夫斯基(P.N.Perofski)。
提到沙俄駐北京東正教會監護官,我們這裡得補充兩句。中俄關係在當時,相對於其它西方列強有與眾不同之處。因為別的國家在北京既沒有東正教會,更沒有監護官。沙俄能弄這么個駐京辦,著實占盡了先機。那么沙俄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
17世紀40年代起,乘大清入關之機,沙俄開始侵入黑龍江流域,占領尼布楚和雅克薩等地。期間,沙俄政府也不斷的向中國派出商團與使團,要求中俄建交通商云云。但由於沙俄在黑龍江的非法侵擾;由於沙俄拒不引渡出逃俄國的偷渡犯-居住在嫩江流域的索倫部頭人根忒木爾;更由於清政府只認朝貢外交-對俄使拒不叩頭卻要求親遞國書的執拗很惱火,所以雙方總是談不攏。雖然有些使團代表回去後向政府匯報:擁有大炮、火繩槍的中國,並不懂得按照軍事科學的要求行動,因此,一支不大的歐洲軍隊就可以把他們制服。ꨁ但是,大清畢竟是個新生的政權,軍隊戰鬥力還是可以的,何況沙俄當時在南方正忙著奪取克里米亞,在西方正準備奪取波羅的海出海口,人力物力有限,在中國邊境投放的侵略人馬那是相當的少,一支侵略人馬,少者二十來個人,多者六十來人。著名的1685年的第一次雅克薩(俄方稱雅克薩為阿爾巴津)之戰,沙俄方面頂多一千人馬,清方出動三千人馬;1686年的第二次雅克薩之戰,沙俄方面八百來人,清方出動二千人馬。ꨁ除了人力懸殊之外,當時雙方的武器也不相上下,雖然當時的沙俄已普遍使用火槍和手榴彈,但是清方除了刀、矛、弓箭,除了一手拿藤牌一手拿刀片的英雄無敵的福建藤牌兵,它還有紅夷大炮-明末由葡萄牙人、荷蘭人販運到中國的16至19世紀之間的英式前裝重型滑膛炮和康熙年間清方仿照紅夷大炮所製造的神威無敵大將軍炮,所以俄方的大炮跟清方的大炮是一個水準。何況攻城掠地看重的就是大炮呢?
所以,中俄之間當時的會戰,大清政府還是挺占上風的。第一次雅克薩之戰後,俄方六百多俘虜被清政府放歸,可是還有四五十人願意留在清朝,於是他們被遷入北京。在康熙皇帝的親自授意下,把他們編為最嫡系的部隊——八旗滿洲鑲黃旗,編制為鑲黃旗滿洲第四參領第十七佐領,史稱“俄羅斯佐領”(俄國史籍稱他們為“阿爾巴津人”)。康熙當時這樣做,有自己的考慮-這些人在以後的中俄戰場上將會有用。康熙把他們送往黑龍江前線,讓他們偵察敵情和招降俄國士兵。所以俄國方面提到“阿爾巴津人”,在某些特定場合,意為“俄奸”。1689年中俄兩國結束戰爭,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劃定了兩國東段疆界,準許俄商前來北京貿易,又規定在此之前,凡在中國的俄國人和已在俄國的中國人均不必遣返。ꨂ於是這些“俄奸”得以在北京留居下來。據清代學者俞正燮考證,雅克薩戰爭前後留居北京的俘虜和他們招降過來的以及主動投奔過來的東正教徒,合計已有百人。ꨃ他們被安置在屬於鑲黃旗地面的東直門內胡家圈胡同。清朝政府對他們的生活待遇很優厚,和旗人一個標準,供給他們住房、衣食,發給他們年俸,準許他們與中國人通婚,將步軍統領衙門收押的女犯配予他們為妻,還給他們當中的某些人匹配了大戶人家的女人。
他們與其他旗人一樣,以當兵為基本職業,並領有糧餉。一些人被授與官職,一些人則在衙門中擔任翻譯工作。這些生活,比當初做俄兵或者武裝移民享受多了。
宗教信仰方面,清政府對這批俄奸俄俘也是相當的寬容,竟然給他們信仰自由。他們中有一個叫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的,是教堂司祭。康熙皇帝把胡家圈胡同內一所關帝廟賜給他們作為臨時教堂,還授給列昂季耶夫七品官銜,讓他主持教堂活動。當時,中國人把俄羅斯人稱為“羅剎”,這座小教堂遂被稱為“羅剎廟”。列昂季耶夫從雅克薩城帶來了聖尼古拉的神像,所以,這座教堂也稱為尼古拉教堂。
由於尼布楚條約規定,俄商可以前來北京貿易,所以俄國開始在赴中國的商隊里混幾個教士到北京秘密活動,並且與“羅剎廟”建立聯繫。這樣,原先所謂的俄奸根據地,慢慢地就滲透進了俄國特務,快要變成俄國特務駐京辦了。1711年,俄國一商隊來到北京,領隊胡佳科夫按照彼得一世的授意,以列昂季耶夫年老為理由,要求理藩院準許俄國另派教士來京接替,康熙皇帝同意了這個要求。1715年,俄國派遣的第一個傳教士團到達北京。清政府居然還定期賜給他們生活費和糧食。政府不知道,北京的東正教這時已開始發生性質上的變化,也就是說,俄國政府可以通過對這個傳教士團施加影響而達到自己的政治與軍事目的。事實上,後來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轉向。1727年中俄訂立了《恰克圖界約》,該條約規定,由中國方面幫助俄羅斯東正教會在北京建立新教堂。還規定,傳教士在京一人,可以從國內補來3人,另可攜帶6名藝術及語言方面的學生。ꨁ此後養成了慣例,傳教士團每10年輪換一次,每次由大約4名神職人員(修士大司祭一名,修士司祭兩名,修士助祭一名,由清政府供其食宿之資)和6名世俗人員(名義上的學生,由俄方提供食宿,有些學生在理藩院做翻譯,盜竊中國情報簡直太容易了)組成。從此時起,一批一批的傳教士團來到北京。至於新教堂,在北京城南部的東江米巷(即後來的東交民巷)建成,舊教堂與新教堂一北一南,這就是所謂的俄羅斯北館和俄羅斯南館之由來。俄羅斯北京傳教士團隨即由胡家圈胡同的北館遷入南館。
1808年開始,俄國外交部還正式派出一名監護官隨同,負責教士團的換班事宜。至於教士團,一開始由沙俄西伯利亞事務衙門領導,後來乾脆直屬沙俄外交部管理了。於是乎,北京的教士團,吃著清政府的大米拿著清政府的工資,卻變成了俄國外交部的下屬機構,在沙俄政府的訓令下,擔當了以下活動任務:其一,維持北京俄羅斯人的東正教信仰。他們中的一些人,受到中國妻子與中國生活環境的影響,不但墜入了溫柔之鄉,還對東正教不怎么信仰了。其二,完成俄國政府的外交任務,自康熙年間至鹹豐年間,俄國東正教會傳教士團,一直兼為俄國政府駐華代表。這也使俄國成為1860年以前唯一在中國首都保持使團的國家。其三,向俄羅斯商隊提供住所和幫助,發展中俄貿易。其四,多方面研究中國,刺探情報。
政府後來甚至訓示:傳教士團的主要任務不是宗教活動,而是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與對中國政治活動的匯報。ꨁ最令人感嘆的匯報是:清政府是一個人口稠密、防禦很差的富饒國家,因此俄國在遠東經濟方面和領土方面發展的可能性幾乎是無限的。ꨂ說得不好聽些,原先的俄奸機構,就這樣慢慢變質成了神奇的漢奸機構。康熙當初利用他們為清國政府服務的,又被俄國改造成為俄國政府服務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情報方面,俄羅斯駐京傳教士團功勞大大的,否則英法聯軍也不至於把仗打得象一場遠東旅遊一樣行雲流水。而對於清政府來講,之所以樂意與俄羅斯保持這種關係,最大的原因是這種關係某種程度上體現的是朝貢色彩。
俄方公文通過理藩院處理,中方給予俄方傳教士盤費養膳。俄方省了諸多經費,清政府得了一些面子,雙方感覺都很好。總之,清政府愣是在中俄關係史上創造了一個奇蹟:己方出資,給彼方養間諜!清政府在這方面的花費是筆糊塗帳,能找到的數字是1820年的。這一年,清政府給傳教士團提供的資金是1千盧布、大米是9千多鎊。ꨃ1858年,恰是俄羅斯傳教士團換班之時。大司祭固禮(Gurii)率領他的傳教士團前來北京換班,外交部官員彼羅夫斯基奉命監護。彼羅夫斯基也沒有和固禮同行,他當時在東西伯利亞總督任地伊爾庫次克,所以直接由此地出發前往北京。這時,中俄《璦琿條約》和中俄《天津條約》相繼簽訂,俄國為了急早完成換約手續,竟顧不上從彼得堡派出新公使了,而是臨時把新公使的頭銜摁在了彼羅夫斯基頭上。伊爾庫次克在貝加爾湖南端,離中國特近,彼羅夫斯基得到新的任命後,從當地起身,於10月10日到達北京,並根據慣例入住俄羅斯館。俄方向清方申明:雖然有派使臣進京之說,但是恐給貴國增累,所以停止另派大臣,轉派監護官彼羅夫斯基交涉天津條約等相關事宜。問題是彼羅夫斯基這新頭銜來得太倉促,根本沒有拿到俄國政府的全權證書以及俄國政府對《天津條約》的批准書。
所以他入住俄羅斯館後的兩個月時間內,也沒好意思向清政府說明自己的兼職,清政府沒有接遞外國使者國書的習慣,也就稀里糊塗的不加過問。
1858年12月,彼羅夫斯基拿到了相關證書,這才跟清方亮相,要求換約的幹活。鹹豐雖然覺得不太對勁兒,但還是派了理藩院兩位高官肅順、瑞常與彼羅夫斯基談判。
由於條約文本的爭執,中俄雙方換約的時間特長,從1858年12月,一直換到1859年的4月。
桂良在上海聽說,俄使都進京了,連忙上奏,英法美知道後就了不得了。桂良的擔心是對的,因為中俄天津條約只規定了一年之內換約,根本沒說換約地點。英法美聽說了,進京換約更理直氣壯了。對此,鹹豐說好辦,北京先談著,到時候改在庫倫換約。同時,受僧王那個北塘進京之餿主意的啟發,他指示肅順與彼羅夫斯基制訂了北塘進京的換約路線:俄使從海口進京,在攔江沙外停泊,中方前往迎接,由北塘進京。並且由理藩院將此辦法專門知會俄國政府。ꨁ找不到確切資料,不知道中俄最後到底在京還是在庫倫換的約。但是軍機大臣的奏報里說肅順已與“該使”換約,那么這個“該使”當是彼羅夫斯基無疑。ꨂ彼羅夫斯基從1858年10月10日進入北京,直到1859年6月25日第二次大沽口之戰爆發,一直呆在北京與清政府糾纏來著。1859年4月換約成功後,彼羅夫斯基並沒有走的意思,按說,傳教士團換班早已完成,中俄換約也已完成,彼羅夫斯基也應該回了。但是,政府授意之下,彼羅夫斯基還有第二項兼職:璦琿條約與天津條約簽訂後,俄國政府在烏蘇里江那旯旮更忙活了。黑龍江以北那60萬是歸俄國了,這不還有烏蘇里江以東40萬中俄共管嗎?總得再確定一下吧。為此,5月4日,彼羅夫斯基突然向清方提交一個《補續和約》八條。
清方一下子傻了。清醒過來後,開始攆彼羅夫斯基走,但人家就是不走,一直賴到6月底沙俄政府調他回國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