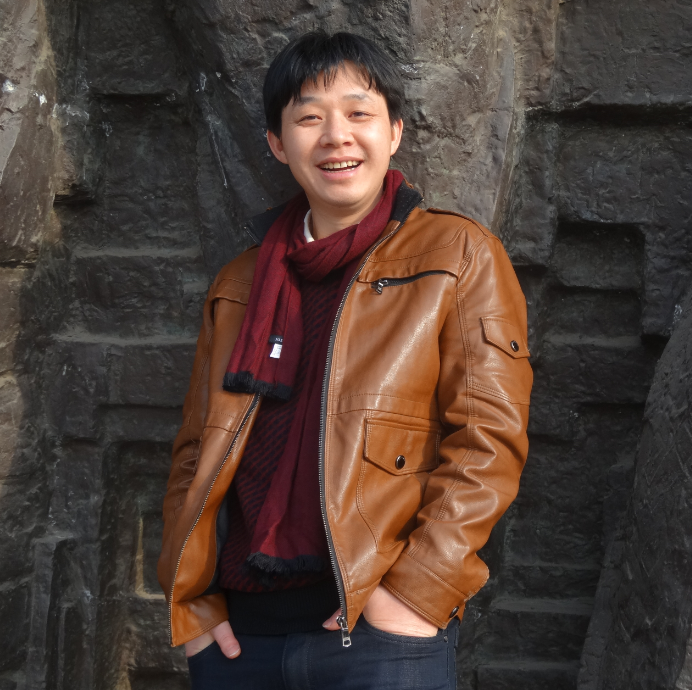楊仕芳,侗族,1977年9月出生,廣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縣人。廣西文壇新勢力代表作家。1997年畢業於桂林民族師範學校,先後當過鄉村教師、縣委辦秘書、報刊編輯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楊仕芳
- 國籍:中國
- 民族:侗族
- 出生地:廣西柳州三江縣
- 出生日期:1977年9月
- 畢業院校:魯迅文學院第十九屆高級研討班
- 主要成就:2007、2008、2009年廣西文學獎
第四屆廣西少數民族創作“花山獎”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 代表作品:長篇小說《故鄉在別處》
- 性別:男
主要作品,相關評論,人物訪談,
主要作品
短篇小說《楊浦十六歲》,發表於《行報》2007年3月15日C13版。 楊仕芳首部長篇小說《故鄉在別處》
楊仕芳首部長篇小說《故鄉在別處》
 楊仕芳首部長篇小說《故鄉在別處》
楊仕芳首部長篇小說《故鄉在別處》中篇小說《明天,我年滿十六歲》,發表於《廣西文學》2007年第8期,獲第五屆廣西青年文學獎。
中篇小說《我們的世界》,發表於《民族文學》2008年第6期。
中篇小說《陽光穿過我們村莊》,發表於《廣西文學》2008年第10期,獲第六屆廣西青年文學獎。
中篇小說《我們的逃跑》,發表於《花城》2009年第3期。
中篇小說《黎明掛在樹梢》,發表於《星火》2009年第4期。
中篇小說《像彩虹奔跑》,發表於《民族文學》2009年第5期。
中篇小說《最後的夜晚》,發表於《廣西文學》2009年9、10期合刊,獲廣西文學“最具潛力新人獎”。
中篇小說《致蔡先生》,發表於《廣西文學》2010年第3期。
小說集《陽光穿過我們村莊》,2010年由廣西民族出版社出版,2011年獲廣西少數民族創作“花山獎”。
中篇小說《徒步上北京》,發表於《廣西文學》2011年第3期。
短篇小說《游在岸上的魚》, 發表於《廣西文學》2011年第3期。
中篇小說《別看我的臉》,發表於《邊疆文學》2012年第3、4兩期合刊。
中篇小說《沒有腳的鳥》,發表於《民族文學》2012年第8期。
長篇小說《故鄉在別處》,被列入中國作協2012年重點扶持作品項目。
中篇小說《誰遺忘了我們》,發表於《廣西文學》2013年第2期,並被《小說選刊》2013年第3期“發現”欄目重點推出。
作品散見於《花城》、《星火》、《民族文學》、《廣西文學》、《邊疆文學》、《佛山文藝》等文學刊物,有被《小說選刊》選載,有入選《華語新實力作家作品十年選》、《廣西侗族小說選》等文學選本,著有中篇小說集《陽光穿過我們的村莊》,長篇小說《故鄉在別處》被列入中國作協2012年重點扶持作品項目。2007年中篇小說《明天,我年滿十六歲》獲第五屆廣西青年文學獎,2008年中篇小說《陽光穿過我們村莊》獲第六屆廣西青年文學獎,2009年中篇小說《最後的夜晚》獲廣西文學“最具潛力新人獎”,2011年中篇小說集《陽光穿過我們的村莊》獲第四屆廣西少數民族創作“花山獎”。
相關評論
作家楊仕芳來自侗族聚集地三江,是我最看好的廣西青年作家之一。從他歷年發表的作品來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的敘事才智直追廣西文壇的“三劍客”,然而,作出這樣的預期和評判,是就其藝術潛質而言的。而要達到“三劍客”在國內的影響力,被納入文學史家的視線,楊仕芳自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楊仕芳中篇小說集《我看見》
楊仕芳中篇小說集《我看見》
 楊仕芳中篇小說集《我看見》
楊仕芳中篇小說集《我看見》楊仕芳曾對我說,《誰遺忘了我們》這部小說是他在看了我對“三劍客”的評論後寫下的轉型之作。但從敘事上看,他沒有模仿東西,也未步鬼子後塵,更無論李馮了。如果說他從前輩的創作中汲取到某種稱之為“靈感”的東西的話,依我看,很可能是他在認知事物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上,有了更為宏大的審美訴求。《誰遺忘了我們》讓我們看到了楊仕芳區別於其他青年作家的某種另類的個性。看來,他已經厭倦於那種純粹寫實的筆調,而是代之以荒誕的形式。但荒誕形式並不能掩蓋文學敘事中現實主義的再生力量。小說中的荒誕感,來自作者對生存的思考,對現實的發現。那種文字的穿透力,讓讀者感到,作者似乎看透了人生,也許對楊仕芳來說,只能藉助一種變形的方式,才能足以呈現這種人生。
鄉村教師是楊仕芳最為熟悉的人群。也許是因為作者自身的鄉村教書生涯,使他更願意把關懷的目光投向這個邊緣的群體。《誰遺忘了我們》這部作品的主人公“我”也是一名鄉村教師,身份之低微,讓他與一切好事察肩而過。但作者所關注的焦點並不在生存的苦難,而是對自我靈魂的追問。
掩卷而思,小說對自我的拷問,及其所引發的現實追問,不能不說還存在有待提升的空間。在敘述的中途,擺脫與現實的“親密接觸”,轉向靈魂的曲折與駁雜,或許,楊仕芳就會擁有另外一個世界。
—— 王 迅 (廣西知名文學評論家)
人物訪談
閱讀是一種心靈放飛
記者:在你眼裡,怎樣才算好的小說? 小說集《陽光穿過我們的村莊》
小說集《陽光穿過我們的村莊》
 小說集《陽光穿過我們的村莊》
小說集《陽光穿過我們的村莊》楊仕芳:我無法用某種標尺來衡量什麼是好小說壞小說。對於任何一部小說作品來說都是仁者見智。我能肯定的是每個人的閱讀期待值不一樣,好小說和壞小說之所以產生緣由於此吧。我覺得對於小說的喜好是與個人成長經歷和閱讀經歷有關。我相信宿命,死亡和悲傷在我的記憶空間中盤踞著很大的位置,所以我在閱讀當中更多地選擇那些帶有悲情色彩的小說。我在這種小說中能夠找到自己的經驗和記憶,痛並快樂著。我無法判斷這種小說是不是好小說,然而我喜歡這樣的小說。它們將像一把刀具一樣切開生活表層,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種可能,也就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質。
記者:小說家應承擔什麼樣的社會責任?
楊仕芳:說到社會責任感,我覺得更應該歸於政治家身上。誠然,小說家自然也該有自己的責任,應該站在思想的前沿,鑄造民族精神和靈魂,以藝術的形式承載著歷史和社會發展的思想。
記者: 有理由相信你的創作受到了一些作家的影響,這種影響有可能還很深,你怎么看待在創作中模仿與超越之 間的關係。
楊仕芳:我的創作受不少作家的影響,尤其是余華、馬原、莫言等作家。我是從模仿開始,那如同看到別人在建設房子,也跟著建,結果卻發現怎么建都不如意,也就是說結果發現自己建設的房子沒有了存在的價值,因為建得再好也只是別人的模仿品。終於明白模仿的結果只是在用別人的語言寫別人的小說,唯獨沒有自己。於是我開始想到了區別,構建區別於別人的房子。於是我重新審視自己,挖掘內心裡的期待和渴望,以自己的目光去看世界,理解世界,解剖世界,把自己的觀點樹立起來,終於有了自己的文章。誠然,我是無法用超越這個詞語來形容自己的寫作。
記者: 一般年輕作家在寫作之初,習慣從切身經歷入手。從你的作品當中卻看不出多少你個人生活的痕跡。仿佛 你更多是從自己熱衷的命題引發開去進入某種寫作狀態的,這種寫作方式勢必更有賴於你的想像能力,你是怎么處理經驗與想像這樣一個在寫作史上恆久的命題的?
楊仕芳:事實上,我的小說寫作也是從切身經歷寫起的,只是我在生活當中找到那么的一個點、一個片段,然後就以此為支點向縱深、橫向不斷延伸,努力抵達事物的核心。也就是說我創作的想像是站在經驗的基礎之上,而當想像推至某個層面時,會引發二次經驗提醒。我沒有刻意去掩蔽切身經歷,只是從經歷當中引發出來的想像,把我的思想和敘述引向了遙遠,從而在某種程度上促使經驗和想像的融合,也就看不出明顯的個人生活痕跡。
記者: 你寫了不少“少年”的小說。在這些小說里,歷史似乎從未出現過,有的只是日常生活場景的細緻展現, 但給讀者的感覺卻是真實的。應該說你非常巧妙地彌合了歷史與日常生活之間的裂隙,這樣微妙的處理是否隱含著你某種獨特的歷史觀?為什麼關注少年?
楊仕芳:在創作中,我的好幾部小說選擇以少年的視角來推進敘述,是因為那樣能更好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受。我覺得世界在少年的眼裡是單純的,生活在少年的眼裡是平和的,而歷史在少年的眼裡是明亮的。正因為如此,那些隱藏在生活表層下的陰暗和陷阱就能產生更大的閱讀誘惑。讀者的目光可以穿越少年的敘述身份而看到那些事物的表層之下的種種美好或者醜陋的本質,從而進入了自己的審美渠道。這種閱讀效果能夠喚醒讀者的某種經驗,使之體味到另一種真實和記憶。這是我在努力偏離歷史的重荷,但事實上,在那些單純的少年敘述者身上卻暗藏著種種歷史隱喻。
記者:你已經從學校走出這么多年,你如何了解當代學生的變化。你如何寫出這種變化的真實?
楊仕芳:我離開學校已經五年多了,也許是因為當過老師的緣故吧,我一直關注著教育,關注著學生成長,尤其是農村的學生。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給農村學生的價值觀、人生觀、榮譽感、成就感等等帶來的種種衝擊,書本上的說教已經顯得蒼白無力,使他們陷入了迷茫和困惑。在某種程度上,鄉村老師也一樣陷入了迷茫和困惑。這種迷茫和困惑,事實上是一種精神缺失。我是通過這種缺口進入關於學生題材的寫作,努力逼近真實。
記者:讀你的作品,能感受到八十年代“先鋒派”的影響,你如何看待他們之後的寫作轉向?這種轉向對你目前的寫作是否有某種提示作用?
楊仕芳:曾有一段時間,以馬原為主的八十年代先鋒派小說作品讓我著迷,我也嘗試過那樣的寫作。後來,先鋒派小說家基本轉向寫實,形成了整箇中國文學的發展趁勢。誠然,於我來說,這種轉向的提示作用是明顯的,我一樣在努力回歸寫實,回到踏實的地面上或者厚實的記憶里,努力讓作品接近我內心裡的真實。
記者:讀過你的《最後一個夜晚》這篇小說,寫得很好,能談談嗎?
楊仕芳:這個故事緣於我的一段親身經歷,也就是說這個故事有我很大的影子。那是我剛從學校畢業到山區里教書,城市和山區的巨大落差向我劈頭蓋臉而來。在這個被山樑圍困的村子裡,文明和落後、現實和嚮往、善良與無奈等等在無盡上演。這樣的村子在山區里存在著千千萬萬。很多時候善良的人們面對生命和生活感到無比無奈,終於使他們變成另一種無知和無情。而這種變化在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今天,又似乎是那樣無懈可擊。小說中的主人公在拯救生命的過程中,事實上是在尋求一種精神的突破口。這是一直困擾著我,而最終寫下這個故事的初衷。
記者: 有評論文章提到你的作品體現了當下寫作的一種趨勢:對日常生活的關注。我個人的閱讀感受是,你的作品更多揭示了人們隱秘的生存狀態。之所以有這種感受的差異,恐怕涉及到對現實生活的認知問題,你是怎么理解現實或者說日常生活的?
楊仕芳:是的,我的寫作更多的是關注人們隱秘的生存狀態。我常常在那些最不起眼的日常生活當中看到一些不尋常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往往會引發我向更遠處思索。這些思索使我看到生活的另一種現實真相,其結果有時候是幸福,有時候卻是痛苦。這些幸福和痛苦是我對於現實和日常生活的理解所至。也就是我的理解是建立在那些日常生活的表層之下。
記者:在我看來,戲謔和解構構成了你作品的總體面貌,加之酣暢淋漓的語言表達,這使得讀者在閱讀你作品過程中充滿了快感,但讀後又不免覺出一種虛無和茫然,還有很多讀者說看到最後還是看不懂你在說什麼。你的寫作姿態是不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楊仕芳:在所有的小說創作中,我總是按照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去書寫作品,很少在意讀者的閱讀感受,或者說很少因為讀者的閱讀習慣而改變自己的寫作初衷,也就是說我的寫作姿態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是的,這個說法很正確,我也樂於接受。我的努力就是為了走向生活的厚度和深度。很多時候,生活應該怎么樣,誰也沒有答案,而很多讀者又往往喜歡在作品裡尋找到這樣和那樣的答案,尋找生活的答案。那是一種閱讀習慣,但是我走了回來,在更多的時候把生活的原本展現出來,也許是疼痛,也許是無奈,也許是無望和絕望。這是一種殘忍。但是我沒能說服自己在小說中寫下生活的答案,生活沒有公式,也沒有固定的答案,只有細心的讀者才會發現自己想得到什麼,應該得到什麼,怎樣去得到什麼。這也許是我的小說與別人最大的不同之處。我的小說難以讓更多人接受的原因也在於此吧。
記者:說說你心中的文學語言?
楊仕芳:小說是一種語言藝術。小說是建立在語言之上的。對於小說來講,語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篇小說的質量。我更願意閱讀那些充滿張力而富有節奏的語言。我的小說語言也是努力往這方向走向遠方,並將會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影響我的創作。
記者:以前,一個人很愛讀書,是件很平常的事,但現在說一個人愛讀書,會讓人覺得很不合時宜,你怎么看?
楊仕芳:是的,當今社會已經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時代,讀書很難直接轉化為經濟利益,所以讀書已經是不合適宜這種說法有其道理。但是我認為如果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喪失了讀書功能是件很可怕的事。我無法想像一個喪失了讀書功能的民族是什麼樣子。
記者:你覺得讀書對一個人的一生很重要嗎?怎么養成良好的讀書習慣?你喜歡看什麼書?你經常看的有哪幾類書?
楊仕芳:關於讀書,我能肯定的是對於一個寫作者的一生是十分重要的。讀書習慣的養成是建立在喜好基礎之上的。我是喜好文學作品的,也多半閱讀文學作品。在我並不豐富的閱讀中,我更多的是閱讀現當代小說。
記者:一直以來,人們說讀書是求知。而現代人更多地強調讀書是消遣,是休閒,是娛樂,你認為讀書是什麼?
楊仕芳:閱讀對於不同的人來說,需求是不一樣的。現代人更多地強調讀書是消遣,是休閒,是娛樂,促成了快餐文化的興盛。這是無可厚非的。對於閱讀者來說,如果閱讀快餐文化能夠使他(她)感到快樂,就沒必要去閱讀那些讓他(她)感到深奧而難受的文學作品。閱讀是自由的,是一種心靈放飛。我認為讓心靈在寬廣的陸地上、大海上飛翔,遠比在一堆垃圾上自娛自樂幸福百倍。
記者: 看你的作品一篇又一篇地推出,並且很多都是精品,作為作家的你同時還身兼三江縣文聯副主席,你如何處理工作、寫作與生活間的關係?
楊仕芳:我於2007年才開始發表小說,至今寫了十來箇中篇。工作壓力和生活壓力太大,沒能找到釋放的地方,後來就學會用小說來減壓。在某種意義上,小說成了我平穩生活、工作和寫作之間的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