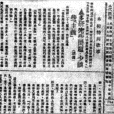“問題與主義”之爭發生在上個世紀初,不僅僅是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之間的一次對於中國未來之路的碰撞式的爭論,而且也一直影響到了並將繼續影響著中國的歷史脈絡。時值今日,“問題與主義”依然是需要國人深深思考的難解的習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問題與主義”之爭
- 時間:1919 年6 月
- 人物:胡適
- 文獻:《每周評論》
事件,胡適,李大釗,
事件
1919 年6 月,《每周評論》主編陳獨秀因散發愛國傳單被捕,胡適接任了該刊編輯工作。7月20 日,胡適在第31 號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勸說人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因為“‘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在該文中,胡適還嘲諷說:“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
胡適文章發表後,首先是研究系的藍公武在《國民公報》發表《問題與主義》一文與之商榷,著重從哲學的角度闡述了“主義”的重要性。不久,在家鄉避難的李大釗也致信胡適談了一些意見,後者為它加了《再論問題與主義》的標題登在《每周評論》第35 號上。在這篇文章中,李大釗首先針對胡適“少談些主義”的主張明確聲明:“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的”,“布爾扎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接著又指出:宣傳理想的主義與研究實際的問題是交相為用、並行不悖的,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社會上多數人的共同運動,而要有多數人的共同運動,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理想、主義作為準則,所以談主義是必要的,如果不宣傳主義,沒有多數人參加,不管你怎樣研究,社會問題永遠也沒有解決的希望。
針對胡適反對“根本解決”的改良主張,李大釗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闡明了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尋求解決的革命主張。他指出:“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庭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沒有生機的社會,“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針對胡適反對階級鬥爭的觀點,李大釗強調:階級鬥爭學說是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內容,要解決經濟問題,就必須進行階級鬥爭,進行革命;如果不重視階級鬥爭,“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
李大釗此文刊出後,胡適又在《每周評論》第36 號上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繼續闡明自己的觀點。而他撰寫的《四論問題與主義》剛在第37 號排版,《每周評論》就被北洋政府查禁,“問題與主義”之爭遂告一段落。
“問題與主義”之爭是一場發生在新文化陣營內部的、具有學術辯論形式但在內容上又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爭論。它事關如何解決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根本方法,反映了二者指導思想上的分歧。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並不是一場純粹的學理之爭,將之視為一次政治論爭更為妥當。
胡適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 少談些主義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么?”
“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我看了這種訊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麼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主義來欺人。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計畫,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裡。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裡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嘆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個是過激黨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有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許可權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那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為什麼談主義的那么多,為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么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徵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甚么樣的結過,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輿論家,只可算是鈔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子了。民國八年七月。
再論問題與主義
李大釗
適之先生:
出京的時候,讀了先生在本報31號發表的那篇論文,題目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發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與先生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現在把他一一寫出,請先生指正!
一、“主義”與“問題” 我覺得“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係。因為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那么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即是一種工具)。那共同感覺生活上不滿意的事實,才能一個一個的成了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不然,你儘管研究你的社會問題,社會上多數人,卻一點不生關係。那個社會問題,是仍然永沒有解決的希望;那個社會問題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響於實際。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並行不悖的。不過談主義的人,高談卻沒有甚么不可,也須求一個實驗。這個實驗,無論失敗與成功,在人類的精神里,終能留下個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減。從前信奉英國的Owen的主義的人,和信奉法國Fourier的主義的人,在美洲新大陸上都組織過一種新村落、新團體。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組織了一個“新村”。這都是世人指為空想家的實驗,都是他們的實際運動中最有興味的事實,都是他們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繼承者集合起來組織一個團體在那裡實現他們所理想的社會組織,作一個關於理想社會的標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這新社會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實現世界的改造的計畫。Owen派與Fourier派在美洲的運動,雖然因為離開了多數人民去傳播他們的理想,就象在那沒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種子的一樣,歸於失敗了。而Noyes作“美國社會主義史”卻批評他們說,Owen主義的新村落,Fourier主義的新團體,差不多生下來就死掉了。現在人都把他們忘了。可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永遠存留在國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幾百萬不曾參加他們的實驗生活,又不是Owen主義者,又不是Fourier主義者,只是沒有理論的社會主義者,只信社會有科學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還有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猶尚儼存。這日向的“新村”,有許多點象那在美洲新大陸上已成舊夢的新村。而日本的學者及社會,卻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說:“他們的企圖中所含的社會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來信也說:“此次東行在日向頗覺愉快。”可見就是這種高談的理想,只要能尋一個地方去實驗,不把他作了紙上的空談,也能發生些工具的效用,也會在人類社會中有相當的價值。不論高揭什麼主義,只要你肯竭力向實際運動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對的,都是有效果的。這一點我的意見稍與先生不同,但也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這是讀先生那篇論文後發生的覺悟。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復如是。他那互助友誼的精神,不論是科學派、空想派,都拿他來作基礎。把這個精神適用到實際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在清朝時,我們可用民主主義作工具去推翻愛親覺羅家的皇統。在今日,我們也可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軍閥的勢力。在別的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班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儘量套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代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這可以證明主義的本性,原有適應實際的可能性,不過被專事空談的人用了,就變成空的罷了。那么,先生所說主義的危險,只怕不是主義的本身帶來的,是空談他的人給他的。
二、假冒牌號的危險 一個學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恆至不為人讀,而其學說卻如通貨一樣,因為不斷的流通傳播,漸漸磨滅,乃至發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難分清。亞丹斯密留下了一部書,人人都稱讚他,卻沒有人讀他。馬查士留下了一部書,沒有一個人讀他,大家卻都來濫用他。英人邦納(Bonar)氏早已發過這種感慨。況在今日民眾運動的時代,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多半是民眾運動的隱語、旗幟,多半帶著些招牌的性質。既然帶著招牌的性質,就難免招假冒牌號的危險。王麻子的刀剪,得了民眾的讚許,就有旺麻子等來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葉得了民眾的照顧,就有汪正大等來混他的招牌。今日社會主義的名辭,很在社會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會主義,跟著發現。這種假冒招牌的現象,討厭誠然討厭,危險誠然危險,淆亂真實也誠然淆亂真實。可是這種現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開荒的時候,有些雜草毒草,夾雜在善良的穀物花草里長出,也是當然應有的現象。王麻子不能因為旺麻子等也來賣刀剪,就閉了他的剪鋪。王正大不能因為汪正大等也來販茶葉,就歇了他的茶莊。開荒的人,不能因為長了雜草毒草,就並善良的穀物花草一齊都收拾了。我們又何能因為安福派也來講社會主義,就停止了我們正義的宣傳!因為有了假冒牌號的人,我們愈發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實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免得阿貓、阿狗、鸚鵡、留聲機來混我們騙大家。
三、所謂過激主義 “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同人,談俄國的布爾扎維主義的議論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運動、交學運動,據日本“日日新聞”的批評,且說是支那民主主義的正統思想。一方要與舊式的頑迷思想奮戰,一方要防遏俄國布爾扎維主義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的。當那舉世若狂慶祝協約國戰勝的時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勝利”的論文,登在“新青年”上。當時聽說孟和先生因為對於布爾扎維克不滿意,對於我的對於布爾扎維克的態度也很不滿意(孟和先生歐遊歸來,思想有無變動,此時不敢斷定)。或者因為我這篇論文,給“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煩,仲甫先生今猶幽閉獄中,而先生又橫被過激黨的誣名,這真是我的罪過了。不過我總覺得布爾扎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不可一味聽信人家為他們造的謠言,就拿凶暴殘忍的話抹煞他們的一切。所以一聽人說他們實行“婦女國有”,就按情理斷定是人家給他們造的謠言。後來看見美國“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這話果然是種謠言,原是布爾扎維克政府給俄國某城的無政府黨人造的。以後殿轉傳訛,人又給他們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報發表的俄國的新憲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幾篇論文,很可以供我們研究俄事的參考,更可以證明婦女國有的話全然無根了。後來又聽人說他們把克魯泡脫金氏槍斃了,又疑這話也是謠言。據近來歐美各報的訊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無恙。在我們這盲目的社會,他們那裡知道Bolshevism是什麼東西,這個名辭怎么解釋!不過因為迷信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人把他譯作過激主義,他們看“過激”這兩個字很帶著些危險,所以順手拿來,亂給人戴。看見先生們的文學改革論,激烈一點,他們就說先生是過激黨。看見章太炎、孫伯蘭的政治論,激烈一點,他們又說這兩位先生是過激黨。這個口吻是根據我們四千年先聖先賢道統的薪傳。那“楊子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邏輯,就是他們唯一的經典。現在就沒有“過激黨”這個新名辭,他們也不難把那舊武器拿出來攻擊我們。什麼“邪說異端”哪,“洪水猛獸”哪,也都可以給我們隨便戴上。若說這是談主義的不是,我們就談貞操問題,他們又來說我們主張處女應該與人私通。我們譯了一篇社會問題的小說,他們又來說我們提倡私生子可以殺他父母。在這種淺薄無知的社會裡,發言論事,簡直的是萬難,東也不是,西也不是。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那些貓、狗、鸚鵡、留聲機,儘管任他們在旁邊亂響;過激主義哪,洪水猛獸哪,邪說異端哪,儘管任他們亂給我們作頭銜,那有閒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決 “根本解決”這個話,很容易使人閒卻了現在不去努力,這實在是一個危險。但這也不可一概而論。若在有組織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個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機會,馬上就可以用這工具作起工來。若在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已閉止,任你有什麼工具,都沒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機會。這個時候,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就以俄國而論,羅曼諾夫家沒有顛覆,經濟組織沒有改造以前,一切問題,絲毫不能解決。今則全部解決了。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可是專取這唯物史觀(又稱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第一說,只信這經濟的變動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於他的第二說,就是階級競爭說,了不注意,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就能實現,也不知遲了多少時期。有許多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者,很吃了這個觀念的虧。天天只是在民眾里傳布那集產制必然的降臨的福音,結果除去等著集產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點的預備也沒有作,這實在是現在各國社會黨遭了很大危機的主要原因。我們應該承認:遇著時機,因著情形,或須取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而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活動才是。
以上拉雜寫來,有的和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異,已經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當,請賜指教。以後再談吧。
李大釗 寄自昌黎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