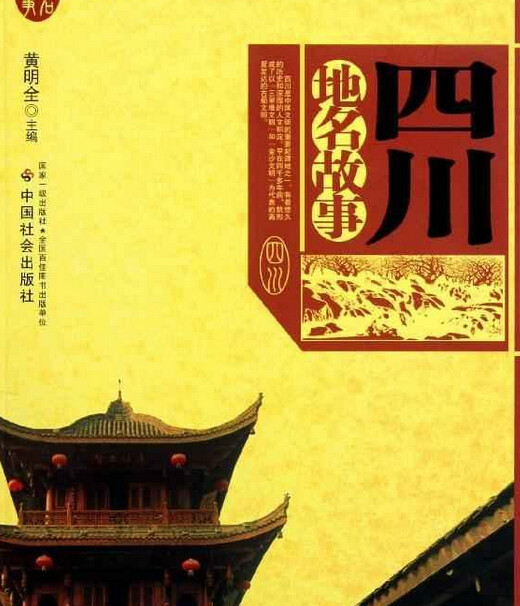基本介紹
事變背景,舉措,改革,影響,事變經過,事變原因,事變結果,
事變背景
巴塘是康區南部重鎮,地處四川西部川、滇、藏三省區交界地,為川藏大道咽喉。元以來為土司統治地方。明代一度為麗江木土府所轄。明末青海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入據康區,派第巴(又稱營官)駐巴塘、里塘,徵收賦稅。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派三路大軍入藏,驅逐禍亂西藏之準噶爾部,四川永寧協副將岳鐘琪率兵2000為先行,擒斬里塘第巴達哇蘭占巴等,巴塘第巴喀木布投降,和碩特蒙古勢力退出康區。清政府在巴塘設立糧台(又稱軍糧府),以縣級官員充糧務委員(簡稱糧員或糧務)負責輸藏的糧餉轉運,兼理地方土司、政務。又設駐防都司、專汛千總各1員,專司台站文報;外委1員,負責稽查金沙江渡口;以流官例,任命當地土頭為宣撫使司1員,副宣撫使司1員(即所謂“巴塘正副土司”)管理地方,其下轄六品土百戶7員。②(註:雍正七年(1729),川陝總督岳鐘琪奏“巴塘、里塘正副土官原無世代頭目承襲,照流官例,開缺題補”。)
雍正四年(1726),勘定川、滇、藏邊界,巴塘正式歸屬四川省。至改流前,巴塘地方包括現今巴塘縣全境和西藏芒康縣的鹽井地區以及今得榮縣北部、白玉縣南部的部分地區。
巴塘地處金沙江河谷,海拔較低,氣候溫和,土地肥沃,是康區主要產糧區,素有“高原江南”之稱。因此,清政府在川邊興辦墾務時,首先選中巴塘作為試辦墾務之地。
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廷因“有人奏:川藏危急,請簡員督辦川邊,因墾設屯,因商開礦”,諭令四川總督錫良“查看情形,妥籌具奏”。錫良認為“惟巴塘土性沃衍,宜於種植。擬在該處先興墾務,需以時日,或期底績。至因墾為屯之議,未敢先事鋪張。商、礦兩端,目下更難大舉”。①(註:《清實錄·德宗實錄》[Z],卷519,第8—9頁。)清廷同意錫良所奏。於是,錫良命巴塘糧員吳錫珍、都司吳以忠,以“奉旨開辦,毋稍觀望”,責成巴塘正土司羅進寶、副土司郭宗札保和丁林寺堪布傲拉扎巴將擬交開墾之土地劃出“指實”,並勘定界址,供墾務專用。當時巴塘正副土司“均遵命具結”,“並無異言”,只丁林寺以“所管土地除牧場外,並無可墾之荒山荒地”,予以抵拒。吳錫珍等認為巴塘“三曲宗”已有其二贊成,“不患無其一,盡可次第辦理”,②(註: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吳錫珍、吳以忠:“巴塘土司會稟投具墾務切結”。轉引自梅心如:《西康》[M],“三曲宗”指巴塘正土司、副土司和丁林寺,三股勢力集團。)便開始招募墾夫在巴塘試辦墾務。
舉措
與此同時,新任駐藏幫辦大臣桂霖“條陳藏事三端”,提議在川邊地區招募土勇3000人,加以訓練,派往西藏“分起扼要,輪流換防”,並將駐藏幫辦大臣移駐於察木多(昌都),“居中策應”。清廷認為其“所陳辦法,不為無見”,③(註:《清實錄·德宋實錄》卷521,第13頁。)命錫良與駐藏大臣有泰和桂霖等“會商妥籌,奏明辦理”。於是在川邊開始了招募土勇的練兵工作。
光緒三十年(1904)六月,英國遠征軍在榮赫鵬率領下侵入拉薩,逼迫西藏地方政府官員訂立城下之盟的“拉薩條約”。達賴喇嘛逃到庫倫(烏蘭巴托),欲求俄援。面對英帝國主義加緊在西藏進行的侵略活動,清政府一方面堅決不承認“拉薩條約”,派唐紹儀為專使赴印交涉;一方面也感到“經營川邊”以“固川保藏”的必要,遂採納“經營四川備土司,並及時將三瞻收回內屬,以為藏援”的意見,決定將駐藏幫辦大臣移駐於察木多,並命新任駐藏幫辦大臣鳳全於入藏沿途“就近妥籌經邊各事”。由於川邊地方系川屬之地,為了鳳全能便利處理,光緒三十年八月清廷又頒布上諭:
西藏為我朝二百餘年藩屬,該處地大物博,久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脅番眾立約,情形叵測,亟應思患預防救補,籌維端在開墾實邊,練兵講武,期挽利權而資抵禦,方足以自固藩籬。前有旨命鳳全移駐察木多。西寧辦事大臣昨已簡放延祉。所有西藏各邊,東南至四川、雲南界一帶,著鳳全認真經理;北至青海一帶,著延祉認真經理。各將所屬蒙番設法安撫,並將有利可興之地,切實查勘,舉辦屯墾畜牧,寓兵於農,勤加訓練;酌量招工開礦,以裕餉源。目前所需經費,著會商崧蕃、錫良妥籌具奏。該大臣等均經朝廷特簡,才足有為,務即盡心籌畫,不 避艱難,竭力經營,慎重邊圍,用裨大局,庶付委任。功多厚賞,其共勉之。④(註:《清實錄·德宗實錄》[Z],卷534,第11頁。)
按照這一諭旨,清政府明確賦予鳳全“經理”川滇邊的職責。所謂的“經理”,即推行屯墾、練兵與招商、開礦等新政。因此,一些關於巴塘事變論著中認為鳳全因貪圖巴塘氣候溫和而滯留不入藏的說法,其實是一種誤解。鳳全在巴塘練兵、開墾等,原本是履行清廷給予的職責。
改革
其二是,將章谷改土為屯。光緒三十年(1904)八月,根據錫良奏請,清政府仿照懋功五屯成案,廢除章谷土司,設立爐霍屯,以州縣官充任屯務委員,兼管朱窩、麻書、孔撒、白利及東谷等土司,隸於打箭爐廳。“將土司原領銅印、號紙並即同繳銷”,形成“改土歸流”和“以流制土”的管理體制。此舉雖由錫良奏準,但實系出自鳳全之意。鳳全認為“籌辦川藏事宜,屯練實為急務,而爐霍適當川藏之沖。欲保前藏來路,當自經營達木、三十九族始;欲保川疆後路,當自經營新設爐霍屯始”。⑤(註:《清實錄·德宗實錄》卷537,第13頁。)他還準備將爐霍屯作為“屯練”的主要基地。並“將德爾格特(即德格)留土職,設漢官,並令沿途土司均受約束,聯為一氣”。這一舉措雖然給後來康北改土歸流打下了一定基礎,但也使當時川邊各土司心懷不安,擔心失去固有的權勢。
其三是,再次籌劃將瞻對收歸四川管理。瞻對(今新龍縣)地處康區中部,界於川藏南北兩條大道之間,清代歷為“邊患”。同治四年(1865),瞻對土司工布郎結侵擾大道,清廷命川藏兩地派兵合剿。亂定後,清廷將該地賞給達賴喇嘛管理,命其派堪布建廟化導當地人民。但瞻對人民不奉黃教,西藏地方政府派代本一人,率兵駐紮瞻對。之後,隨著清朝日漸衰落,西藏上層統治集團開始以瞻對為“跳板”,企圖侵占川邊備土司地方,引起川邊社會動盪不安。光緒二十年(1894),四川總督鹿傳霖提出將瞻對收歸川管,次第經營各土司的建議。清政府最初積極支持鹿傳霖的收瞻舉動,一度將瞻對收歸川屬。但後來因達賴喇嘛的請求和駐藏大臣文海、成都將軍恭壽的聯合反對,清廷又罷黜了鹿傳霖,將瞻對仍賞藏。光緒三十年(1904)英軍侵入拉薩,達賴喇嘛外逃後,清廷為經營川邊,再一次提出收瞻問題,命錫良與有泰、鳳全會商收瞻歸川問題。有泰因懼引起藏中動盪,堅決反對收瞻。鳳全為經營川邊計,則力主及時收回瞻對①(註:劉廷恕:《不平鳴》[M]。)。川督錫良“心無主宰,托諸空言”。②(註:同上。)清廷決定由鳳全於赴藏途中“就近辦理收瞻之事”。“鳳全檄令打箭爐文武,告諭三瞻,覘視向背”。駐瞻藏官則以“必俟藏中檄調,始肯離瞻”相拒。西藏地方政府聞訊後,一面“密諭瞻番,修備兵戎,嚴防碉隘,防川師之潛襲”;一面向清政府遞交“闔藏公稟”,要求瞻對繼續歸藏管理。而“關外土司喇嘛等,因瞻事風謠煽布,蠢起抗爭”,“里塘僧土竟敢要挾文武,逼釋盜匪,揚言瞻酋派隊圍犯里塘。”③(註:《錫良遺稿·奏稿》[Z],卷1,“復陳籌議收瞻折”。)在此情況下清廷對收瞻問題又猶豫不決起來。
清政府的這些舉措都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巴塘事件的發生。此外,在巴塘事變發生前,川邊爆發的“泰寧事件”也對巴塘事變的產生有著一定影響。
影響
泰寧又作泰凝,在今四川道孚縣協德鄉一帶。清雍正六年,因西藏不靖,清廷將七世達賴喇嘛移住於此,建惠遠寺供其駐錫,劃附近71戶人民歸寺屬,用以供養該寺。雍正十二年達賴喇嘛返拉薩後,此寺住持仍照例由拉薩三大寺委派,屬民逐漸發展到近百戶。河埡分為上、中、下三河埡,為泰寧寺屬之地,在雅礱江一支流岸,沿河多有金砂。清代以來,川邊金夫多有買通僧人私往淘采的,凡淘得者均須向寺廟繳納稅金。光緒年間金苗甚旺,寺廟收入頗為豐厚。光緒三十年十月,有商人向川省礦務局申請在河埡開金廠。鳳全和錫良想增加邊地稅收,便督促打箭爐廳準令商人開辦,並派官弁前往彈壓。由於金廠的開辦直接傷害了寺廟、僧人的利益,故剛一開辦,便遭到泰寧寺僧人率當地人民阻拒,雙方發生衝突,金廠被毀,金夫數人被殺。劉廷恕派都司盧名揚率綠營兵一哨前往鎮懾,又遭到當地人的偷襲,全部被殺。“瞻對藏官亦暗助泰凝寺為亂”,派出馬隊至道孚界上示威。
川督錫良聞訊後,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廿一日奏派四川提督馬維騏率兵五營進駐打箭爐,“相度事機,再行進發”。馬維騏三月中旬抵達打箭爐後,即逗留不前。三月十七日,錫良得知巴塘事變後,責命馬維騏迅速進軍解決泰寧問題,以便回軍征剿巴塘。四月十三日,馬維騏分軍三路進攻泰寧,“喇嘛即棄寺而逃”④(註:查騫:《邊藏風土記》手抄本,卷1。查騫,字介休,安徽懷寧人,光緒三十一年任里塘糧務。泰寧事件和巴塘變亂時他正在川邊,比較了解真實情況。)。泰寧事件雖與巴塘事變無直接聯繫,但由於此前打箭爐廳的駐軍均集中於應付泰寧之亂,忽視了巴塘方面亟待增添軍力的問題,以致巴塘兵力不足,鳳全被困後待援不至。同時,泰寧開礦,政府與寺廟爭利的情況傳到巴塘,對丁林寺等也必然會產生負面影響,進一步加劇了它們對巴塘開墾、練兵的反抗。
事變經過
鳳全,字弗堂,滿洲鑲黃旗人。以舉人出身,同治十二年捐官入四川。先後署理過開縣、成都、綿竹、蒲江等縣和崇慶州、邛州、資州、瀘州及嘉定府、成都府。光緒二十二年,川督鹿傳霖疏奏:“鳳全性情勁直,辦事勤能,治盜安民,立志向上”。光緒二十九年,川督岑春煊以“明決廉能,胸有經緯”奏請以道員留川補用,權成綿龍茂道。光緒三十年四月,清廷免去因“眼疾”一直逗留成都的桂霖之駐藏幫辦大臣職務,任命鳳全為駐藏幫辦大臣,賞給副都統銜。
鳳全在川既久,對邊藏危急情況早有風聞,尤其對鹿傳霖收回瞻對問題更深有感慨。一旦被任駐藏要員,亟思有所建樹。加之清廷對駐藏幫辦大臣許可權的提升,更使鳳全感到朝廷對自己的倚重,故“自蒙簡擢,感懷時局,激發忠誠,即有奮不顧身之慨”,急於建功立業,“所有邊外屯礦練兵事宜,無不殫心規劃”,①(註:《錫良遺稿·奏稿》“查明駐藏幫辦大臣鳳全死事情形折”。)於是不免產生操切之心。然而,鳳全雖然幹練,又勇於任事,但他為官的經歷都在四川內地,對川邊藏區了解甚少,對藏族社會文化、宗教十分陌生,卻又想下車伊始即刻對其改革,這就必然只能收到南轅北轍的效果,注定了其悲劇的命運。
鳳全被任命為駐藏幫辦大臣後,清政府令將打箭爐的阜和協的續備新軍右營歸其統帥,作為行轅本標之兵,並批准他另募土勇1000名訓練後帶領入察木多駐防。當時,右營管帶(營長)張鴻聲率部正駐防清溪(今漢源縣)。②(註:清末改綠營為續備軍,阜和協為續備右軍,共五營,分統陳均山率前營駐打箭爐,張鴻聲右營駐清溪(漢源縣)。其餘三營駐雅、邛、眉州。)鳳全入康時,該營因接防部隊遲遲未到,而未能隨行。鳳全只帶著經過警察學堂培訓的100名警察兵,於光緒三十年八月由成都起程。抵打箭爐後,停留約一個多月,一面與劉廷恕策劃收瞻之事,一面招募土勇進行訓練,準備帶入西藏。但最終只募到土勇200名,且素質很低,短期難勝軍事。十一月初,在清廷的催促下,鳳全只好令50名隨行之警察兵留下作教練,自帶50名為護衛,經雅江、里塘、巴塘一路向察木多赴任,命張鴻聲率兩哨隨後趕來里塘駐防,保障川藏大道安全。鳳全行至里塘後,又在當地招募土勇50名。十一月十八日,鳳全抵巴塘,見巴塘氣候良好,土地廣沃,且為川邊墾務首創之地,糧員吳錫珍等試辦墾務已一年,進展較順利,已初見成效。鳳全遂在巴塘住了下來,經營“勘辦屯墾”、“練兵”和“飭收三瞻內屬”等事,並向清廷提出“勘辦巴塘屯墾,遠駐察台,恐難兼顧,變通留駐巴塘半年,爐廳半年,以期辦事應手”的申請。③(註:《清實錄·德宗實錄》卷537,第13頁:“風全奏請擬經營爐霍屯事”。)雖然清廷不準所請,命他仍駐察木多,但他卻一直在巴塘住了三個多月。駐藏的欽差滯留在巴塘久久不走,難免引起當地人的猜疑,而鳳全在巴塘期間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更影響到寺廟、土司及駐瞻藏官的利益。
其一是擴大巴塘墾務的面積,招工開墾。鳳全到後見巴塘土地膏腴,即欲廣開墾地。他看中巴楚河谷七村溝茨梨隴一帶地方廣闊,於是招漢人開墾。丁林寺感到利益被侵,指其地為“神山不可動”,煽惑七村溝民眾請求鳳全停止開墾。但鳳全不聽,強行將該處劃作墾場。
二是在當地招募兵勇,實施訓練,作長久駐紮的準備。鳳全到巴塘後,又招募了100名兵勇④(註:劉廷恕:《不平鳴》之“辯誣說”。),命所帶警察兵帶領訓練,並準備半年後與打箭爐所練新兵合練。巴塘土司頭人和寺廟上層,對這么多兵丁駐紮在此,不能不心存疑慮,擔心威脅到自己對地方的統治。
三是限制寺院的僧人數目,令丁林寺將超編僧人清理出寺。光緒三十一年正月,鳳全以關外寺廟僧人太多,寺廟陰庇“夾壩”,肇亂地方,排斥洋教為由,奏請“申明舊制:凡土司地方,大寺喇嘛不得逾三百名;以二十年為期,暫停剃度。嗣後限以披單定額,不準私度一僧。其年在十三歲以內喇嘛,飭家屬領回還俗”。在清廷尚在“妥議”之時,他便迫不及待地“嚴飭土司、堪布,將大寺喇嘛令其各歸部落,另建小寺散住梵修”,聲言要限定巴塘丁林寺僧侶人數⑤(註:《東華續錄》[Z],卷191,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乙未“鳳全奏請限制喇嘛寺僧數”。)。鳳全直接打壓宗教勢力,從而激起寺廟僧侶的強烈反對。
其實鳳全要求清廷申明的“舊制”,是指雍正二年(1724)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條奏青海善後事宜十條中提出的“請嗣後定例,寺廟之房不得過二百間,喇嘛多者二百人,少者十數人,仍每年稽察二次,令首領喇嘛出具甘結存檔”等措施。該措施是因為雍正元年(1723)青海蒙古羅布藏丹津叛亂時,青海、甘南等地僧侶多有參與叛亂,“西寧各廟喇嘛多者二三千,少者五六百,遂成藏垢納污之地”,年羹堯為穩固平叛成果,防止寺廟勢力發展,因而提出限制寺廟僧侶人數之議。清廷當時雖曾批准此事,但實際上藏區各寺廟並未嚴格執行。不久,年羹堯被處死,此事更成流案。其實藏區黃教大寺實際人數多在千人以上,大大超過此規定。鳳全昧於邊情翻出這一併未兌現的“舊制”來作依據,希望按照“如此辦法,二十年後,喇嘛日少,百姓日增,何至比戶流離,緇徒坐食,有土有人之效,可立睹也”。①(註:《東華續錄》[Z],卷191,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乙未“鳳全奏請限制喇嘛寺僧數”。)雖然用心良苦,謀劃長遠,但卻不切合當時川邊藏區實際。孟浪行動,難免釀成禍端。
丁林寺坐落巴塘城中,是著名黃教大寺,在宗教上為拉薩三大寺的“子寺”,時有僧侶1500餘人,轄有四鄉小寺16座,在巴塘擁有很大影響力。早在鳳全到巴之前,該寺就因反對開辦墾務與巴塘官員衝突。鳳全到巴後,發現丁林寺氣焰囂張,當地政令常因其寺阻撓而難行,因而想採取壓抑其寺氣焰,削弱其寺勢力的辦法來鞏固政府的權威,為推行墾務等新政掃清障礙。恰好當時發生了一起巴塘法國傳教士蒲德元被劫案。雖然劫案發生在里塘地界,但鳳全風聞劫匪與丁林寺有關,遂責令“巴塘文武懸賞購線協拿,期於獲盜,究出(丁林)喇嘛寺勾通情罪,一併重懲”。②(註:同上。)此事雖未究出結果,但卻引起丁林寺對鳳全的怨憤。此時,鳳全又提出限制該寺僧侶人數的主張,使丁林寺對鳳全更加仇恨。鳳全由於不了解民眾的宗教感情和當地信仰習慣,在清政府尚未批准其限制寺廟人數奏議,也沒有充分地實施準備的情況下,卻“時常當堂對眾言道,每寺只許住喇嘛三百名,余則一千二百餘名即行還俗,如不遵允,定行誅戮”。③(註:劉廷恕:《不平鳴》,“巴塘番夷公稟”。)這就更加速激化了矛盾。丁林寺僧侶利用鳳全的衛兵均著新式陸軍短裝,戴大蓋帽,佩帶洋槍,與以往清軍著裝迥異的情況,造謠說鳳全“非大皇帝所派欽差,是洋人所派,將收我土地畜牧財產,傀送洋人。於是夷眾大嘩,群情鼎沸”④(註:據查騫:《邊藏風土記》“風都統全被戕始末”等書載,鳳全所帶警察兵按新編陸軍操典,訓練在巴、里二塘新募土勇。每日在屋頂吹洋號、擊洋鼓,鳴放所帶新式快槍,以顯示兵威。又聲稱不日調大軍來巴、里鎮懾。)。
其實早在二月中旬,已發生巴塘人民襲擊墾場的情況,但鳳全並未引起警惕,不但不耐心做民眾說服工作,反而一味只知彈壓。二月二十日,鳳全給錫良發電稱:“巴塘番匪出而擄掠,並聲稱阻止練兵、開墾等事,擾及近台。鳳全派勇追拿,道經喇嘛寺,詎敢施放槍炮,擊傷勇丁;始知番匪滋事,均由喇嘛主使。速調在爐營哨前往巴、里。”此後,⑤(註:《錫良遺稿·奏稿》第1冊,“奏報泰凝巴里番夷滋事片”。)二十一、二日,七村溝民眾在丁林寺僧侶的煽動下,焚燒茨梨隴墾場,驅殺漢族墾夫。二十八日,一些人沖入法國天主教堂,趕殺教民,焚燒教堂。法司鐸牧守仁與助手逃至副土司官寨避難。騷亂民眾聚集城內達三四千人,並斷駐軍水源、柴薪。二十八日傍晚,吳錫珍赴行轅稟告“情形吃緊,早為籌備”,鳳全才命“都司吳以忠,帶領新練土兵80名,駐紮轅外巡防,以助衛隊所不逮。正土司羅進寶、副土司郭宗札保各帶土兵數十名,均扎轅內保衛。吳錫珍帶領漢民,巡警街道,兼探訊息”。⑥(註:劉廷恕:《不平鳴》,“巴塘糧員吳錫珍:巴變經過稟”。)都司吳以忠帶弁兵數人在行轅彈壓時,被眾人指為勾結洋人的漢奸,當場打死。鳳全這時才感到驚恐失措。鳳全的欽差行轅原來設在巴塘糧台衙門,其地名喇嘛城⑦(註:又稱皇華城,原為清初進兵西藏時所築駐兵及屯糧之所,地廣數百丈,四周築高土牆如城。後來售給喇嘛寺作僧房,故稱喇嘛城。巴塘糧務衙門在其中。)。鳳全感到其地不安全,於二十九日凌晨將欽差行轅轉移到正土司羅進寶的官寨中。此時鳳全所募土勇大都逃散,只有警察兵保衛。不過,土司官寨牆高壁厚,又有衛兵持新式快槍把守,正副土司也同住寨中,外面的僧人、民眾雖然圍住,放槍示威,並未進攻。從鳳全當天發給劉廷恕的求援函來看,他只是要求“即刻選派熟練夷務能事哨弁,將全留爐衛隊勇丁50人率領,馳赴巴塘,以壯聲威而資鎮懾”。⑧(註:劉廷恕:《不平鳴》,“鳳都統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十九來函”。)說明鳳全當時對事態的嚴重性並沒有足夠的認識,只準備調50名衛隊來“威懾”。
但”巴塘宣撫司羅進寶與副土司郭宗札保預謀亂,久欲逐鳳全亟返爐關,興兵重來剿逆定亂。又恐嚇鳳:‘不亟出巴塘,番眾喇嘛必至扼險守隘,焚燒漢民,延及土寨,我輩受殃,大臣愈危矣!’”①(註:查騫:《邊藏風土記》手抄本,卷1,“鳳都統全被期戕始末”。)鳳全驚懼之中,無奈只得聽從兩土司意見,決定三月一日動身返回打箭爐。糧員吳錫珍此時住在頭人阿登之家,聞訊急忙趕來勸阻,請求鳳全留下來堅守,以待援兵。但鳳全不聽,執意要走。當鳳全一行50餘人行至離巴塘2里的鸚哥嘴紅亭子地方時,被早已埋伏在此的僧人和民眾衝出襲擊,鳳全及其隨行人員全部被殺。此前,匿於副土司官寨的法司鐸牧守仁等2人,見土司不可信,乘夜翻牆逃走,途中被殺。
吳錫珍因臨行時被馬踢傷,沒有隨鳳全回爐,由於其在巴多年,與當地上層關係較好,故留在城中,並未受到傷害。三月初二,吳聞知鳳全被殺訊息後,“趕緊請房主業巴阿登轉請正副土司傳集頭人,設法遣散民眾,將鳳全屍骸運回城內,趕做棺木裝殮,暫停昭忠祠內;都司吳以忠、委員秦宗藩等屍身,抬至城隍廟內,招雇木工陸續做棺裝殮;其衛隊戈什哈五十餘人,分埋數處”。當日午後,巴塘各鄉村民眾代表等向吳錫珍遞交了四份“公稟”,請他轉稟打箭爐廳劉大人和大皇帝。“公稟”上蓋了正副土司印信及各鄉村頭人圖章。“公稟”除控訴鳳全一切為洋人,全不顧百姓外,竟然宣稱:
此番原為國除害,實出無奈,求乞恩宥善辦,無生兵釁。如再有差派官兵勇丁進來,則眾百姓發咒立盟,定將東至里塘,西至南墩十餘站差事撤站,公文折報一切阻擋。甘願先將地方人民盡行誅滅,雞犬寸草不留,誓願盡除根株,亦無所憾也。②(註:劉廷恕:《不平鳴》,“巴塘糧員吳錫珍向爐廳稟巴變經過”。)
在遞交公稟的同時,土司與丁林寺堪布等已聯絡一氣,派人將“各處險要隘口及山徑小路均扼塞不通”,從而使打箭爐廳在事變發生後近半個月才知曉。
事變原因
鳳全被殺是清代歷史上自乾隆十五年西藏珠爾墨特之亂殺害駐藏大臣傅清、拉卜敦之後,第二次發生的殺害駐藏大臣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是:
一、清政府經營川邊藏區,推行一系列政策措施,必然會對藏區傳統的社會制度、人文環境造成一定的衝擊,直接或間接地損害到寺廟上層、土司的利益,難免引起衝突。當時康藏社會中的統治者是三大領主,即土司、頭人、寺廟(即三曲宗)。“三曲宗”之間雖是分立,但維繫著相輔相成、利益相連的關係,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當他們任何一方的權利受到侵犯時,總會聯合起來反抗。丁林寺在巴塘一帶擁有巨大的勢力,寺廟不僅有大量所屬的田地農奴,而且干預社會事務,掌控當地經濟。巴塘正副土司雖名為“流官”,實為世襲,其勢力在當地盤根錯節甚為深厚。土司要藉助丁林寺的宗教影響來維持統治,而丁林寺則需要土司政治力量的扶持。鳳全力主將霍爾章古土司改流,已經使川邊各土司感到危機,而在巴塘推行新政,壓制丁林寺勢力的行動,更不能不使寺廟與土司共同感到自身利益受損,從而促使巴塘三股勢力勾結起來進行對抗。同時,鳳全欲強迫寺廟接受規定人數,逼部分僧人還俗的舉措,也傷害了當地人民的信仰權利和宗教感情,容易激起僧人與信教民眾的不滿,為三大領主利用和煽動民眾的反對情緒提供了機會。
二、史實證明丁林寺上層是這一事變的主要發動者,而瞻對藏官是事變的背後推動者。丁林寺在宗教上隸屬於達賴喇嘛和拉薩三大寺,其行動往往與受西藏宗教上層影響不無關係。達賴喇嘛雖然逃亡庫倫,卻仍一直遙控藏事,指示噶廈反對清政府收瞻。在川藏官員中,鳳全是收瞻的積極倡議者和力行者,早為駐瞻對的藏官所仇恨。巴塘事變前後,駐瞻藏官曾揚言派馬隊圍犯里塘,拒斷官軍來援,顯然是為巴塘肇亂者打氣,讓他們感到有恃無恐。幾乎在巴塘事變發生的同時,阿敦子、鄉城、貢嘎嶺、鹽井等地喇嘛寺均相繼發生叛亂,都說明巴塘事變的背後有西藏上層統治集團的陰影。據《英國侵略西藏史》記載,英駐騰越領事李頓在蒐集巴塘事變情報時從某法國教士處得知,“兩年以來,四川政府不斷努力於巴塘一帶改土歸流之工作,而各喇嘛則強烈反對之”。巴塘事變前,“拉薩各大寺首領已密令巴塘及各地喇嘛盡殺藏邊漢人及歐人”①(註:榮赫鵬著,孫熙初譯:《英國侵略西藏史》[M],第23章。),可見巴塘事變的發生絕非偶然,丁林寺和土司實早有預謀,並受到西藏宗教上層和駐瞻藏官的支持或挑唆。
三、變亂主謀者利用了當時“仇洋”的情緒。英軍侵藏和傳教士憑藉不平等條約的保護深入巴塘等地傳教,在藏區人民心中激起普遍的“仇洋”隋緒。巴塘地方建有三處天主教堂②(註:巴塘城區一座,亞海貢一座、巴塘所屬的鹽井一座。)。光緒六年(1880),法國神父路過項達村,被憤怒的民眾打死。此後,又多次發生襲擊傳教士的事件。尤其是法國司鐸牧守仁來巴後,這種情緒更增。牧守仁原在瀘定教堂任司鐸時就有惡名,到巴後大肆發展教民,擴大教產,深受當地人忌恨。鳳全所帶警察兵全為新式警裝,與邊地習見清軍裝束完全不同。其裝備又都是洋槍洋號洋鼓,均當地所未見過。於是丁林寺與土司利用民眾的無知,造謠說鳳全是“洋人所派的假欽差”,來巴的目的是要將巴塘“盡歸與洋人管轄”。③(註:劉廷恕:《不平鳴》,“巴塘番夷公稟”。)
由於巴塘久為內屬之地,人民對“大皇帝”十分忠順,要想令老百姓起來公然反抗,甚至殺死“大皇帝”所派的欽差大臣,是十分困難的。何況鳳全所作之事,對廣大民眾尚無大的傷害。至於限制僧人人數一事,也還只在口頭上說說,實際上還未執行。因而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僅憑此是絕不敢起來造反殺欽差的。只有造謠說鳳全是洋人所派假欽差,才足以激起人們的仇恨,使民眾敢於圍攻行轅,殺斃鳳全。關於這點我們在巴塘土司和丁林寺炮製的“巴塘番夷公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該公稟中稱:
鳳大人隨帶兵勇人等到台,隨即吩諭教習洋操,學洋話,行洋禮做作,又私開漢夷百姓老幼男女人丁戶口名冊。……鳳大人與吳統領商辦,將巴塘漢夷百姓僧俗盡歸與洋人管轄是實。……百姓看透此情,故耳不揣有罪,一時錯亂,已將漢官二員及洋人一併誅戮。④(註:同上。)
從這一公稟的內容和口氣,都可以看出巴塘事變的主使者是丁林寺與土司,他們將發生事變的原因歸咎於鳳全“將巴塘漢夷百姓僧俗盡歸與洋人管轄”,顯然是荒謬不經的謊言,但卻道出了當時能煽動起這場變亂的藉口。奉命經邊的欽差大人將當地人丁戶口造冊,被說成是“私開”,更不能成立。因此,巴塘事件表面上雖帶有民眾反洋教的色彩,但實質上卻是巴塘三大領主為維護自身利益反對清政府新政的一次事件,大多數民眾不過是被“反洋教”的藉口所蒙蔽而參與。
四、巴塘為川藏咽喉,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但自乾隆以來200年間,其地承平已久,軍力馳廢,連兵營也賣給了喇嘛寺作僧房。乾隆以前,巴塘都司領騎步兵298人,土著騎兵60人,均系由川省綠營遣派。乾隆以後,大量裁減綠營戍兵數量,僅留隨營差遣馬步兵83名,由內地操營揀派,3年更換。其餘全為當地招募的土兵。土兵中還有40名歸正副土司直轄,這些兵除充衛兵外,主要負責台站文報的轉送和竹巴籠金沙江渡口的稽查。鳳全到巴所帶的兵只50名警察兵可用,其餘150名土勇均為新募的當地人,遇亂即散,因此巴塘變亂發生時,可用之兵不過百餘人,根本無法應付偌大巴塘各處的騷亂。另外,鳳全等人不顧力量單薄,企圖用武力彈壓,到形勢危及時才慌忙向打箭爐調兵。清代“自打箭爐至里塘8站,計程685里。自里塘至巴塘6站,計程545里”⑤(註:黃沛翹:《西藏圖考》,記打箭爐至巴塘站程。)。共14站,1230里。其間要乘船過雅礱江,翻越4座海拔4500公尺以上的高山。即使以最快速度,也要十來天,何況當時信息不暢。故待張鴻聲營準備出發相援時,鳳全等早已被殺。據查騫等熟知當時情形人的記述,騷亂發生時,當地人並未敢直接攻擊欽差行轅,只是聚眾要求風全離開巴塘。後來看到鳳全接連派快馬去調兵,卻久未見有援兵到來,於是更信鳳全是“假欽差”,故才敢於將其殺死。
五、鳳全個人的思想、性格、作風也促成了巴塘事變的爆發。鳳全在晚清稱為“幹員”。在川為官20年,以“治盜能,馭下猛”而聞名。為人執傲,剛愎自用,不善聽取他人意見,即使同僚、上司亦常頂撞,動輒便稱“你把鳳老子怎樣!”⑥(註:查騫:《邊藏風土記》手抄本,卷1“鳳都統全被戕始末”。)。加之鳳全久住內地,初到藏區,對藏族風俗文化缺乏了解,又有嚴重的大民族主義觀念,欲憑藉官威武力在藏區人民中樹立威信,平時“謾罵成性,接見夷目,率肆口無狀,或以吸淡巴菰(香菸)銅斗擊夷目首日:‘好戴爾顱頭!鳳老子早晚殺爾蠻狗!’聲色俱厲”。土司頭人怨憤難當,而他卻“毫不警惕,亦不設策預防”。①(註:查騫:《邊藏風土記》手抄本,卷1,“鳳都統全被戕始末”。)鳳全個人的這些思想作風,造成了巴塘人民對他疏遠與反感,形成民族關係緊張,從而為土司寺廟煽動民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鳳全經邊雖然以悲劇告終,但從當時川藏全局的角度來看,他不懼艱難,勤於任事,“籌劃經營,不遺餘力”,②(註:陳渠珍:《芄野塵夢》[M]。)在晚清時代官員中是很難得的。他所極力推行的開墾、收瞻、練兵及改土歸流、限制寺廟勢力等舉措,是立足於“固川保藏”,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維護國家統一的需要,是貫徹清政府“經營川邊,以為西藏後援”這一正確戰略決策的必然。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層面上看,這些舉措具有積極意義。只不過鳳全昧於邊情,對三大領主的反對估計不足,過於操切行事,才使其成為悲劇人物。因此,過去多將巴塘事變說成是“反洋教運動”和“巴塘人民的起義”,值得商榷。如果歷史地、辯證地來看,這一事件實質上是巴塘宗教上層和土司為維護自身利益,反對清政府新政,在西藏宗教勢力和駐瞻藏官支持下,利用民眾仇洋情緒和文化衝突而煽起的一場動亂。
事變結果
巴塘事變發生後,川藏震動,清政府立即令提督馬維騏率提標兵五營進剿,又命建昌道趙爾豐為善後督辦率兩營續進。同時命駐藏大臣有泰“審度事機,妥為安撫”,“曉諭藏番毋聽謠煽”。馬維騏於四月平定泰寧後,當即率部向巴塘進發。抵巴境後,偵知“前數日有巴塘派來喇嘛頭人於此調聚百姓,壘卡防守,暨見大兵前來,皆不願應戰,於前夜自行解散”③(註:劉贊廷:《趙爾豐奏議公牘》,卷1。)。並未像所具“公稟”那樣“甘願先將地方人民盡行誅滅,雞犬寸草不留”。因此馬軍沿途只遭遇幾次輕微抵抗。六月二十六日,馬軍順利地進入巴塘城,“擒兩土司而誅之”。以八閣堪布為首的倡亂僧人據守丁林寺。馬軍攻不進,以炮轟擊,大殿中彈起火,全寺焚毀。八閣喇嘛等被擒,餘眾逃往七村溝。馬派軍“分剿七村,斬馘亦不少”。趙爾豐於八月初到達巴塘時,馬維騏“已火焚丁林,馬踏七村”④(註:同上)。趙駐巴後,“麻多哇等七村以愚悍聽番僧驅使”⑤(註:《錫良遺稿·奏稿》第一冊,“匯保攻克巴塘泰凝出力員弁折”。),繼續頑抗。趙派兵三路進剿,血洗七村溝。巴塘事變始平。之後,趙開始清戶口,查地畝,規定糧稅,廢除土司,委吳錫珍代理地方一切事宜;委候補知縣王會同為鹽井委員,前往招安兼征鹽稅。
巴塘事變使清政府進一步認識到經營川邊,必須改土歸流,建立行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於光緒三十二年秋,任命趙爾豐為川滇邊務大臣,將土司地方一併改流,興辦屯墾、教育、開礦、招商、練兵等新政,籌建西康省。自此,趙爾豐以巴塘為基礎,開始了在康區全面“改土歸流”、籌備建省的行動。
巴塘事變發生後,清政府以鳳全“死事慘烈,深堪憫惻”,仿傅清、拉卜敦之例,於成都北郊建“昭忠祠”以祀,並賜謚“威愍”。⑥(註:見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賜恤鳳全上諭。)鳳全妻李佳氏是鳳全續娶,工書畫,有文采。鳳全死後她赴打箭爐迎回靈柩,督工建祠。她將鳳全之死怪罪於打箭爐廳同知劉廷恕的“遲不發援兵”,遂四處告狀,並寫成“蜚白”(類似傳單的一種公開張貼小字報)散布。川督錫良無奈,只好以“年老糊塗,幾誤邊事”將劉參革。劉任打箭爐同知多年,熟悉邊情,鳳全抵爐,諸事多詢其意見,本為知友。不意竟被牽扯丟官,心甚不平。故將當時鳳全、錫良的有關函電、指示和所知實情,輯成《不平鳴》一書,以辯其冤。其中雖不免有為己開脫之處,但也為研究巴塘事變提供了許多珍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