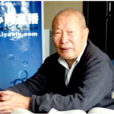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孟馳北
- 國籍:中國
- 民族:蒙古族
- 職業:記者、小說家
- 畢業院校:昆明大學
- 代表作品:《中國歷史新視角》(上、下卷)、《歐洲歷史新視角》等
人物簡介,社會評價,論孟馳北先生,孟馳北其人,認識孟馳北,閱讀孟馳北,苛求孟馳北,
人物簡介
孟馳北,原名們都巴亞。1926年生,蒙古族貴族後裔,內蒙古額濟納旗人。1947年在昆明大學(今昆明學院)參加學運,後赴蘇北解放區,歷任《蘇南日報》記者組長,《新華日報》工業組副組長,《雨花》編輯部小說組組長,《新疆日報》工業組副組長,《新疆畫報》編輯組長,中國文化大家、“草原文化理論之父”、著名記者、小說家。1955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說集《不沉的湖》,長篇紀實小說《新疆疏勒劫獄奇案》等。孟馳北歷時14年,完成了當今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草原文化和人類發展的恢弘巨著 《草原文化與人類歷史》(上、下卷),開創了人類草原文化學系統理論。此後,經過十年的研究,孟馳北先生再次推出70萬字的巨著 《中國歷史新視角》(上、下卷),更加完善了人類草原文化學系統理論,對重新審視中國歷史提出了全新的視角和認識論。年事已高的孟馳北先生又開始撰寫 《歐洲歷史新視角》,此書的完成,一個完整的草原文化體系將呈現給世界。他被國外華裔學者譽為“草原文化之父”。
社會評價
論孟馳北先生
吳華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理論處處長)
□他好似向我們推開了一扇從未打開的思維之窗,透過這扇窗戶我們看見了過去從不曾看見過的“文化景色”;他好似為我們架設了一條心靈的時空隧道,通過這條隧道我們能夠理解波瀾壯闊的過去;他好似為我們提供了一面直達心靈深處的“內視鏡”,藉助這面鏡子我們感受到人格深處的歷史烙印;他好似為我們建起某種“橋”,通過這橋能在不同文化模式間穿行。類似摩爾根揭示了遠古社會的“序”,達爾文揭示了生物世界的“序”,孟馳北先生揭示了古代草原社會的“序”。
□孟馳北先生精彩地分析了農耕文化與草原文化的衝突、混合對古代亞歐大陸一些區域文明興發的巨大作用,我都贊成,但對不同文化之間相互作用的機制如同化、順應、對抗塑造、浸染等,缺乏規範性的概括、表述。這方面的學術條件已經具備,只是需要跨學科的方法組合。
□孟馳北先生在草原文化領域已經實現基礎性的突破,需要拓展,需要有更多的學人、學科進入。期望更多的人閱讀孟馳北、傳播孟馳北、共享孟馳北、發展孟馳北。
孟馳北其人
孟馳北先生是個思想家。什麼是思想家?這顯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以為思想家有六個共性特質:一是具有淵博的“總和知識”;二是具有先進的思考方式和強大的思考力;三是具有以思考為人生最大趣好的人格特質;四是具有“思想勇士”的性格特點;五是具有豐碑式的思考成果;六是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和公認。以這些標準來衡量,我認為孟馳北是還需要進一步擴大影響、得到更廣泛公認的思想家。孟馳北的思想 孟馳北先生的最大貢獻是深刻揭示了草原文化的本質和各種外表的形態,深刻透視了草原文化的人格特徵,他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發現了遊牧民族和草原文化在歐亞歷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
他主要論說了些什麼呢?他提出的問題
“很長時間以來,人們都在想:世界有好幾個大洲,為什麼只有歐亞大陸創造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化輝煌而長久不衰?在歐亞大陸為什麼歐洲和亞洲在歷史上走著各自不同的路?為什麼歐洲和亞洲在文化上有這么大的差異?這個差異不僅僅表現在歷史的哪一個方面,而是表現在政治、經濟、法律、宗教等各個方面,是整體的差異。為什麼歐洲文化一直處在發展中,表現為不斷有質變的動勢,而亞洲竟在農業文化圈畫上了句號?” 他分析問題的基本範式是“6種文化形態論”
“對社會文化內蘊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生產樣式。從遠古到現在,大致上可區分出這樣幾種社會樣式:原始狩獵生產樣式、原始採集生產樣式、牧業生產樣式、農業生產樣式、商業生產樣式、工業生產樣式。與這幾種生產樣式相關聯,人類歷史長河出現過6種文化形態:原始狩獵文化、原始採集文化、牧業文化、農業文化、商業文化、工業文化。要解釋清楚人類歷史必須要研究這6種文化的生成與發展。”
“6種文化是從人類歷史整體說的,作為一個地區、一個民族並非都要經歷這6種文化。但是從當今世界各民族物質文化發展水平折射出一個巨大的差別來看,凡是完完全全經歷了這6種文化的民族在認識上與社會生活上就比較成熟,就站到了世界的前列,而沒有完全接受這6種文化的民族就表現出先天不足,只好尾隨歷史之後。” 他認為文化是一種積澱在人們心靈的 “集體無意識”,也就是“主觀範式”
“不同的文化形態表現為不同的生存方式,每一種文化在歷史上都有很長的時間跨度,幾千年、幾百年。在這個跨度內可以改朝換代,可以有政治權力交接的大變動。只要社會生產樣式不變,文化形態的經緯網路就不會變,生存方式的構架也不會變。人的生命在一定的軌跡里一次又一次地重複,形成一個常數,它對人就不能不留下心理積澱,形成集體無意識。這種無意識是人們認識客觀世界的中介和對外部世界信息進行加工處理的範式,在價值判斷、道德判斷和審美判斷上就表現出一種定向性,這種定向性形成一個民族的文化差異。” 他認為歐亞大陸所有民族幾乎都是遊牧民族和農業土著民族的混合
“公元300年到800年,日耳曼遊牧民族整部落整部落地向歐洲縱深推進,建立了許許多多王國,出現了人類歷史上最為壯觀的牧業民族與農業民族大融合,時間延續了500年,這就形成了今天的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義大利人。雅利安遊牧民族和印度當地農業土著達羅毗荼人混合,後來又有白匈奴和蒙古人混進,這就構成了今天的印度人。雅利安遊牧民族和伊朗的土著混合的結果,成了今天的伊朗人。北非的含米特遊牧民族和尼羅河三角洲務農的土著民族混合就成了埃及人,後來西亞的閃米特遊牧民族又侵入埃及,埃及人又有了一次新的混合。鐵的事實證明:中華民族同樣是遊牧民族和農業土著民族混合而成的。中國人自稱是炎黃子孫,炎黃兩大部落就來自西域。根據現有史料推斷,最早出現在新疆和甘肅的遊牧民族是雅利安遊牧民族,進入蘭州的塞種人和進入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都是操印歐語系語言的民族。說中華民族是雅利安遊牧民族和華夏農業土著民族的混血,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他用 “文明混合論”解釋歐洲和亞洲的歷史分野
“雖然歐洲和亞洲的民族都是兩種民族的混合,但混合的結果不同。遊牧民族帶著草原文化,農業民族帶著農業文化,兩種民族混合的過程也是兩種文化的混合過程。在歐洲,因為農業文化很脆弱,不能構成對草原文化強有力的同化,再加上草原民族不停地進入歐洲,直到13世紀,這種混合還在進行著,因此,草原文化就以強勁之勢保持著它的存在,形成歐洲自始至終的傳統。而在東方(特別在中國)則是另外一個樣子。因為有尼羅河、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印度河、恆河、長江、黃河、珠江、渭河,適宜於發展農業,農業人口很多,都創造了良好的農業文化,因此有很強的同化力。遊牧民族在軍事進攻中能取勝,而在文化上則被同化,雖然每次大的混合之後,農業文化都能獲得一定的活力,政治上出現新的局面,像埃及,在西克索斯人入侵以後出現過強大的王朝;中國在春秋戰國,各種民族混合以後出現了強大的秦與漢,南北朝混合300年以後,出現了強大的隋唐,但草原文化最終還是被同化了。”
“在歐洲形成了草原傳統,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則形成農業文化傳統。”
“東西方文化差別的根源就在於草原文化有沒有起重要作用。在東方,因為農業人口眾多,農業文化縝密完善,具有極強的同化力,遊牧民族可以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甚至奪取政權建立帝國,但在文化上卻是徹底的失敗者。再強大的遊牧民族進入東方農業文化網路後,就意味著把遊牧民族從原始初民身上承傳下來的、人類在數百年時間錘鍊出來的、能保證和大自然抗爭的心理層次的文化含量化為烏有,用農業民族心理層次的文化含量去代替。而在歐洲,農業人口稀少,農業文化底子本來就稀薄,又受到遊牧民族的頻頻破壞,一直建不起像中國那樣包羅萬象的農業文化體系,所以同化力非常差,牧業文化就不至於受到粉碎性的摧殘。那份從原始初民傳承下來的寶貴精神遺產就得以保存,它就使歐洲的歷史保持了創造的活力。”
“西方文化繼承了草原文化傳統;東方文化維持著農業文化傳統。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根源就在這兒。且不說抽象的理論問題,看看西方人現在的生活也能證實這一點。馬背民族愛吃肉食和乳酪,西方人也如此;馬背民族吃飯用刀叉,西方人也用刀叉(改進過的);馬背民族愛喝奶茶、奶酒、馬奶酒,西方人愛喝飲料;馬背民族愛用大碗喝酒,西方人用大杯子喝酒;馬背民族愛狗,西方人對狗有深厚的情感;馬背民族愛馬,西方人不論男性女性,連大家閨秀、名門少婦也愛馬……諸如此類的現象還可羅列許多,不從這種文化傳統上找原因就說不清東西方歷史發展和文化的差別。” 他提出了“人格文化論”
“牧業民族的草原文化主要不表現為物質、典章、制度和各種符號所記錄的思想成果,而是表現在他們的精神氣質方面,也就是他們的生活、行為、思想方式方面。正因為如此,也就受到史學家們的輕視。似乎草原民族除了歌舞和一些說唱史詩之外,其它幾乎是一片空白。草原民族從物質的豐富和各種符號積累的深厚方面雖遠不如農業社會,但絲毫也不能低估表現在他們身上的精神和氣質。”
“草原文化是動態文化,不停地變動。牧業文化是尚力的,遊牧民族形成力崇拜,特別是追求暴力。戰爭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娛樂,有戰爭的時候參與戰爭,沒有戰爭的時候就參加體育,體育是假想的戰爭,是在假想的戰場上與假想的敵人較量,使人處於高度戒備狀態,激勵人身上的活性精神元素。”
“農業文化是靜態文化,它千方百計要守住祖宗的經驗,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最簡約地表述了農業文化的思維框架。靜才能加深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靜才能積累整理前人的經驗,靜可使各種制度日趨規範化、合理化,靜把人的注意力收攏在生產技術上,使原始人的力轉化為技術形態,可以不斷推動社會生產力。文字的出現是人類破天荒的大事,語言可以在流動中形成,文字則必須在相對穩定的靜態環境中才能形成。”
“社會的靜態給人類帶來過巨大的貢獻,但當靜態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會走向反面,會成為人類歷史發展的重大障礙。維持靜態要扼殺創新,這樣就會形成頑固的保守心理。當保守觀念滲入到人的骨髓時,就會形成一種強烈的排異心理,對異質文化採取排斥態度,把自己牢牢封閉起來。在動勢中,人的固定關係不容易形成,今天形成的關係在流動中很容易破散。農業社會的穩定狀態是宗法血親制度得到了枝蔓糾結的發展,使封建社會有了牢靠的根基;靜態意味著權力行使系統不會停止和中輟,這樣就會使權力不斷膨脹起來,使庶民百姓承受越來越大的權力重壓;靜態也使權力和財富的分配定型化,富貴的總是富貴,貧賤的總是貧賤;靜態也能使一個民族變得愚昧起來。”
“學者們都忽略了理想人格模式塑造在歷史中起的作用,在歐洲經歷了神話人物塑造——史詩英雄塑造——騎士的塑造——紳士的塑造,這些理想人格模式都尚力,尚自由,珍惜愛情,珍視人的尊嚴,貫穿著草原民族的精神氣質。”
“而在中國則是清官——君子——名士——隱士——才子,這些理想人格模式都恪守封建倫理道德規範,都要嚴格遵守三綱五常,人的本性嚴重被扭曲,顯露不出人的本真。” 他提出了“文化信使論” “當原始初民分為農民和牧民兩部分後,務農的人就停止在歐亞大陸進行的大流動,在適宜於農業生產的地方構成大大小小的農業板塊。每個板塊都有清晰的邊際,這些板塊的空間都是固定的。人類選擇生存地點,不能按人的主觀願望,而是按自然條件。遊牧民族追逐的是水草豐盛的地區,而農民尋找的是適宜於農作物生長的地帶。這種地帶不可能是綿延千萬里的廣袤區域,總被山川、河流、森林、荒漠切割成許多小塊,每一個小塊就是一個封閉體。原始農業當然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封閉體與封閉體之間很少有社會聯繫。許多小塊封閉體組成一個大的封閉體,像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恆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錫爾阿姆河流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都是古代大的農業區,也是大的封閉體。大的封閉體之間要發生交往談何容易!即使大封閉體中的小封閉體之間也難交通。就是山前山後兩個村,‘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事還是很多的。文化是人的智慧的結晶,而人的智慧單靠自我開發是有限度的,它必須從他人身上吸取異質智慧因子。固然在一個封閉體中,有你我他三方的存在,可以從你他兩方接受異質智慧因子,但在同一個封閉體中的人,隨著文化認同的擴大,智慧因子的相似性也在加大,相似的智慧因子的撞擊就難產生出新質來。到了這時,人的創造活力就會枯竭。”
“如果信息體之間沒有信息交通,人類的進步就會十分緩慢,封閉體之間的創造就會各立門戶,極少有相似性。但從出土文物看,無論是陶器、青銅器、鐵器都是有相似性的。這種相似性的大小是和地域距離的遠近成正比的,距離越近,相似性越大;距離越遠,相似性越小。”
“就以彩陶文化來說,它所以能普遍存在於中亞、西亞和歐洲,自然是以狩獵和遊牧為主的人相互傳播的結果。”
“在歐亞大陸上,遊牧民族踩出了許多道路。在歐洲,他們翻越阿爾卑斯山深入到歐洲心臟地帶。在亞洲,他們表現得更英雄,阿爾泰山、天山、帕米爾高原、崑崙山、喀喇崑崙山、阿爾金山、喜馬拉雅山、祁連山、興都庫什山都沒擋住他們的去路。不說別的,光是辟出這些路沒有遊牧民族的勇敢無畏都是不可能的。正是靠著這些路打破了歐亞大陸的大大小小封閉體,使彼此都能吸取其文化的精粹。當時的中亞是連線東方和西方文化的中間地帶。著名的絲綢之路也是遊牧民族開闢出的傳播文化信息的道路。道路是溝通封閉體間的重要設施。道路又要探明水源、飲食、草料供給、住宿等輔助條件,這是一項艱巨的工程。正是靠遊牧民族前仆後繼終於辟出條道路,這才使文化傳播有了可能。遊牧民族的活動空間靠著道路的開闢不斷擴大,作為文化信息的媒體的功能也就更大。”
“有遊牧民族傳播文化信息是歐亞大陸獨具的優勢。美洲、澳大利亞、非洲都不具備這種優勢,所以他們就相當落後。在冰河時期的澳大利亞和西太平洋因為海水被阻於地極冰盆,海平面很低,有一批舊石器時代的人帶著舊石器時的文化來到了塔斯瑪尼亞島。他們屬於歐羅巴人種。因為他們處在絕對封閉狀態中,吸取不到一點異質文化的營養,人的智力不斷衰退,沒有一點創造的活力,永遠保持舊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物質生活水平永遠固定在一個刻度上,人口也繁殖不起來。1876年,最後一個塔斯瑪尼亞人死去,從此也就絕跡了。當澳大利亞土地上也因沒有遊牧民族用異質文化信息撞擊各封閉體,英國殖民者踏上這塊土地時,這兒的土著還生活在石器時代的階段。不知稼穡的南方猿人在更新世第一個冰河期以前就在非洲生活,那時,他們已經能用雙手製造一些簡單的石器,他們應算是人中的老資格,比亞洲猿人還要早,只是因為沒有強大的遊牧民族,所以文化遠遠落後於歐亞大陸。從這個對比中,人們不難看出遊牧民族在人類歷史上扮演著何等重要的角色。” 他提出了“文化轉型論” “牧業文化如果沒有發達的商業接替並予以發揚,日久天長自會淡化下去。在歐洲有著獨特的發展商業的條件,遊牧民族大批大批定居下來以後,對於在一個小天地內從事沉重而又乏味的農業勞動,他們從本能上是抗拒的,遊動已經形成他們的本性,固定在土地上當農民,他們承受不了,由牧民轉為商人就是合情合理的事。牧民的生活是流動的,商人的生活也是流動的;牧民需要冒險,商人也要冒險;歐洲的商人,半是商人半是強盜,牧民也是如此,因此,由草原文化發展為商業文化,這是很自然的。牧業文化繼承了原始文化的精髓,商業文化又繼承了牧業文化的精髓。也因為歐洲草原文化影響太強大,在代表農業文化的封建專制國家中,又出現了商業共和國,就在這些商業城市中釀造出完全適合商人需要的商業文化。高度發達的商業又為工業社會的誕生鋪平了道路,由商業發展為工業文化就成了順理成章的。因為有競爭機制和利益驅動,工業文化是更高層次上的動態文化,它最大限度地消化了牧業文化的精髓,成為最富有創造性的文化。”
“原始文化——牧業文化——商業文化——工業文化,在歐洲形成一個發展系列。這些文化有一脈相承之處,高揚人生命中的活性精神元素,唯其如此,它就能不斷創新,不斷發展。”
“農業文化的根本之點是要保持社會的穩定態,因此,它就要千方百計扼制人的生命中的活性精神元素,發揚人生命中的惰性精神元素。它尚德而不尚力。所謂尚德,就是對人的生命本性進行特殊的文化塑造,實際是一種扭曲。農業文化對人的塑造不外兩種途徑:一是運用宗教;一是運用倫理道德。埃及、印度是用宗教改造了人生命中的活性精神元素;中國則用倫理道德教化人的本性。在東方,這兩種方式都運用得很成功,人性被扭曲,惰性精神元素占了主導,人變得老實、馴服、忍耐、屈從,生命失去爆發力,像被閹割了一樣,大大強化了人的奴性。農業文化就成了終極文化,再沒向新的文化形態轉型。學者們在探討東方特別是中國何以未能進入資本主義工業社會這個問題時都未抓住問題的根本。” 他提出了他的“西域論”
“中國人被稱為炎黃子孫,而炎黃兩大部落就是來自西域的遊牧民族。《史記·五帝記》說:‘黃帝者,少典之子,黃帝居軒轅之丘’。《莊子·天地篇》說:‘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莊子·至樂篇》說:‘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郭璞注《西山經》云:‘葉日辛酉,天子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崑崙見於莊周、屈原等書,《莊子·大宗師》‘堪坯得之,以襲崑崙’。《屈原·九歌·山鬼》說:‘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屈原·離騷》說:‘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屈原·天問》說:‘崑崙懸圃,其居安在?’《史記·大宛列傳》引《禹本記》‘河出崑崙,其高二萬五千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者也,其上有醴泉瑤池’。《山海經·海內西經》說:‘崑崙之虛,……面有九井,以玉為檻’。《淮南子》說:‘禹掘崑崙虛以下地……珠樹、玉樹、旋樹在其西’。看起來,這絕非是純粹的神話,確有地理根據,崑崙山就是出玉之山,這肯定是從西域進入中原的遊牧民族帶去的,否則不會把玉和崑崙聯繫在一起的,而黃帝又和崑崙有聯繫,這證明黃帝是從西域去的遊牧部落。”
“西域曾是遊牧民族馳騁的地區,中原是農耕民族生活的地區,這兩大部落的民族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的生活樣式以及由此產生的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情感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也就是說各自具有有別於對方的文化。這兩個部落民族並不是各守自己的生活疆界,兩個民族經常衝突、融合,由此產生了文化混血和人種混血。這兩種混血都會在歷史上表現出來,世界歷史證實一點:凡是這兩種混血最多的地方,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
“中國歷史曾經有過的興盛衰亡的動因常常來自西域。這個歷史局面延續了數千年,直到鴉片戰爭,中國的歷史關聯才由西域轉向西方世界。新疆正式建省以後,西域的地理概念大大縮小,西域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也就淡化了。”
以上是我全部贊同或部分贊同的孟馳北先生的重要觀點,我所完全不贊同的就沒有列舉。當然這只是很概要的掃描,算是種“點擊”吧。
讀以上內容可能略顯沉悶。實際上,孟馳北先生的著述具象與抽象相結合,既深刻又妙趣橫生。比如,他講到“草文化”時有這么一段:“從草上就可看見中西文化的差異。西方文化是草原文化傳統,西方人對草表現了特殊的愛好,因為牛羊是吃草的,遊牧民族終年遊動,就是追逐水草豐茂之地,這種追逐成為西方文化的傳統,西方人走到哪兒,都要種草,草皮是西方人培育出來的,西方農村種草,城市也種草,西方的足球場、高爾夫球場都是草地,檯球桌上鋪的綠布也是草場的象徵。而中國因為是農耕文化傳統,農民是最恨草的,有草必除,有草必剪。農民對草恨到了這種程度:一定要斬草除根,對草恨得咬牙切齒。中國的文字作品中雖有‘奇花異草’之說,但在過去的公園裡,人只能見到花木,卻沒有草的地位。中國人從來不用草裝飾空間。種草皮、鋪草皮這都是從西方學來的。”
孟馳北先生總是從多種細節看到人格的塑形,從多種細節看到內在人格的閃現,從多種細節看到文明的內在本質及其分野。
認識孟馳北
我認識孟馳北先生是偶然中帶有必然性。
我長期研究人類“團結現象”,除了實際觀察,就是有目的有選擇地閱讀信息學、經濟學、文化學、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方面的書籍。其中草原文化、草原秩序、草原生活是缺頁,完全沒有體驗。
為了補這個缺頁,我讀了一些有關草原民族史方面的書,但我所想知道的書里基本沒有;請教過一些人,也不得要領。後來有幸結識現任自治區廣播電視廳領導的西林女士和她的丈夫道爾基先生,就向他們請教有關草原文化的問題。他們向我推薦了孟馳北,問我想不想見見。我心裡想:“社會科學對近現代的理解還說得過去,對農耕社會的理解就迷糊,何況草原文化,那就更迷糊了,誰要揭開草原文化的秘密也許應該給他諾貝爾獎吧。”我心裡這樣想,嘴上就說:“算了!”“算了”就是不抱希望了。這是2007年的事。
一晃到了2010年6月的一個星期天,我習慣性地逛烏魯木齊市的陽光書城,看到一套上下兩冊的書上寫著孟馳北著,由於西林、道爾基的介紹駐在我心頭,我就拿起細看,書名是 《中國歷史新視角》,直接翻到講唐代大詩人李白的草原文化人格和杜甫的農耕文化人格在他們詩中的體現部分,略讀之下,我對孟馳北先生把人格作為文化本質存在的視角深為贊同,對他的具體分析深為讚佩,其書的文學風格也甚合我意。
我把書買下來,四天看完。從封底介紹得知,孟馳北先生1997年就出了《草原文化與人類歷史》一書,我就到烏市各大書店查找這部書,只有陽光書城有一套,還被老闆自留不賣。我又托人找出版社,先說庫房裡有一套,後說沒有了。我找《新疆經濟報》社的吳卉女士,她說有一套,可以借閱。對我來說,讀書是精神的投入和心靈的再創造過程,需要邊讀邊在書上寫下我的看法,只借閱怎么行?我又托人到一心書店,也沒有了。我只好從吳卉那兒要了孟先生家的電話,直接向孟先生求書。孟先生說手頭沒有了,可以找一部。
一晃半個多月過去了,心裡惦記著《草原文化與人類歷史》,心像貓抓一樣難受。我就琢磨把吳卉那套先借過來讀,心想:“還不還到時候再說吧”。就在我向吳卉借書時,她說孟馳北先生給我找了一套,過兩天帶給我。
得到孟馳北先生的書後,讀之甚為歡喜,就思考如何回報呢?這種情況錢、物都俗而無用。直到臨近中秋節,我約朋友盧春萍女士到孟馳北先生家拜訪。我對孟馳北先生說:“你的書一百年、三百年、五百年後都有人研讀,會傳之久遠。”他只微微笑了一下,那自信是堅如磐石的。我說了些他的理論不完善的地方,他說:“你應該把看法寫出來”。臨走時我講:“你的書也許像《紅樓夢》一樣不朽呢!”我覺得孟馳北先生顯出有點自愧不如的表情。其實,各是各的事,不好比的,但從中可以看出孟馳北先生對《紅樓夢》的崇敬。
我是把自己、把所經歷的人和事放到文化大背景中去思考的那種人。過去我對20多年來在新疆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一些現象究之不解,甚至用了很多心理分析的方法思考仍不得要領。讀了孟馳北先生的草原文化論後明白,我身上也有草原文化,新疆人的人格中也帶有草原文化因子。有了孟馳北先生提供的新視角,我了解了大腦中的很多現象。
閱讀孟馳北
我一直以為中國的學術與中國歷史的悠久、文明的宏富、規模的龐大、崛起的影響很不相稱,讀了孟馳北先生的著作,我的看法有點改變。
我一直以為新疆是理想的學術之地。正如已故的季羨林先生曾經說過的:“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遼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新疆地區。從人類發展的遠景來看,對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義。目前研究這種匯流現象和匯流規律的地區,最好的、最有條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既然如此,這該是產生學術大師的土地。我一直以為我們現在的學術研究成果與此不相稱,讀了孟馳北先生的著作,我的看法有點改變。
這些年閱讀、思考新疆和新疆人,反覆看到這樣的文字介紹:“新疆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地區”,在講了“多”之後,就沒有與“多”有關的下文了。好像“多”是新疆的本質特徵似的。但公允的外國學者都不這樣看,比如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林凱特就認為:多種文化、多種宗教、多民族“充分交匯和融合”才是新疆文化的主要特徵。各種文化是如何交織、交融、包容、生成中國新疆地域文化、不斷塑造出中國新疆人性格的呢?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憑直覺,新疆跨境民族的境內境外部分有共性也有差異,主要區別在於境內部分是“中國化”了的。這種“化”,包括歷史上中原文化與當地文化、外來文化在這裡相互的“化”,更包括現實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這兒的“化”。同樣,新疆的漢族人與全國其它地方的漢族人也有所不同,原因也在於新疆的漢族人被新疆的各少數民族“化”過了。記得一次在上海參加短期培訓,幾個同學一起到餐館吃飯,聽到隔間很熱鬧,我們一起吃飯的一個同學說:“隔壁吃飯的是一群新疆人。”我們都說:“像!”。店裡的服務員說:“神了,你們怎么知道的?那是幾個在新疆工作過的上海人在聚會。”由這個細節可知,這塊土地上的多種文化確實在不斷發生著“化合反應”,這種“化合反應”生成的“複合文化”在不斷地塑造出“新疆人格”,這種“新疆人格”像空氣中的氧一樣,的確是我們每天都在呼和吸的。問題是:多種文化在新疆是如何發生“化合反應”的?讀孟馳北先生的著作對我們理解新疆和新疆人有極大幫助。
新疆各民族要在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共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就需要“解放思想”、需要“以現代文化為引領”。而“解放思想”、“以現代文化為引領”,都有個從哪兒解放到哪兒、從哪兒引領到哪兒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從傳統“解放”和“引領”到現代,從過去、現在引領到未來。對新疆各民族和所有新疆人來說,就是要適應時代發展,實現自我創新、自我更新、自我超越。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對我們的傳統實事求是地重新認識、重新評價,在廣泛吸收的基礎上進行再比較、再選擇、再建構、再提升。讀孟馳北先生的著作對我們認識新疆特性和新疆的文化轉型有極大幫助。
苛求孟馳北
苛求一下孟馳北先生如何?
誠然,孟馳北先生創作的《草原文化和人類歷史》等學術著作是里程碑式的。他好似向我們推開了一扇從未打開的思維之窗,透過這扇窗戶我們看見了過去從不曾看見過的“文化景色”;他好似為我們架設了一條心靈的時空隧道,通過這條隧道我們能夠理解波瀾壯闊的過去;他好似為我們提供了一面直達心靈深處的“內視鏡”,藉助這面鏡子我們感受到人格深處的歷史烙印;他好似為我們建起某種“橋”,通過這橋能在不同文化模式間穿行。類似摩爾根揭示了遠古社會的“序”,達爾文揭示了生物世界的“序”,孟馳北先生揭示了古代草原社會的“序”。
但是,個人,包括思想家、理論家們,在無限的自然面前,在60多億人構成的人類面前,在以無數意志相互作用為動力的社會演進面前,在由無數知名不知名的人們的貢獻匯成的知識海洋面前,局限性顯而易見。一個人的思維有多遠,他的思想局限性的隧道就有多長;一個人的“思界”有多大,那條思維的無形“限界”就有多大。苛求孟馳北先生不僅可以,也有必要。關於一個“基本命題”
孟馳北先生說:“對社會文化內蘊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生產樣式。”我認為這是片面的。馬克思多次講:決定一個社會的哲學、文學、法律、宗教、政治等上層建築的是社會的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一定社會的文明程度取決於這個社會生產和交往的發達程度。馬克思把生產和交往、把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一起講,是一以貫之的,是他思想和著作的一條紅線。馬克思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交往不是生產的簡單延伸,交往方式不一定由生產樣式決定,沒結合著的人就沒有人的生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制約、相互推進,猶如鳥之雙翼。以技術進步為例,既有生產技術,又有交往技術,二者相互依賴、相互轉化。生產工具的變革推動歷史前進,交往工具和方式方法的變革也推動歷史前進。人類的交往技術如道路、馬、馬車、汽車、飛機、輪船、文字、傳媒、貨幣、度量衡等技術的每一次進步都極大地提高了人類交往效率,極大地提高了知識、信息、文化傳播、貨物流轉、人員流動的效率,提升了社會共有知識和物質財富效用的數量和質量,也極大地提升著生產的效率。包括交往規則的創新、進步,都會極大地解放交往力,從而提升生產力。近代化、現代化、全球化就是從航海等交通交往革命引起商業革命進而引起工業革命,生產和交往的變革一路互補著走過來。中國的現代化不也是如此嗎?實際上,近代交通和傳播革命都首先是聯結技術和交往方式的變革,網際網路引起的變革首先是聯結方式的變革,整個服務業主要是聯結、交往業。可是,由於多種因素,我們一些教科書在闡釋歷史唯物主義時,往往單講生產力,不講交往力,講生產方式,不講交往方式,講生產和產業革命,不講交往革命。比如講技術進步的時候,如對度量衡技術進步之重要性不提或一筆帶過。講中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背景時,講鐵器的發明和在農業生產中的運用,不講它的另一個技術背景:即書寫技術這一交往技術的巨大進步。生產和交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一定社會文化的內蘊取決於生產和交往兩個方面的狀況。人們不僅在生產過程中塑造人工自然的同時塑造自己,而且在交往過程中彼此塑造著。生產樣式塑造文化,地緣文化之間也彼此塑造,外部輸入的文化還可能塑造出新的生產樣式。同樣是工業生產樣式,可能與計畫交往方式結合,可能與市場交往方式結合,這種結合的不同,會導致與之相聯繫的文化模式不同。同樣是傳統的農耕生產樣式,可能是古代中國占主導的小農生產方式,也可能是西歐中世紀的農莊生產方式,與之相聯繫的文化模式也不同。不僅如此,不同文化模式之間也不斷相互作用。比如,中國的地域文化 “楚文化”雖然不能離開楚地的生產樣式得到理解,也不能單從楚地的生產樣式得到理解。中國古代北方的關中、關東傳統文化既受著農耕生產樣式的塑造,也在與草原文化的交往當中相互塑造。宇宙萬物,不單自身是自身的根源,相互作用也是其根源,完整地說,事物內部的相互作用和外部的相互作用的結合才是事物的根源。事物不能僅從自身得到理解,必須在相互作用中得到理解。這一點,完全適用於文化。實際說,孟馳北先生的著作既分析了人與自然互動方式對人格的塑造,也分析了人類交往方式對人格的塑造,更分析了文化與文化相互作用中的相互塑造,他的分析是系統的、深刻的,但我總感覺他 “對社會文化內蘊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生產樣式”的表述缺少點什麼。
關於“理論基座”問題
建樓房要有地基,理論大廈要有基座。理論的基座就是理論的對象存在其上的那個基礎。由於人類從動物界脫穎而出?升上了新一層的發展形態,所以我們往往容易忘記我們本來是、一直是、也無法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就連我們創造的“文化”也仍然屬於一種“自然現象”。這種文化的空間大而言之在太陽系,小而言之不過是地球表面 “岩石圈”、“水圈”、“大氣圈”、“生物圈”、“社會圈”這“五個圈層”的相互作用。在這“五個圈層”中,“社會圈”具有主動性,但它是被其它“四個圈層”所無形支配的。直至今日,人類對於地質變動只能順應、無力改變,對氣候變化也主要是順應。所謂草原文明、農耕文明都主要是人類利用工具馴化、利用生物以滿足自己吃、穿、住、用、行等需要的文明,所謂工業文明不過是人類以大規模利用金屬和非金屬礦物為關鍵發展起來的文明。就是說,理解草原文化、農耕文化就必須理解人類馴化、利用生物的不同方式,要理解這種方式的不同,就必須理解地球上不同區域生物分布的差異及其根源。大致而言,是緯度、海拔、海陸關係三個要素決定著氣候(氣流、氣溫、濕度),主要是氣候決定著生物的分布。地質地貌的變遷非常緩慢,地質地貌變遷引起的氣候變遷、進而引起的生物分布的變遷也非常緩慢,人類對這種變遷是不知不覺適應的。遠古時期,例如距今15萬年前吧,青藏高原的抬升還沒有完全螢幕絕印度洋暖濕氣流的進入,新疆應該是沒有沙漠或只有很少的沙丘。在當時的人類生存方式下,西域應該曾經是亞歐大陸人類生存的 “相對好環境”。由於青藏高原的繼續抬升,使這片土地接受的暖濕氣流越來越少,中國的西部地區漸漸沙化。這個沙化過程導致的生存環境變差是西域這個一度的亞歐中心舞台的部落演員們向東亞、南亞、西亞、歐洲移動的原因之一,是我們的祖先炎、黃等部落(部落聯盟)東遷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由關中平原漸漸向東轉移的原因之一,也應是東亞中國農耕民族與草原民族的角逐、拉鋸唐代以前主要在西北、唐代以後轉移至華北和東北的原因之一吧。一個著名的歷史學教授說過:西北地區人口過載導致沙漠化是象徵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首都唐以後東移的主要原因,這是不成立的。在沙漠化過程中,人為的作用通常不超過10%,江浙地區人口密度那么高也沒有沙化吧。亞歐大陸中北部草原沙化的原因是青藏高原抬升屏障了印度洋暖濕氣流,和其它因素引起的氣候變遷,導致了植被減少。這種變化使亞歐大陸北部的草場退化,導致了遊牧民族相互之間爭奪草場的重心也發生了變化。不論還有多少自然因素,都是氣候變遷引起了植被變化,引起了社會文化重心的移動。當然還有重大社會原因,自然和社會原因是結合發生作用的。孟馳北先生講到中亞遊牧民族向東亞、西亞、南亞的大規模遷移,他沒提到促使這種遷移的動因,更沒提及自然因素對人的生存選擇無形而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巨大的。比如,生長較早的古代印度、埃及、巴比倫、中國四大農耕文明的中心大致分布在北緯28度至北緯38度之間。這四大早期農耕文明生長的條件有很多共性:比如都在亞熱帶和溫帶,都在落差較大的河流沖積平原,這些地方土質肥沃,用木製農具就能耕作。而歐洲由於較平,河流落差小,沒有形成適宜木製農具耕作的較大的肥沃沖積平原,加上歐洲大部分在寒帶和寒溫帶圈內,按其緯度來說,直到中世紀都可能延續草原遊牧生產方式,但由於受大西洋暖流的影響,那裡氣候比同緯度的其它地方氣溫高些,農耕生存方式和農耕文化也在中世紀發展起來。文明是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產物,人類的遺傳基因99.9%是相同的,差異的是生存環境。基本構造相同的人在不同的生存環境中與自然相互作用創造了不同的原生文明模式。孟先生講了人類不同生存方式的特質、相互影響及轉化,如果他提及導致早期文明劇本不同的舞台背景差異就更好了。
關於原生“文化的複合性”問題
文化從新石器時代就是“混合的”,那時 “採摘”、“狩獵”、“漁獵”、“種業”、“牧業”、“工業”、“商業”都是有的。打制石器由掌握了專門技藝的人完成,那就是“工業”。商業就更古老了。至於先後出現的遊牧社會、農耕社會、商業社會、工業社會,只是其中的“一業”占了主導地位,塑造了“其它各業”和整個社會文化的基本面貌。早期人類與自然的相互作用發生在相對隔離的種群與自然環境之間,就形成了各自獨特的文化。由於一些區域生存環境本身的多樣性,就使一些地域呈現出原生文化的“複合性特徵”。如亞歐大陸北部的腹地就是相對單一的遊牧方式和草原文化,但也並非沒有工商業,也不是一點沒有種植業。有些地方半牧半海,一半靠草原討生活,一半靠海洋討生活,兩個比重都較大,就會形成草原文化與海洋文化的原生性複合。有的地方,比如中國沿海某些地方就是半農半海的生存環境。有些地方,比如中國的川東、雲南、貴州、廣西等,屬於南方山地生存環境,由於地處南方,雨水、積溫較高,平壩、河套和山脊相間共生,那些地方傳統上就是農耕、狩獵和山林牧業的複合。當然,如黃河流域的關中平原、關東平原就是相對單一的農耕,由於與遊牧文化的衝突和遊牧文化的進入,當然也有遊牧文化的因子,但不屬於原生型的複合文化。從世界文化分布來看,希臘—羅馬—西歐的傳統文化是最典型的多元複合型文化。早期地中海國家都是原生性農耕、工商、遊牧文化複合類型,在其中有些國家的有些時期工商文化曾占過主導地位。比如,以擴張方式為例,遊牧民族對新擴張領土採取 “分封制”;農耕民族沒有向非農耕區域擴張的衝動,即便防衛性擴張後,也 “因俗而治”,只是要求象徵性地稱臣納貢就行了;工商民族的擴張方式是殖民,早期地中海沿岸國家強盛擴張時搞的就是殖民地方式,近代西方國家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搞擴張的方式更是建立殖民地。西歐即便在傳統農耕文化地位和作用最突出的中世紀,一些國家、地區的農耕、遊牧、工商所占比重也是大致三分天下有其一。大致說,天主教區(主要是南歐)的農耕因素更多一些;基督教新教特別是清教源區 (主要是西北歐)的工商因素多一些;東正教區 (主要是東歐)的草原文化因素更多一些。至於這些文化類型生成的原因需要很多文字才能敘述,此處不便展開。但很明顯,這種複合類型文化轉型的內在動力是強大的,內部積累性轉型是或遲或早會發生的事,在一定的外部條件下就會加速。相反,那些內陸腹地單一的草原文化和那些單一的農耕文化的轉型就比較艱難。遊牧民族的所謂 “動性”不是西歐文化從農耕文化為主導向商業文化、工業文化為主導轉型的根本原因。孟馳北先生從希臘文化中看到了草原文化的影響,那是對的,但地中海早期文化中農耕、工商、遊牧文化因素同樣突出,是典型的 “早期多元複合型文化”。比如希臘出現了早期精密科學,就是以工商經濟思維為動力的;比如希臘人給諸神都裝上翅膀,是很務實、很理性的工商集體無意識的體現,而印度、中國的種種飛天只要飄帶或練習騰雲駕霧的功夫就可以了,就虛一點,至於草原民族飛天的方式又為不同。實際上他們的這些區別源於他們的夢或清醒時的集體無意識,這種集體無意識源於生產、交往和生活的方式。坦率地講,孟先生用分析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法分析歐洲文化類型,沒有充分估計歐洲文化的原生多樣複合性質,是容易走偏的。
關於草原文化與海洋文化、工商文化“動性”的區別問題
孟馳北先生總講草原文化和海洋、工商文化都是動性的,因而草原文化容易向商業文化、工業文化轉型,而農耕文化則不能或不易轉型,實際不是那樣的。文化轉型固然有 “動性”因素的影響,但不是主要的。一個事物越是具有內在的多樣性、複合性,在不同外部條件作用下,它的轉化、適應的可能性空間就越大,反之就越小。一種事物之所以能向它事物轉化,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其內部本身包含了它事物的因子;二是一定的外部條件。文化轉型的動力也只能從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兩個方面去尋找。那些單一的草原或農耕生活方式都難以轉型。那些半農半海、半牧半海的生產、交往和生活方式在外部條件適宜時都容易轉型。特別應注意到,草原文化的動性與海洋文化、工商文化的“動性”具有性質的不同。草原人與農民不一樣的是,草原人騎在動物上動,在感受上大地沒有動;海洋人就不一樣了,水動、船動、人在動,都在動、始終動。更重要的是,在草原上動和在海上動需要的知識(特別是場景感受性知識)體系、技術體系和技能技巧大為不同,在古代知識更多是經驗形態的情況下,是很不容易相互學會的。例如,清朝大將施琅收復台灣時,那么多 “動性”很強的八旗兵到海邊都嚇得往後縮,還是靠福建海邊半農半海的農民出生的士兵們才把事情辦了下來。至於說到 “商性”,則另有根源,總之也不是由草原民族的動性轉化的。古代 “商性”民族或民族 “商性”的產生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在 “基本匱乏”、 “多元互補”、“多元破碎”、 “低交易費用”的特定條件下,人們的生活方式會商業化。在古代技術條件下同時具備這些要素的地域相對較少,在近代技術條件下整個西歐都率先具備了上述條件,所以 “商性”都蓬勃發展起來了。另一種情況是 “背井離鄉”生產商人。背井離鄉使人脫離人情交換環境、進入理性交換環境,古代中國農村的外來戶往往具有多一些的 “商性”;背井離鄉使人們必然從差異當中發現寶貴商機;背井離鄉迫使人們進入商業生活狀態,迅速學習商業知識、商業思維。 “商性”偏於實事求是、精於算計的性格,與工業思維都是最理性的性格,與 “牧性”的情感氣質相去甚遠。 “背井離鄉”使猶太人的商性、理性思維更早、更深入地發展起來,使他們的理性人格和理性思維發展程度更高,這是他們當中大商人、大科學家更多的歷史文化原因。至於西北歐的那些所謂帶著草原文化基因的人,他們不是單純的牧人,也不只帶了草原文化基因,他們本身就帶有商業文化、甚至工業文化的基因。不是“牧性”轉換成了“商性”,而是本身帶有的“商性”在一定外部條件下得到了選擇、發揮和放大。比如西北歐那些所謂遊牧民族都不是單純的遊牧民族,他們同時從事海上捕魚、海上搶劫、海上貿易和工礦業,他們本身早就帶上了“海性”、“商性”、“工性”,所以條件適宜時率先轉型了。關於“文化相互作用”問題
孟馳北先生精彩地分析了農耕文化與草原文化的衝突、混合對古代亞歐大陸一些區域文明興發的巨大作用,我都贊成,但對不同文化之間相互作用的機制如同化、順應、對抗塑造、浸染等,缺乏規範性的概括、表述。這方面的學術條件已經具備,只是需要跨學科的方法組合。祝願孟馳北
孟馳北先生在草原文化領域已經實現基礎性的突破,需要拓展,需要有更多的學人、學科進入。期望更多的人閱讀孟馳北、傳播孟馳北、共享孟馳北、發展孟馳北。謹以此文表達對孟馳北先生的敬意,謹以此文祝孟老幸福、健康、長壽。
(原刊於《新疆經濟報》社會科學版 責任編輯燕紅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