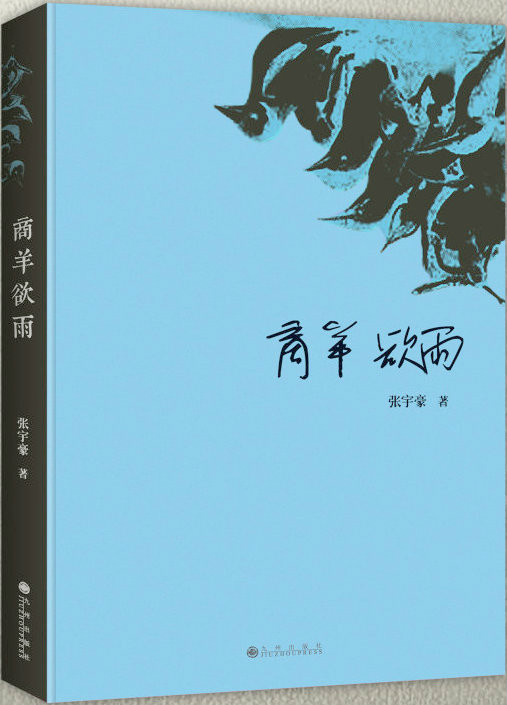本書起因於:景公十五年,商羊飛臨齊國,殘疾的、奇特的鳥是暴雨的預兆;二,《多刺的梨頭》中的老木頭人,中空的身體發出歷史的羅音,在曠野里日復一日的枯坐著。但這部長篇小說最深層次的肇因還在於——類似某位義大利當代作家所言,他想毒殺一位修士——而我,我想毀滅一個國家。
序
麻姑自云:三次目睹滄海變桑田,桑田百轉千回地萌發以滄海。
言時甚是雀躍,那螻蟻般的聽眾一聽(完成規定動作)懵了,我想,我就想,汗漫的時間是可觀的、可接納的、可推理而憬悉的,但可恥的“滄海桑田論”飽含毀滅的慾念:微笑著念出大物質的覆滅和重新來過,卻又滑膩地轉入了進一步蟄伏的狀態。
(表達清楚上述的心理機制多么困難)
《商羊欲雨》是我的首部長篇小說,成於2012年冬,在這時,寫了新小說《商羊欲雨》的人是名叫張宇豪的。方及明了起來,“歷”“史”這東西,長長的一段看上去也很短,短短的一段看上去也很長,十幾萬字的稿子們如今裝訂成冊,像棲息在銅柱子上的稀有鳥一樣開始啼唱啼唱著那曩昔繁華夢囈,唯獨保留所有的粗糙與真空。身為作者,嗯,蜿蜒的徜徉者,蟄伏者!——即我們時常在馬格利特的畫中窺見的打著雨傘的黑衣男子,——委實願意坦承,寫作並不快樂,哪裡有那么多快樂的事呀,它近乎遠古的巫者占卜,近乎造一面水晶鏡,鏡中之景紛紜複雜,交媾繁衍,鏡子是頑固的,它不動。頑固於它的不動。
然而,我們總可能錯(毫不掩飾),好壞,佳運實體。商羊欲雨?機率。
基本介紹
- 書名:商羊欲雨
- ISBN:9787510830075
- 頁數:256
- 定價:26.00元
-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4-7
- 裝幀:精裝
作者簡介

海報
少量的說,少量的寫,少許生活——我們久已感覺不到這是我們的生活。很多事情都已飽和了。
——《商羊欲雨》海報

目錄
2.王城
3.晏嬰
4.衛國馬戲團
5.廢太子
6.骨偶
7.楚巫來朝
8.露寢台
9.視察 10.鐵豬
11.盛大歌舞表演
12.納查夫人
13.擒象記
14.戰爭疾病
15.鹽鹼地
16.畿遇荒津樵夫
17.畿遇木頭人
18.齊魯之戰
19.畿遇孔先生
20.商羊欲雨
21.編年史家
22.春秋

本書起因於:景公十五年,商羊飛臨齊國,殘疾的、奇特的鳥是暴雨的預兆;二,《多刺的梨頭》中的老木頭人,中空的身體發出歷史的羅音,在曠野里日復一日地枯坐著。但這部長篇小說最深層次的肇因還在於——類似某位義大利當代作家所言,他想毒殺一位修士——而我,我想毀滅一個國家。
眾所周知(運用這擋箭牌似的中國成語),“離題”“對細節的窮究”儼然高居現代派文學的聖器室上:猶如青黑色的巉岩,以上兩者作為細微的裂縫構成了另一幅關乎一整片區域的地圖冊。本書的特點也在於離題離得特別多,對細節關注到了懵懂的程度,以文中的編年史家為例——對歷史一竅不通,卻洋洋灑灑;隱匿於時空的每一道罅隙之間(不知道誰膽敢藏匿這樣的人?)喋喋不休;是什麼?他是一顆空洞的大眼睛,左眨右眨,紋滿了紫羅蘭花飾的曲線與飄帶。
恐怕《商羊欲雨》會被形形色色的優劣讀者們視作Monster,但我希望它不是不能生育的弗蘭肯斯坦,而高貴地榮膺第一個沒毛的直立行走大猩猩的漿果勳章。絕對的,殘忍的作者把包裹在大青葉子裡的無數人物交給了同等殘忍的讀者,我不帶情感的語調整合了各人物參差的生命階段,但千萬勿忘,他們縱然死去,卻遠遠比愚笨的讀者活潑得多,他們洋溢著話語永動的青春。
我在堂·吉訶德式的謙虛之後,往往湧現出堂·吉訶德式的咒罵,我要說:小說是敘事的藝術。並非什麼“講故事”,或露骨的、近乎病態的自然主義筆調(此類自然主義的自然體現在外部尤為機械,在內部,則淪為虛假的意識流)。我念念不忘《不存在的城市》里這段驚醒了的句子:
身穿元朝官吏制服的馬可·波羅在大殿下滔滔不絕地講述著異域見聞,忽必烈想像著塔樓、紅屋頂、車水馬龍的街衢時,突然意識到這個外國人的漢語竟講得如此之好。
我之所以說“驚醒了”,有鑒於這段描寫所傳達出的精微心理轉變,應奉為圭臬。我們在分神遐思的片刻都更能觸及一種人的本體,總體——每個人都回到了思考的初始狀態,有著簡單的邏輯。無關忽必烈和波羅,《不存在的城市》固然深情地緬懷了叢叢簇簇的浮雲般豪華的城市,但當文中內在的筆鋒轉動時,這一種由馬可·波羅的敘說所帶來的分神,已鋪天蓋地,以幻化的姿態瞬間在聽者的頭腦中占據並改竄了一切,只不過,那個小說里唯一有資格作為聽者的人此時此刻竟也處於相似的分神狀態,他油滑地鑽出了夢的底層,像條比目魚,僅在這誰都未曾注意的一秒鐘,忽必烈安全地退回了內心,並反覆打量著那講故事的陌生客人,注意到後者與故事完全無關的普通人的特徵,“他的漢語講得如此好”。
不知怎么的,我就覺得(而且事實如此):這是講者與聽者之間友誼的開始。
敘事的藝術歸根結底是生活與思維的雙重抵達,是芒刺的撩撥,而想像力歸根結底是善的駐留。
那些譫妄著嘲笑所有小說式杜撰的現代蠻人必然棒喝任何改寫的渴望,並將在生活的河流中成為涸轍之鮒。(不是早已如此了嗎?)而語言,曾將人脫離物自體的混沌,將人從包圍他的物中間解救,或許在人越來越無所依憑的今天,也是自由的末日堡壘,所以我越來越警惕於無知之人、心懷叵測之人、昨日之人、明日之人對語言的污損,否則,這世界只瓜熟蒂落成一隻巨大的連體嬰兒,許多精神的卵殼在搖曳之前先學會了自我破裂。如果我們曾經費盡心力命名了世界的每一片葉、每一朵花,我們卻又將其自願地遺忘——拱手相棄,這是否就是“被驅逐”了?另一類看似聰明的處理辦法即指鹿為馬,好端端地自欺欺人,如此行事的結局是人既不再知道鹿,更不再知道馬。
每當我想要談嚴肅話題,就感到聽眾的稀缺。我能意識到一種在碌碌現實中大煞風景的存在,我知道普遍的平庸(承認了吧)狀態下激怒庸人的方法,我清楚極了徒勞無功的汗漫過程,也即“思維”,——夾雜在語言的抽絲剝繭里。如果我們有很好的聽眾,很配合的對話者,誰還惜乎寫作呢?“寫”是這樣踽然走來的孤獨症嗎,多說無益,多寫也無益,多生活也無益。
少量的說,少量的寫,少許生活——我們久已感覺不到這是我們的生活。很多事情都已飽和了。
一切問題都是心理問題,而文學是真的心理學。
不要試圖說什麼,不要去做什麼,只是待在原地,使出渾身解數地待在原地,盯緊自己,由腐敗的人群造成的障礙也必然在人群的腐敗中分化瓦解。我從來沒看見堅持自我的一丁點兒的困難。如果說身為作者的我但凡試圖說明什麼,那我率先想到的就是被說明之事必是先於我存在的,甚而我就是被它們創造的、構成的,寧是它們改變了我。——喔,分分合合的世界,巋然不動地經受著狂風暴雨般的說明、解釋和歪曲。
《商羊欲雨》歷盡歪曲。
《商羊欲雨》的結尾引用了維根斯坦的名言,他執著地認為邏輯學包含了某些神奇的倫理觀念,適用於日常罪錯,政治,和街角的閒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