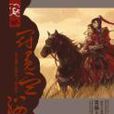現世中,空蕩的靈魂映出古老災難中的悲劇, 下決心的改寫, 殊不知在改寫之中,已經越陷越深,無法自拔, 最初的目的只是想要讓夏朝延續,否定奴隸制與獨裁集權,但隨後,面對這個垮台一般的世界, 需要一個象徵性的領導者, 改寫之人,也就登上了背負罪孽與罵名的皇位, 滔天的陰謀在坐定的一刻,依舊蔓延上剛剛重修未完成的堤岸, 皇權只會將真理帶入墳墓,在戰爭來臨之際,首先被摧毀的便是人權,葬送真理, 即使我不願意相信,皇權有別的含義, 我不干涉政治,只在民生和祭祀中,留下一個淡淡的疊影,讓大家相信我可以做到, 那便已經足夠, 政治家的謊言與虛偽是交織如麻的現實, 我卻單純的像是白紙, 軍事家的強權與尊嚴是風吹浪打的涸礁, 我卻懦弱的像是只能依附的青苔, 依附政治,卻不想去參與, 至少,我還不是墳墓里的代言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冠冕血纓魂
- 外文名:Tassel crown blood soul
關雪茗:不干涉的第十八位君主。
誕生花:銀丹草
花語:美德
她是唯一一個貫穿故事始終的角色,開篇滔天的戰火與悄然醞釀的陰謀,欲要侵蝕著每一位敢於鬥爭的志願者的神經,姒履癸,那個曾經背負了詛咒出生,卻被祝福著備戰的戰神,在女人和國家面前選擇了前者,前後的差距或許只是時間問題所能夠彌補,但既然如此,就等於將世界拋向了深淵。
她本是現實中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國中生,前世妺喜的靈魂,像是銀丹所散發的芳香將沉睡在地獄中的姒履癸喚醒,他是罪孽,陰謀於一身的不可接觸者,在佛教里,這樣的人需要上千年的沉澱,罪惡才能夠洗清,然而就在封印鬆動的那一刻,他又回到了人間,並找到了那個女孩,告訴她,想要活下去,唯有穿越到那個時代,改寫悲劇,那么一切都將會改變,連同中國塵封的歷史,也將一併改寫。
對此,她只有默默點頭,冒著被利用的危險在交換法器之餘,等於簽署了一份賣身契,她所不知道的是,這等於她永遠放棄了現代的便捷,而轉身向一個滿是血腥和屠殺的世界走去,一切的未知都在經歷了浩劫的夢魘甦醒之前,悄然展現。
好在她降落的時代,是全面戰爭爆發之前的南方,南方的寂靜,阡陌的光暈,她既然知道了世界的結局,又怎能甘願享受這份即將不再的美夢,她有她的使命,即使是身軀遭到毀滅,也要完成這一份根本不可能的任務,改寫夏朝的結局。
改寫之後,中國將再也沒有奴隸制,沒有被摧殘的文化,甚至不會有誤人子弟的儒家學說的出現,但這一切,僅僅在穿越的第一天晚上,她動搖了。
當眼見姒履癸殺人的血腥,她便已經好感不再,屢次質疑他的決定,而姒履癸,也與她保持著十分的疏離,不去理會這個沒有過去的女孩,但僅僅是因為好奇,他將她帶回了中原,帶到了自己身邊。
姒履癸有自己喜歡的人,又怎么能去喜歡一個身份不明的女子,他轉身離開的身影,讓雪茗感受到的,只有一份不被青睞的安心,和釋然,讓一個惡魔去喜歡自己,那便是萬劫不復的地獄,她知道,跟這樣一個屠夫,沒有好的下場,二人的距離越來越遠,幾乎沒有了平行的可能,而勾曜的出現,卻好似點亮了一盞明燈,那是救贖深陷囚籠的青鳥脫離苦難的燈火,為其,雪茗第一次與勾曜交談,便已經略有好感,一起徙倚在夕陽之下,攀談明日的故事,一起在祈禱的時候,訴諸幽思,對父母從未敞開的心聲,卻為了一個早已淹沒在歷史長河中的小人物而痛快敞開,歷史是冰冷而沉默的,即使眼前的人物再怎樣的澄澈透明而立體,那也是無用的徒勞,雪茗不願意這樣承認,即使是知道勾曜活不過二十,更不會成家,她也奮盡全力,去為改變這一個人的命運,而不斷努力著,只可惜,她錯了方向,挽回了一個無關緊要的人的性命,可誰知,這一次,她卻成功了,成功說服勾曜在自殺式之前放下屠刀,成功說服他感受到世界的美好,只是因為她愛他,而他,卻毅然決然為她斬斷了封建的枷鎖,義無反顧的,寧願放棄太守的高位,也要與她一併同行,她說他是自己的星星,是那顆在只有血腥屠殺瘋狂暴虐的世界中唯一的一顆看的見的星辰,但距離太過渺遠,身份懸殊,國家危難,使得兩個人始終的隔閡不斷,惡魔詛咒的摧殘,更是給這一份即將劃出深淵的愛情裂痕,更下了一把鋒利的斷箭。
她是那早春倉皇盛放的銀丹,宛如脫離線條的夢境在覺悟之時會幡然破碎一塌糊塗,太早太過的人生,在現代本是國中生做夢也想不到的早戀,在那個十五歲算成年,出生之前就定娃娃親的時代,這一切太過正常不過。
夏朝是剛脫離荒蠻時代的第一文明,它早早的盛放將能力全部灌注在人的啟迪,統治者往往頭腦活躍,不拘小節,大禹的後代宛如龍的九子,個頂個的不是省油的燈,這樣的社會開放,自由,儘管歷史書的描寫如此面目全非,那個時代,說起來,它沒有奴隸制,沒有想像中的那么可怕,但卻有數不清的敵人對中原大地虎視眈眈。
她就好像是塔羅里代表愚者的那張紙牌,即使是愚蠢也有她可愛的道理,帶著一股早春的倉皇,那股活蹦亂跳的新鮮勁,在傾頹的末世里,成為了唯一清新亮麗而簡約的風景。
她的存在,對這個國家可以說是驢唇不對馬嘴,從來沒有人去注意她的存在,除了兩個人,一個,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勾曜,另一個,是太史令。
太史令:雙重性格的美男子,一半魔,一半人。
誕生花:野薔薇
花語:你心知我心
他是具有兩面人格的美男子,天生如瀑布般的長髮,高挑的鼻樑,濃而炯炯的雙瞳,散發著中式男性最古老的美麗,本是風度翩翩儀表堂堂的艾陵城太守,一次公務之旅,他在中原因關龍逢臨時出差,而接手了這份工作,核查關雪茗的身份。
在第一次的見面,他便源源不斷的展示著自己的殷勤,嫻熟的倒茶,談吐不凡的風流,時不時的玩笑語氣,精巧華麗見多識廣的趣聞,對一個女性來說該是如何的迷人。
她感覺好像是找到了真命天子,卻不知道這是一個喪偶的中年男子,不怪她發現的太晚,也不是他隱藏的太深,而是,這份責任無法推敲和自拔,這份沉重的飄渺的看不見的責任,日益讓美男子逐漸消瘦,他只能一次次隱藏自己的欲望,卻依舊捨不得放開手中唯一的溫暖。
即使他發現她的偽造,也並沒有秉公執法,而是以權謀私,願意用自己的身份去隱藏她的一切,殊不知這種隱藏在日後卻成為了不信任因素之一。
太史令的雙重人格,每一重對她來說都是異樣的迷人,宛如在漆黑的夜路前方,路燈中的微笑,便是家的溫馨,她不顧一切的投入他做作的懷抱,不知道他雙重人格下,隱藏的到底是風流的韶華,還是支離破碎的噩夢。
他對她隱藏的,自己的真實身份,夏朝最大的武器世家太史世家,當時,哪裡有死亡,哪裡就一定有太史家的身影,他們不效忠任何組織,也不效忠任何信仰,只是用血腥謀取金錢,即使是挑撥離間也不過如此。
他是在最後的春天綻放的遲來的野薔薇,虛無縹緲的落日是他看到的唯一美的景色,那浮華瑰麗的天邊,留存的卻只有死亡的陰影,他是末世的高官,注定要為了國家喪命,他是國家的犧牲品,是姒履癸精心培養的殺戮機器,為扳回國勢的傾頹,欲要彰顯自己的衷心,他不惜與卡斯特簽訂契約成為半魔族,他曾心想在瘋狂之後了結自己的生命,這樣對國家來說也算是盡忠,自己無愧忠節,可誰知在全面戰爭爆發前一個月,他空虛的心卻被毫不相干的女人填了個一點不剩。
工作之餘他不忍心將這樣的女孩送到慎刑司逼問家境然後含冤處死,他希望能將她摟在身邊,存留著溫柔的氣息,將最後的慈愛統統送給了她,遞交愛情的信物在此時看來的愉快,卻在將來成為了不可逾越的障礙。
卡斯特的詛咒蔓延全身,痛苦讓心臟的負荷一度升高,無法感知心的溫度,這讓他如同套上了冰封的棺材,在棺材裡看到外面的美麗卻依舊無法觸摸,全身冰冷是成為魔族的必修課程,這對於那個只會殺戮的他來說根本沒有什麼,但對於那個女孩,他不忍心,不忍心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國家,而寧願奉獻給女孩。
他背負罪孽,背負毀約的懲罰,欲要殺出一條生存的道路,齒輪閉合的嘀嗒作響,還是將他推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當知道了自己的前世,那個相同的靈魂,竟然是卡斯特早已死去的弟弟,波呂克斯,他愚蠢的認同了卡斯特的觀點,以不傷害關雪茗的契約與他做了再一次的交換,被他改造成了戰爭機器。
在建國的那天,太史令頹然的從眾人的眼裡消失,轉身奔赴萬劫不復的黑暗深淵,他的赴約讓卡斯特明白了女人的重要性,此時的關雪茗本應隱姓埋名逃離卡斯特的魔爪,卻稀里糊塗的當上了女皇。
卡斯特當然不會這樣相信一個還思念著敵人的人,他派出了自己的親信奧契狄索斯,本以為這樣一個恐怖的九頭水妖能禁錮住太史令,可誰知奧契狄索斯早已對帕勒克氏暴政心存不滿,與太史令一同策劃了逆反的初衷,而被克法變成石像的卡斯特,囚禁在沒有自由的深淵,日益加重的仇恨蒙蔽了他的一切,他只能動用謊言的鼓動性,多數都已經是空頭的支票。
乾:沒有實體的靈魂,強行介入只有空蕩和虛偽的感情。
誕生花:冬紫羅蘭
花語:思慕
魔心:絕望之心
她本是在時空裂變中從關雪茗身體內分裂出來的不完全的靈魂,取代了關雪茗一部分的智力,卻不懂得感情,這樣的人只能在這個時代,被洗腦灌注思想,而她卻沒有被灌注那些殺戮,周圍的人,有幸是嚮往和平的兄弟姐妹。
在初冬第一場雪中誕生的冬紫羅蘭,猶如她那冰封一般的內心,滿是質疑的嘆息充滿了她的大腦,作為靈魂她很知趣的聽從主人的吩咐,聽從主人的任何話,卻在一次意外中,第一次動起了貪婪的欲望,也第一次有了心,她吸收了完顏肅台所有的元神,作為己用,從此有了主見和實體,也從此意味著有了牽掛。
冰封的心神,在第一次喚醒之後,已經有所醒悟,她擁有著和關雪茗一樣的相貌,只是更加清秀嚴肅和冷峻,不近人情的外表下,所隱藏的也是嚮往著自由和和平的心。
小卡斯特·斯庫里:浪子回頭。
誕生花:蘇格蘭松
花語:開拓精神
魔心:喜悅之心
他是沒有出身的分身,他遺忘了家室,遺忘了姓氏,甚至遺忘掉了一切可以追尋的東西,他是卡斯特為了方便而用黑血隨意捏造出來的分身,賜予了他和卡斯特相同的力量。
製造出來的他,沒有感官,沒有神經,沒有一絲感情,整天在鮮血橫肆之中執行著卡斯特交授的殺戮任務,不折不扣的惡魔的代言人。
九百多年如一日的殺戮,在他眼裡成為了過往的風景,他不記得自己殺了多少人,只是知道那些人都在恨著自己,也許還有別的,不過他根本不會在乎那些。
卡斯特的所有部下,都有兩個姓氏,賜姓斯庫里,和原本的形式,而分身已經忘記了自己本來的名字和姓氏,此斯庫里,其實是莫大的侮辱。
妖冶如狂風般的紫色長髮,像是高貴的馬鬢,血紅色的深深凹陷的瞳孔之中,除了憎惡與仇恨,似乎還有別的感情。
他本來這樣殺下去,就不會有後來的朝代,只可惜,命運在極端的邊落總是給人亦逆轉的奇蹟出現,也只有奇蹟,才能拉回迷失道路的罪子。
幽冥魔邪的父親,因觸犯了卡斯特的利益,被卡斯特批准討伐,然而卻沒想到,就是這件事情,讓小卡的靈魂,像風吹岩石,終有一天會鬆動一樣,將他與血腥絕緣。
幽燁,同樣也是殺戮無數的罪子,可即使是這樣的人,居然會為了保護自己的女兒獻出生命,給小卡演了一處沒有排練的偽劣的戲,本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局,卻有著最難以理解的感情摻雜其中,為什麼?明明是與自己並不相干的人,卻要這樣保護,沒有力量,不就沒有活下去的資格么?
從此,這種思想在他的心底動搖,他漸漸開始不相信卡斯特,卡斯特覺出了異樣,對於他來說,世界,還有分身,都是積木草草搭建的樓房,稍微不爽就可以一腳踢倒,重新組建一副自己喜歡的出來,他暗中計畫回收這個分身,可曾想就在他被復仇的幽冥魔邪催眠之後,小卡變成了一灘黑血凝固成了新的個體,對於他來說,那是第一次品嘗自由的味道,和血腥味不同,他願意將這種味道牢牢記在心底,並為自己過去的行徑感到慚愧,至少,這個世界還沒有糟糕到必須要毀掉。
在目送魔羅懷抱著不滿十歲的幽冥匆匆離去的那一刻,靈魂的蛻變便已經開始。
在他真的看穿這個世界之前,請讓我們一起相信,只要擁有信心和勇氣,陽光總會穿透黑暗,逝者會安息和轉世,而生者會品嘗到永遠甘甜而芬芳的自由的爽風。
幽冥魔邪:並蒂雙生子,卻有各自的逞能。
幽冥:
誕生花:大鶴望蘭。
花語:愛的音符。
黑的像綢子,靜的像是一灘墨綠色的潭水一般深邃的髮絲,柔美的順勢而下,天生遭遇詛咒的金色瞳孔,隱藏著讓人膽寒的魔力。
她是從早秋到初冬連開四個月的花朵,也只有大鶴望蘭,能忍受的住簌簌飄落的悲傷和寂寞,承受住寒冷和炎熱各不相同的溫度,無聲佇立在河邊,投下希望的種子,十年只為一次,轉瞬變作土灰。
大鶴望蘭,會站在低矮的河堤上,連續佇立上四個月之久,無聲無息,暗自準備著,像是少女小心翼翼的準備著珍珠項鍊一樣,它珍藏著的種子,是它送給河水的禮物,也是送給河水的祝福。
與鶴望蘭同一天出生的幽冥,亦是個喜歡逞強的孩子,她故作堅強的背後,籠罩著悲慘的家世和不順的歷程,風吹雨打十年一日,用自尊為衛冕內心的脆弱,亦在艱難險阻前毫不膽顫心驚。
建國之後,她一直在眾人看不見的地方作著自我的戰鬥,自我的反省,極力適應著動盪而時刻變化的年代,並為了保護身邊的人毫不猶豫挺身而出,她有她的傲骨,只是這份自尊不會放下,即使逞強鬧出了笑話,也在希望著能夠有人能夠理解和包容。
滔天的戰火和逝去的生命,不會動搖他對自由的永遠的渴望,好像是只要有冬日的風就能催開綻放的花瓣那樣,她無私的將所有珍藏的寶貝奉獻給需要的人,自己卻飽受著冬日烈風的洗禮。
受到質疑和摧殘的時候,她也僅僅只是默默的承受和忍耐著,笑對一切坎坷不順,也要把最美的果實留給每一個需要的人。
鶴望蘭在秋冬兩季,兩個相差近四十度的季節(九月秋老虎)(十二月寒流)(鶴望蘭大多生長在北方),都會義無反顧的徐徐展開金黃色的花瓣,不會有一點猶豫便自豪的將所有的美麗迅速淘盡,展現最美的容顏,就像那個天真像水,熱情如火的女子,不管有沒有人垂青讚賞,都會竭力展現自己最美的一面。
酸與櫫獳:碧綠色的哀傷,積怨而生的森林之子。
誕生花:四季秋海棠。
花語:我是你的永遠、互換的理解。
碧綠色的短捲髮,清澈的像是河水一般的青藍色的大瞳孔,精靈族特有的尖耳和細膩而白嫩的皮膚,是這位靦腆的紳士的最好寫照。
他是飽含著逝去生命痛苦而生的最後一位槐樹與豆藤的兒子,槐樹與豆藤的結合,讓他能夠自由的操控木本和草本的各種植物,操控植物的能力本就是十分稀有而罕見的本領,他卻玩的爐火純青,卻依然不會桀驁不馴,而是,像是七月上旬的那縷和諧而美好的初夏的風一樣,時刻在疲勞的午後吹過,喚醒半天的活力。
他出生之時,山神用休眠之前僅剩的法力賜予他以人的生命力,從九百九十九顆種子之中,此時正值孔甲亂夏,夏朝的第十三代君王將整個朝代搞亂的那一時代,孔甲要求手下大臣伐木開墾,毫不在乎森林的命脈,只是為了微薄的土地,成了農耕民族永遠不懂得欣賞美的遺憾,同時也是莫大的可悲,他們飢餓的頭腦不允許他們欣賞美景,只是為了能夠填飽肚子的來年而拚命努力。
眼中的彷徨是那逐漸消失的綠色,往日充滿生機歡聲笑語的一片生靈的樂土,被鋸子和鐮刀殘忍分裂,他親眼看著自己無法動彈的父母被鋸子分崩離析,心中的憤怒和仇恨自然不言而喻。
每一個生命,都是接受著祝福誕生的。。。不過他想,踐踏別人的生命的人,沒有活下去的資格,他拚命的復仇,放棄了自己的生命的本來意義,山神的第九百九十九分之一的幸運,換來的難道只能是詛咒?
櫫獳被卡斯特所惑,簽訂契約後不久卡斯特沉眠,他也再次歸隱山林,他愧對山神,便將自己的靈魂從肉體中分離,卻被族人們合夥救醒,從此,他便對自己下了禁錮,將植物和肉體結合,擁有理性的感知和動物的感官,後果是一旦狂化就會變成一堆沒有靈魂的朽木,到那個時候,誰也回天乏術,好在,這選擇的路,是他自己為自己挑選的,接受著祝福誕生的人,自然也會接收著祝福安詳死去,想必那個時候回到山神面前,他也無愧終生。
此時他用自己畢生所學,為一個迷了路的女孩子點燃了豆藤掛起的明燈,在高大的槐樹下一起吹奏起明媚的葉笛,願他不留遺憾的祝福,能夠永遠佇立在天涯的彼方,他的心中充滿了自我的克制,脾氣好的被朋友戲稱為櫫娘娘,願他的心境,能夠像山神所說的那樣,一切都是該被祝福和稱讚的美好。
好在這樣一個時代,也將馬上來臨。
魔邪:
誕生花:白紋草
花語:責任與信賴
赤紅色如鳶鳥的尾翼般華麗而鮮艷的長髮,華貴而一塵不染,那冰藍色的冷冽清眸,像是摻了凍的雞尾酒般清香而醉人,三角形的標準鼻樑挺拔而高瘦,兩邊顴骨高高架起在清俊的兩腮。
他是成熟男性兼大哥哥一樣的角色,在早早就脫離父母的兄妹兩人並肩為生存而努力的時候,魔邪很好的做出了擔當的表率,他無私的履行著作為家人的責任,任勞任怨亦無怨無悔。
幽冥雖然豪爽但惟獨缺根筋,缺乏理性的思考卻總是經不起別人的哀求,自生下來便帶有一種分秒必爭的特點,這點兩兄妹高度契合,只可惜妹妹卻用錯了地方。
大鶴望蘭的高調綻放,總是少不了曠野的歌唱,少不了庇護種子的矮草。
魔邪就是那顆永遠堅強的小草,即使知道了自己的妹妹會比自己更加強大,也會無私的讓出一片天地,他所履行的,是幽冥的先父交給他父親的重任,他毫不猶豫的接下了沉重的接力棒,並為生存作著無比艱辛的努力。
白紋草生來的使命是庇護那些沒有自衛能力的樹種,等到樹種發芽之後,他們便會成群在春天變成萎葉,即使這個季節他們已經等待了幾個年頭甚至幾十個年頭。
無論是草還是樹,都在無比期待著春天春雨的降臨,而白紋草卻能夠頑強撐過烈日炎炎的夏日和多雨多風變幻不定的秋日,和被雪覆蓋了一個季節的冬日,卻唯獨在最美的季節望著自己的守護長成了參天大樹和旋轉開俊俏的爭奇鬥豔的花瓣,他欣慰的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將在此刻終結,帶著隱約的不甘埋入泥土,在幾十年以後再次復甦。
無論守護也好,堅強也好,這種沒有背負,沒有被迫的心甘情願,是最美的一廂情願,哪怕小矛盾,不愉快,也將一併煙消雲散。
玂獄禍斗:叛逆的小神仙。
誕生花:紫色丁香。
花語:不滅之火。
禍斗的出身,本是說高不低,說低了又讓凡人羨慕無比的天上,自幼有著仙班的物資保障,衣食無憂的在沒有感情的冰冷的鳥籠里學習著仙人的理解。
成年之後,他被分配在雷神的身邊當做小跟班,時不時還會變成寵物狗逗樂身邊的人,他好像一個小丑一樣,能給嚴肅而沒有自由的天庭帶去最無邊的快樂。
他桀驁不馴,且不信邪,禁酒是罰酒他愣是不信,愣是想犯一次法嘗嘗好奇的各種新鮮,可曾想那酒一喝再也戒不掉,並會不斷增長酒量,從此禍斗百喝不醉,日益增大的酒量讓他渴求著人間的美酒。
有朝一日當他聽說了人間有很多沒嘗過的水果酒,他便耐不住性子問雷神下次何時下凡人間,雷神沒有耐心的告訴他一年以後,人間一年,天上一日,三百六十五天也就是三百六十五年,這樣他又怎能甘受不自由的煎熬,無奈之際禍斗用了最下流的機會犯下重罪貶入人間,要求天上一百天地下一百年,將他貶入戰亂最頻繁的夏朝末年去體驗奴隸的感受,怎想卻陰陽差錯的貶到了新野,與櫫獳相遇並結拜。
日後又陰陽差錯的碰上了懷孕的柯堇,並與其是一見鐘情,懷孕的人自然也有男人,那個男人是廣陵的貴族,有著沾花惹草的花花公子的風範,自幼看不慣仗勢欺人的禍斗在廣陵戰爭之後將倉皇撤離的寧權好好教訓一番之後娶走了柯堇,並發誓愛她並愛她肚子裡的孩子,即使這個孩子不是自己的,也比跟著一個罪孽深重的父親,要好得多。
天神是無法生育的,這點禍斗自然也明白,好在他如今有了一群打打鬧鬧的兄弟和一個半路的妻子,還有一個看似輕浮脫線卻又意外靠譜的上司,這個不算太完整的家庭也算的上是圓滿了。。。
伊芙利特·斯多普尼堪:忠誠的心,曾經曾是一個人,如今,願意為一個人示愛永恆。
誕生花:冬青。
花語:先見之明。
她是愛琴第一朝的諸多公主殿下之一,愛琴遭遇波塞冬之怒之後被摧毀過半,伊芙利特為了活命不得不與卡斯特簽訂契約成為魔族並跟隨其來到東方大陸。
愛琴人典型的特徵,一頭太陽顏色的金髮,左眼如海水一般遼闊的水藍,右眼卻是被魔化的猩紅。
卡斯特限制了她的自由,限制了她的能力,企圖要求她永遠為自己效力。卡斯特的宗旨是:“你們去尋找人類並分開契約,但利用完了可以自行處理,吃掉他們!”
但當其他的下屬都已經找到食用人類,伊芙利特卻還沒有找到,不是因為她太挑剔,而是,她實在難以看穿人的欲望潛在何處,她不是純粹的魔族,更不熟悉這片東方大陸的人們,她只能顯得拘謹。
卡斯特的最後通牒下發之後,狠心將她丟在大街上揚長而去,又冷又餓的她遇見了年僅八歲還穿著女裝的勾曜,二人相遇,勾曜僅僅是出於熊孩子對外界事物的好奇,不等伊芙利特說完便要求契約,伊芙利特自然沒有二話。
西方人對於契約的忠誠,在卡斯特所謂墮落西方文化的政治策略影響下,被其他魔族認為是愚蠢。
她遠遠的保持著距離,除了必須的任務之外從未與契約者勾曜大人有過任何的接觸,甚至沒有肢體。
就這樣默默的站在一旁,看著勾曜成長,長大成人,她默默的看著勾曜對關雪茗情有獨鐘,自己只是沒有勇氣,更是因為契約的隔閡,我們只是工作關係,她這樣勉強自己道。
她默默的為他們祈禱,像是冬青花撐起三角半圓傘似的站在阡陌的雨點下,靜靜的守護著和諧與安寧,衷心祝願著他們喜事天成,一切安好。
隨後契約解除,他也邂逅了自己喜歡的那個人,那個有點反應遲鈍,愛憎分明嫉惡如仇的笨蛋,那個愛好美食性格靦腆的男人。
勾曜:我對你的愛,亦願意帶你,走遍輪迴,即使下一世,我依然不會認錯。
誕生花:仙人掌
花語:燃燒的心
那個出身貴族卻桀驁不馴的男子漢,瞳孔中像是燃燒著永遠不會熄滅的火焰,永遠充滿活力的自豪與威嚴,像是抖擻精神的獅王一般衛冕著自己的權利。
自幼高貴的出身讓他自豪,同時也讓他苦惱,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過上浪跡天涯的浪人生活,而不是錦衣玉食的在太守的宮殿里滿腦子的政治條文,在案牘前幾個小時勾勾圈圈。(而且政治還不是自己的,說起來太守這個職位也實在憋屈,上面有丞相有皇上還有太監督導隊,下面萬民等待著自己的恩惠,看著嚴肅的身邊的太監皇上的寵兒的臉,實在有愧於蒙受欺騙的百姓。)
不過好在現在的皇上是自己最喜歡的女孩,又擁有著無與倫比的家世,自然他富可敵國,不可一世。
他豪邁的氣概不怒自威的尊嚴讓所有小人都無法直視他光輝燦爛的沒心沒肺的笑容,但只有一種真實的笑,他只會留給一個女人,寧可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也要為了一個女人而活著。
他誕生在最熱烈的夏季,是剛褪去雨水的乾柴烈火燃燒的最猛烈的七月下旬,與生俱來從骨子裡透出的滿腔豪情,與不顧一切的衝勁讓關雪茗看到了脫離封建的人的怒放的熱烈。
此刻他不用擔心自己的熱情會將對方衝散,因為對方也正巧到了最喜歡談戀愛的妙齡,當初春的細雨碰上三伏的烈日,愛情的結果將是我們無法想像的出乎意料。。。
朱彥隝徯:禁獸之子
誕生花:天竺葵
花語:決心
他是十三禁獸順位第五的朱彥羽一生下來的獨子,他誕生在遙遠的漠北平原,那是被詛咒的涸土,是無人涉足的絕境,四處堆滿了人為的枯骨,滿是絕境的哀傷與嘆息,或許其中一個枯骨曾經的靈魂,就是轉世的他。
發色是令人窒息的夜空的顏色,漆黑中透出點點深紫,雙眸中沁著一絲仇恨的血紅久久揮之不去。
屬於夜空的翼族,當濃密的黑色降臨人間,帶有風的窒息感摩擦在每一個路人的心臟上,稍不留神便是從天而降的死神,以恩賜般的青睞使其暴斃。
朱彥幼年聽過太多父親殺人的故事,心中的矛盾一直沒有解開,直至親眼所見。。。
他的父親是為夷國效力的將領,是將領中為數不多的戰績佼佼的英武之士,只不過,統治者總是對英雄有那么一點小小的要求,政治將最美好的前途斷送的那一天,他們默然點頭,朱彥羽一利用權力將妻兒送往遠在千里的漠北,自己轉身赴死,他也知道,政治的代價是什麼,或許立功的獎賞在歸來時,只有那個薄殼棺材屬於自己。
好在他與家人的最後一面,他贈予了親生兒子最重要的禮物,封印住他的力量,即使將影響他的反應,對於經歷那些屠殺的人來說,節制緊鎖能力,是為數不多的奢侈。
當朱彥在卡斯特門下,意外的聽說了是卡斯特間接害死他的父親的時候,復仇的傲火又怎能不愈演愈烈,跟小卡斯特商量之後,他同意叛逃,在夜色的掩護下,他永遠的逃離了殺父的仇人,但他終有一日會親手宰殺那個挑撥離間的人,所有血債不會沒有結局,欠下的債終究還是會被償還。
他就好似是那紅的似火的天竺葵,帶著誘惑似的香氣,花瓣緊鎖,卻又顯得淒淒迷人,看似嬌弱,卻有著能將絨毛勒緊成為針一般鋒利的能力,慣用莖針來武裝自己封閉的內心,而又有誰,能夠青睞他的美麗,賜予他最真摯的微笑,他也終究會自行拔下禁錮的莖針,收穫一份美好的幸福。
魘魃:無名無姓僅僅只是稱謂,我也有我存在的意義。
誕生花:銀邊吉祥草
花語:滿載希望
黑色的短髮乾淨利落,如浩瀚奔騰的浪花沖洗的岩石一般的曜石銀色的瞳孔,散發著智慧的睿光。
他在赤聯所擔任的雖然是水軍將領,卻有著像救火隊員一般的責任,他不苟言笑,話少事多,嘗嘗忙的不可開交卻又井井有條,笑看一群粗心的兄弟姐妹,用自己的方式點醒每一個歧途上漸行漸遠的人。
曾經的他,與禺京齊名,是魔族最血腥的戰士,他們不效忠任何信仰和組織,只為出高價的人去尋找那金錢所指的目的,亡命旅途是他的自嘲,不要追問是他的紀律,一絲不苟是他永遠的態度。
因過度疲勞而沉睡的他,可曾想會有一日被新的主子所喚醒,他竟奇蹟般的感到這個世界要比以前的舊世界要好得多,他便許下效忠的諾言,甘願為自己新的主子效力永恆,而收效甚微,或者收穫一個民主而自由的世界。
他就如同是那好管理的銀色吉祥草,不需要太多的看管可以自行律己,沒有太多的欲望和追求,只需要有一個有規律的世界,他就可以自己頑強的生長,而這個世界,有充足的水分和泥土,可以帶來他想要的希望。
賀蘭杜澤&賀蘭嘉黎:不是親人,勝似親人。
誕生花:臘梅&剪秋羅
花語:高尚的心靈&機智
他是桐柏縣精靈族中位置不高,卻有著僅次于山神的權威,擁有與生俱來對植物的感知能力,會製造一些“黑科技”類型的迷之藥物,雖然經常被養女鬧出烏龍,但終究還是心存善意。
她是自小因為血統而被遺棄的孩子,親生父母中有一位隱藏了魔族的血統,卻在孩子誕生後血統畢露無遺,她親生父親是那種對迷信忠誠不二的信徒,對這樣一個異族表示無法接受,隨後拋棄了母女。
四歲那年,父母居住的村落遭遇野火,被全部焚毀,她被庶查司的好心人領養,並在七歲那年被賀蘭杜澤所收養。
賀蘭杜澤本想要一個小男孩來幫助自己上山下野,代替自己日益的腿腳不便,可誰知庶查司里僅僅只剩下未成年的少女,且只有嘉黎一人健康,其餘無不是先天的殘疾。
當命運封鎖住了親情的大門,封建的苦難殘酷的隔閡了本該相見的親人,也會有非親非故有緣人,來再續這斬斷的緣分。
她本性是溫吞乖巧又纖細敏感的少女,與櫫獳的相遇並因為同族帶有的安全感的吸引,使她對外界充滿了好奇,養父用假死來刺激她的堅強,但隨後養父的謊言卻成了笑話,不過不管怎樣,總算是有了一個不算完整的家庭,可供疲勞的旅人依偎守護棲息取暖的光火。
以賽·奧加斯:迷途的忠犬。
誕生花:海桐
花語:自重
他本是斯巴達神學時代的一名普通但極為忠誠的騎士,性格嚴謹自律,按規矩辦事,不折不扣的原則主義讓他的道路並不順暢,甚至錯愛了一個逆賊的女兒,甘願放棄自己的原則為了博取岳父的歡心,而走上了刺殺主教的道路。
刺殺失敗之後慘遭砍手之刑,隨後流血而死,被卡斯特救活並安裝義肢,用殺戮來武裝自己,從此變成了不折不扣的仇恨聚斂器,他永遠只會效忠一個主人,但主人是會變的。。。
猩紅如血如蒼老的古木般的發色與瞳孔,濃的可以迷失人的本性,也像極了他的內心,是迷失在血潭之中的一隻忠義的狗,永遠效忠是他作為騎士所宣誓的那樣,不會對婦女動手也是他畢生所遵守的教條,但卻為了摯愛,而無論是任何交易,都能欣然接受,哪怕是賣身的不平等契約引導走向歧途的鴆毒,哪怕是知道了結局,也會義無反顧的走下去,至少他知道現實容不得他來改變。
像是龐大而莊嚴的海桐,日夜板著同一副面孔,用倉促的華麗來笑對暖陽的洗禮,花開即黃,即黃即敗,如此不祥的讖言與注定悲慘的命運交相輝映。。。注定了他命運的悲慘,不過這依然不代表注定的結局,即便是他不想去改變,有些抱怨不公的人,正在做著無比艱辛的努力,想必他終究會明白存在的意義,無非生與死的極端。。。
克法·撒魯姆森:罪孽的噩夢,不甘心被詛咒,也想拼盡全力讓罪孽塵封於心。
誕生花:美女櫻
花語:和睦、一切安好
他是古埃及第十三王朝法老王阿門埃瑪特朝時期到賽索斯特里斯時期的生命體,當時的他,和櫫獳一樣是植物身,只不過,被法老王發現了沙棘的功效里,有一種細菌能夠加速傷口感染,用來當刑具的話會讓犯人痛苦萬分。
後來,這一恐怖行徑驚醒了貓神貝斯特拉,貝斯特拉降下雷電和暴雨來懲罰人類,可曾想一道雷電擊中銅柱上的犯人,犯人被劈的焦黑,那根沙棘便是後來的克法,此時,他因為雷電的力量,而進化出了人形,無知的他被卡斯特的自由所吸引,然後,成為了令人聞風喪膽的時空沙棘僱傭者,為埃赫戰爭服務。
埃赫戰爭中殺人無數的恐怖魔物便是他,自此,埃及人打敗了西臺人的進攻,隨後賽索斯特里斯去世(死時不滿三十歲,也是罪有應得),繼位的是培羅斯法老,這位法老膽子略小,年齡略小,害怕父親時期的一切魔物會對自己造成影響,於是下令驅逐,克法被驅逐出境之後,到了東方,繼續被人為僱傭,直至卡斯特沉眠之後,才被重新召喚出來,並第一次以正常人的面貌示人。
衛冕和平的道路上,有偉大的勝利就一定有偉大的死亡,克法不是第一,更不是最後,衛冕需要成千上萬的志願者慷慨赴死,這是時代的鐵律,罕有不流血的革命,或是說,所有真理的詮釋都是用血換來的。
他的存在,就好比是早春三月匆匆爬上枝頭的美女櫻花,急於綻放,毫不在意天氣是否乍暖還寒,不在意是否適合盛開,他所在乎的只有對自由的渴望,急不可耐的高調的在枝頭舞蹈。
櫻花是注定充滿了悲傷的花朵,繁華盛雪,難掩淒涼與嬌柔,獵獵盛放,灼灼其華之後,總會在最美的時候,被和煦的春風吹過後,凋零成滿地的碎片。
克法·撒魯姆森,與諸多對自由懷揣夢想的志願者一樣,為了推翻封建帝制,否定奴隸制與獨裁君主集權,寧願最早的盛開在嚴寒之中,不畏懼封建的侵蝕和凍結,為了不朽的信念和堅定的意志,哪怕香消玉殞在完美盛開的地方,也無所畏懼。
科爾雅·維根·瑪格達:與政治永遠絕緣,只為謀求心理的寬恕。
誕生花:旅人蕉
花語:大無畏精神
她出身富貴,是維根王朝末期的公爵之女。
耀眼如白金在太陽下的璀璨光輝一般的白色長髮,幽藍的瞳孔中一絲鬼魅的淺紫游弋在瀚海般的視野之中,水滴狀的鼻樑是北歐中部地區人特有的象徵,連同那幽藍色的瞳孔,都是為之驕傲而自豪的象徵。
年少的她早早的經歷過了國家敗落,親人死於國政者之手,僅僅是平白無故的牽連與莫須有,就能隨便踐踏忠直之人的忠心,哪怕天地可鑑,也無濟於事。
失去了父親的她流浪在丹麥王朝統治下的德黑蘭島,沒有親人和依靠,只能乞討或者靠撿拾垃圾賺取僅有的為數不多的黑麵包。
而迦賽爾與母親的出現,卻好似是打開了一扇幸福的大門,只可惜這扇門關閉的又太早。
她不知道或者依然沉浸在自責之中,是自己為他們帶來了威脅,在墓地祭奠那天,是卡斯特的出現讓她第一次擁有了力量,卻也是卡斯特毀掉了她剛剛信任的母子二人。
迦賽爾的母親特洛托科索夫人,用死亡在她的心底植入了感情和幸福的種子,用獻身讓她明白了家人的作用,哪怕悲劇來的太過突然,她也只能在沒有力量的時候悄然接受,裝作毫不知情。
被帶到東方之後,安排在空幽的手下,在漠北靠恐嚇牧民換取羔羊作為保護費。
其實這一切無不是空幽的所作所為,他重傷科爾雅唯一的非血緣的弟弟,來恐嚇科爾雅用羊來換取他的生命,被蠱惑的她只能照做,空幽還不滿足,又將科爾雅的靈魂在睡覺的時候抽走並綁定在樺木上,從此她便植入了精靈族的體質,依靠樹木作為本體的精靈,雖然不完全是,但殘忍的改變,對於沒有力量的他來說,還只能是接受。
空幽又讓雪魁來製造謠言,謠言不脛而走,每一個牧民都遭受到了類似的恐嚇宣傳,相傳倘若不交羊的話,那么雪災會將村莊吞沒,看似無力的謊言,實為宛如一頂以死亡的人性加冕的罪之冠冕,讓科爾雅再也不願意服從這一道指令,她屢次放走到手的獵物,寧願連聲道歉也不願意用魔的力量強壓人類,對於空幽雪魁他們來說,這便是愚蠢,好在廣陵戰役之後卡斯特的老巢慘遭毀滅性的打擊,而空幽在撤離的途中被我們的主角們合夥擊斃,雪魁到處亂竄,逃到位於商洛的墓穴營地。
而科爾雅被櫫獳勸說放下屠刀,欣然接受一份和平,她說她永遠與政治絕緣,因為她不會忘記那是殺害父親的利器,永遠埋藏在心底的仇恨,會在最後一刻醞釀出怎樣的衝動。。。
德黑蘭的旅人蕉,雖說是外來且屈指可數,但同時又如她可貴的內心在這個世界上顯得珍貴而脆弱無比,喜好溫暖卻被移栽在殘酷的冰原,命運的不公讓她有了她的信念和她的奉獻,以及對他的始終堅守,終將會將千年沉澱的冰雪化作一股心裡流淌的暖泉,她是否能放下塵封的悲哀枷鎖,欣然接受這一份快樂。
請一定要相信,不管過去怎樣黑暗,所有的黑暗僅僅只是在襯托黎明的璀璨,因為太陽需要夜的開幕,才能更加盛大壯麗而輝煌,否則平白無故的成功將顯得太過做作且浮華喧囂,沒有深刻的含義會成為過往的雲煙被人所恥笑。
誕生花:銀丹草
花語:美德
她是唯一一個貫穿故事始終的角色,開篇滔天的戰火與悄然醞釀的陰謀,欲要侵蝕著每一位敢於鬥爭的志願者的神經,姒履癸,那個曾經背負了詛咒出生,卻被祝福著備戰的戰神,在女人和國家面前選擇了前者,前後的差距或許只是時間問題所能夠彌補,但既然如此,就等於將世界拋向了深淵。
她本是現實中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國中生,前世妺喜的靈魂,像是銀丹所散發的芳香將沉睡在地獄中的姒履癸喚醒,他是罪孽,陰謀於一身的不可接觸者,在佛教里,這樣的人需要上千年的沉澱,罪惡才能夠洗清,然而就在封印鬆動的那一刻,他又回到了人間,並找到了那個女孩,告訴她,想要活下去,唯有穿越到那個時代,改寫悲劇,那么一切都將會改變,連同中國塵封的歷史,也將一併改寫。
對此,她只有默默點頭,冒著被利用的危險在交換法器之餘,等於簽署了一份賣身契,她所不知道的是,這等於她永遠放棄了現代的便捷,而轉身向一個滿是血腥和屠殺的世界走去,一切的未知都在經歷了浩劫的夢魘甦醒之前,悄然展現。
好在她降落的時代,是全面戰爭爆發之前的南方,南方的寂靜,阡陌的光暈,她既然知道了世界的結局,又怎能甘願享受這份即將不再的美夢,她有她的使命,即使是身軀遭到毀滅,也要完成這一份根本不可能的任務,改寫夏朝的結局。
改寫之後,中國將再也沒有奴隸制,沒有被摧殘的文化,甚至不會有誤人子弟的儒家學說的出現,但這一切,僅僅在穿越的第一天晚上,她動搖了。
當眼見姒履癸殺人的血腥,她便已經好感不再,屢次質疑他的決定,而姒履癸,也與她保持著十分的疏離,不去理會這個沒有過去的女孩,但僅僅是因為好奇,他將她帶回了中原,帶到了自己身邊。
姒履癸有自己喜歡的人,又怎么能去喜歡一個身份不明的女子,他轉身離開的身影,讓雪茗感受到的,只有一份不被青睞的安心,和釋然,讓一個惡魔去喜歡自己,那便是萬劫不復的地獄,她知道,跟這樣一個屠夫,沒有好的下場,二人的距離越來越遠,幾乎沒有了平行的可能,而勾曜的出現,卻好似點亮了一盞明燈,那是救贖深陷囚籠的青鳥脫離苦難的燈火,為其,雪茗第一次與勾曜交談,便已經略有好感,一起徙倚在夕陽之下,攀談明日的故事,一起在祈禱的時候,訴諸幽思,對父母從未敞開的心聲,卻為了一個早已淹沒在歷史長河中的小人物而痛快敞開,歷史是冰冷而沉默的,即使眼前的人物再怎樣的澄澈透明而立體,那也是無用的徒勞,雪茗不願意這樣承認,即使是知道勾曜活不過二十,更不會成家,她也奮盡全力,去為改變這一個人的命運,而不斷努力著,只可惜,她錯了方向,挽回了一個無關緊要的人的性命,可誰知,這一次,她卻成功了,成功說服勾曜在自殺式之前放下屠刀,成功說服他感受到世界的美好,只是因為她愛他,而他,卻毅然決然為她斬斷了封建的枷鎖,義無反顧的,寧願放棄太守的高位,也要與她一併同行,她說他是自己的星星,是那顆在只有血腥屠殺瘋狂暴虐的世界中唯一的一顆看的見的星辰,但距離太過渺遠,身份懸殊,國家危難,使得兩個人始終的隔閡不斷,惡魔詛咒的摧殘,更是給這一份即將劃出深淵的愛情裂痕,更下了一把鋒利的斷箭。
她是那早春倉皇盛放的銀丹,宛如脫離線條的夢境在覺悟之時會幡然破碎一塌糊塗,太早太過的人生,在現代本是國中生做夢也想不到的早戀,在那個十五歲算成年,出生之前就定娃娃親的時代,這一切太過正常不過。
夏朝是剛脫離荒蠻時代的第一文明,它早早的盛放將能力全部灌注在人的啟迪,統治者往往頭腦活躍,不拘小節,大禹的後代宛如龍的九子,個頂個的不是省油的燈,這樣的社會開放,自由,儘管歷史書的描寫如此面目全非,那個時代,說起來,它沒有奴隸制,沒有想像中的那么可怕,但卻有數不清的敵人對中原大地虎視眈眈。
她就好像是塔羅里代表愚者的那張紙牌,即使是愚蠢也有她可愛的道理,帶著一股早春的倉皇,那股活蹦亂跳的新鮮勁,在傾頹的末世里,成為了唯一清新亮麗而簡約的風景。
她的存在,對這個國家可以說是驢唇不對馬嘴,從來沒有人去注意她的存在,除了兩個人,一個,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勾曜,另一個,是太史令。
太史令:雙重性格的美男子,一半魔,一半人。
誕生花:野薔薇
花語:你心知我心
他是具有兩面人格的美男子,天生如瀑布般的長髮,高挑的鼻樑,濃而炯炯的雙瞳,散發著中式男性最古老的美麗,本是風度翩翩儀表堂堂的艾陵城太守,一次公務之旅,他在中原因關龍逢臨時出差,而接手了這份工作,核查關雪茗的身份。
在第一次的見面,他便源源不斷的展示著自己的殷勤,嫻熟的倒茶,談吐不凡的風流,時不時的玩笑語氣,精巧華麗見多識廣的趣聞,對一個女性來說該是如何的迷人。
她感覺好像是找到了真命天子,卻不知道這是一個喪偶的中年男子,不怪她發現的太晚,也不是他隱藏的太深,而是,這份責任無法推敲和自拔,這份沉重的飄渺的看不見的責任,日益讓美男子逐漸消瘦,他只能一次次隱藏自己的欲望,卻依舊捨不得放開手中唯一的溫暖。
即使他發現她的偽造,也並沒有秉公執法,而是以權謀私,願意用自己的身份去隱藏她的一切,殊不知這種隱藏在日後卻成為了不信任因素之一。
太史令的雙重人格,每一重對她來說都是異樣的迷人,宛如在漆黑的夜路前方,路燈中的微笑,便是家的溫馨,她不顧一切的投入他做作的懷抱,不知道他雙重人格下,隱藏的到底是風流的韶華,還是支離破碎的噩夢。
他對她隱藏的,自己的真實身份,夏朝最大的武器世家太史世家,當時,哪裡有死亡,哪裡就一定有太史家的身影,他們不效忠任何組織,也不效忠任何信仰,只是用血腥謀取金錢,即使是挑撥離間也不過如此。
他是在最後的春天綻放的遲來的野薔薇,虛無縹緲的落日是他看到的唯一美的景色,那浮華瑰麗的天邊,留存的卻只有死亡的陰影,他是末世的高官,注定要為了國家喪命,他是國家的犧牲品,是姒履癸精心培養的殺戮機器,為扳回國勢的傾頹,欲要彰顯自己的衷心,他不惜與卡斯特簽訂契約成為半魔族,他曾心想在瘋狂之後了結自己的生命,這樣對國家來說也算是盡忠,自己無愧忠節,可誰知在全面戰爭爆發前一個月,他空虛的心卻被毫不相干的女人填了個一點不剩。
工作之餘他不忍心將這樣的女孩送到慎刑司逼問家境然後含冤處死,他希望能將她摟在身邊,存留著溫柔的氣息,將最後的慈愛統統送給了她,遞交愛情的信物在此時看來的愉快,卻在將來成為了不可逾越的障礙。
卡斯特的詛咒蔓延全身,痛苦讓心臟的負荷一度升高,無法感知心的溫度,這讓他如同套上了冰封的棺材,在棺材裡看到外面的美麗卻依舊無法觸摸,全身冰冷是成為魔族的必修課程,這對於那個只會殺戮的他來說根本沒有什麼,但對於那個女孩,他不忍心,不忍心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國家,而寧願奉獻給女孩。
他背負罪孽,背負毀約的懲罰,欲要殺出一條生存的道路,齒輪閉合的嘀嗒作響,還是將他推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當知道了自己的前世,那個相同的靈魂,竟然是卡斯特早已死去的弟弟,波呂克斯,他愚蠢的認同了卡斯特的觀點,以不傷害關雪茗的契約與他做了再一次的交換,被他改造成了戰爭機器。
在建國的那天,太史令頹然的從眾人的眼裡消失,轉身奔赴萬劫不復的黑暗深淵,他的赴約讓卡斯特明白了女人的重要性,此時的關雪茗本應隱姓埋名逃離卡斯特的魔爪,卻稀里糊塗的當上了女皇。
卡斯特當然不會這樣相信一個還思念著敵人的人,他派出了自己的親信奧契狄索斯,本以為這樣一個恐怖的九頭水妖能禁錮住太史令,可誰知奧契狄索斯早已對帕勒克氏暴政心存不滿,與太史令一同策劃了逆反的初衷,而被克法變成石像的卡斯特,囚禁在沒有自由的深淵,日益加重的仇恨蒙蔽了他的一切,他只能動用謊言的鼓動性,多數都已經是空頭的支票。
乾:沒有實體的靈魂,強行介入只有空蕩和虛偽的感情。
誕生花:冬紫羅蘭
花語:思慕
魔心:絕望之心
她本是在時空裂變中從關雪茗身體內分裂出來的不完全的靈魂,取代了關雪茗一部分的智力,卻不懂得感情,這樣的人只能在這個時代,被洗腦灌注思想,而她卻沒有被灌注那些殺戮,周圍的人,有幸是嚮往和平的兄弟姐妹。
在初冬第一場雪中誕生的冬紫羅蘭,猶如她那冰封一般的內心,滿是質疑的嘆息充滿了她的大腦,作為靈魂她很知趣的聽從主人的吩咐,聽從主人的任何話,卻在一次意外中,第一次動起了貪婪的欲望,也第一次有了心,她吸收了完顏肅台所有的元神,作為己用,從此有了主見和實體,也從此意味著有了牽掛。
冰封的心神,在第一次喚醒之後,已經有所醒悟,她擁有著和關雪茗一樣的相貌,只是更加清秀嚴肅和冷峻,不近人情的外表下,所隱藏的也是嚮往著自由和和平的心。
小卡斯特·斯庫里:浪子回頭。
誕生花:蘇格蘭松
花語:開拓精神
魔心:喜悅之心
他是沒有出身的分身,他遺忘了家室,遺忘了姓氏,甚至遺忘掉了一切可以追尋的東西,他是卡斯特為了方便而用黑血隨意捏造出來的分身,賜予了他和卡斯特相同的力量。
製造出來的他,沒有感官,沒有神經,沒有一絲感情,整天在鮮血橫肆之中執行著卡斯特交授的殺戮任務,不折不扣的惡魔的代言人。
九百多年如一日的殺戮,在他眼裡成為了過往的風景,他不記得自己殺了多少人,只是知道那些人都在恨著自己,也許還有別的,不過他根本不會在乎那些。
卡斯特的所有部下,都有兩個姓氏,賜姓斯庫里,和原本的形式,而分身已經忘記了自己本來的名字和姓氏,此斯庫里,其實是莫大的侮辱。
妖冶如狂風般的紫色長髮,像是高貴的馬鬢,血紅色的深深凹陷的瞳孔之中,除了憎惡與仇恨,似乎還有別的感情。
他本來這樣殺下去,就不會有後來的朝代,只可惜,命運在極端的邊落總是給人亦逆轉的奇蹟出現,也只有奇蹟,才能拉回迷失道路的罪子。
幽冥魔邪的父親,因觸犯了卡斯特的利益,被卡斯特批准討伐,然而卻沒想到,就是這件事情,讓小卡的靈魂,像風吹岩石,終有一天會鬆動一樣,將他與血腥絕緣。
幽燁,同樣也是殺戮無數的罪子,可即使是這樣的人,居然會為了保護自己的女兒獻出生命,給小卡演了一處沒有排練的偽劣的戲,本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局,卻有著最難以理解的感情摻雜其中,為什麼?明明是與自己並不相干的人,卻要這樣保護,沒有力量,不就沒有活下去的資格么?
從此,這種思想在他的心底動搖,他漸漸開始不相信卡斯特,卡斯特覺出了異樣,對於他來說,世界,還有分身,都是積木草草搭建的樓房,稍微不爽就可以一腳踢倒,重新組建一副自己喜歡的出來,他暗中計畫回收這個分身,可曾想就在他被復仇的幽冥魔邪催眠之後,小卡變成了一灘黑血凝固成了新的個體,對於他來說,那是第一次品嘗自由的味道,和血腥味不同,他願意將這種味道牢牢記在心底,並為自己過去的行徑感到慚愧,至少,這個世界還沒有糟糕到必須要毀掉。
在目送魔羅懷抱著不滿十歲的幽冥匆匆離去的那一刻,靈魂的蛻變便已經開始。
在他真的看穿這個世界之前,請讓我們一起相信,只要擁有信心和勇氣,陽光總會穿透黑暗,逝者會安息和轉世,而生者會品嘗到永遠甘甜而芬芳的自由的爽風。
幽冥魔邪:並蒂雙生子,卻有各自的逞能。
幽冥:
誕生花:大鶴望蘭。
花語:愛的音符。
黑的像綢子,靜的像是一灘墨綠色的潭水一般深邃的髮絲,柔美的順勢而下,天生遭遇詛咒的金色瞳孔,隱藏著讓人膽寒的魔力。
她是從早秋到初冬連開四個月的花朵,也只有大鶴望蘭,能忍受的住簌簌飄落的悲傷和寂寞,承受住寒冷和炎熱各不相同的溫度,無聲佇立在河邊,投下希望的種子,十年只為一次,轉瞬變作土灰。
大鶴望蘭,會站在低矮的河堤上,連續佇立上四個月之久,無聲無息,暗自準備著,像是少女小心翼翼的準備著珍珠項鍊一樣,它珍藏著的種子,是它送給河水的禮物,也是送給河水的祝福。
與鶴望蘭同一天出生的幽冥,亦是個喜歡逞強的孩子,她故作堅強的背後,籠罩著悲慘的家世和不順的歷程,風吹雨打十年一日,用自尊為衛冕內心的脆弱,亦在艱難險阻前毫不膽顫心驚。
建國之後,她一直在眾人看不見的地方作著自我的戰鬥,自我的反省,極力適應著動盪而時刻變化的年代,並為了保護身邊的人毫不猶豫挺身而出,她有她的傲骨,只是這份自尊不會放下,即使逞強鬧出了笑話,也在希望著能夠有人能夠理解和包容。
滔天的戰火和逝去的生命,不會動搖他對自由的永遠的渴望,好像是只要有冬日的風就能催開綻放的花瓣那樣,她無私的將所有珍藏的寶貝奉獻給需要的人,自己卻飽受著冬日烈風的洗禮。
受到質疑和摧殘的時候,她也僅僅只是默默的承受和忍耐著,笑對一切坎坷不順,也要把最美的果實留給每一個需要的人。
鶴望蘭在秋冬兩季,兩個相差近四十度的季節(九月秋老虎)(十二月寒流)(鶴望蘭大多生長在北方),都會義無反顧的徐徐展開金黃色的花瓣,不會有一點猶豫便自豪的將所有的美麗迅速淘盡,展現最美的容顏,就像那個天真像水,熱情如火的女子,不管有沒有人垂青讚賞,都會竭力展現自己最美的一面。
酸與櫫獳:碧綠色的哀傷,積怨而生的森林之子。
誕生花:四季秋海棠。
花語:我是你的永遠、互換的理解。
碧綠色的短捲髮,清澈的像是河水一般的青藍色的大瞳孔,精靈族特有的尖耳和細膩而白嫩的皮膚,是這位靦腆的紳士的最好寫照。
他是飽含著逝去生命痛苦而生的最後一位槐樹與豆藤的兒子,槐樹與豆藤的結合,讓他能夠自由的操控木本和草本的各種植物,操控植物的能力本就是十分稀有而罕見的本領,他卻玩的爐火純青,卻依然不會桀驁不馴,而是,像是七月上旬的那縷和諧而美好的初夏的風一樣,時刻在疲勞的午後吹過,喚醒半天的活力。
他出生之時,山神用休眠之前僅剩的法力賜予他以人的生命力,從九百九十九顆種子之中,此時正值孔甲亂夏,夏朝的第十三代君王將整個朝代搞亂的那一時代,孔甲要求手下大臣伐木開墾,毫不在乎森林的命脈,只是為了微薄的土地,成了農耕民族永遠不懂得欣賞美的遺憾,同時也是莫大的可悲,他們飢餓的頭腦不允許他們欣賞美景,只是為了能夠填飽肚子的來年而拚命努力。
眼中的彷徨是那逐漸消失的綠色,往日充滿生機歡聲笑語的一片生靈的樂土,被鋸子和鐮刀殘忍分裂,他親眼看著自己無法動彈的父母被鋸子分崩離析,心中的憤怒和仇恨自然不言而喻。
每一個生命,都是接受著祝福誕生的。。。不過他想,踐踏別人的生命的人,沒有活下去的資格,他拚命的復仇,放棄了自己的生命的本來意義,山神的第九百九十九分之一的幸運,換來的難道只能是詛咒?
櫫獳被卡斯特所惑,簽訂契約後不久卡斯特沉眠,他也再次歸隱山林,他愧對山神,便將自己的靈魂從肉體中分離,卻被族人們合夥救醒,從此,他便對自己下了禁錮,將植物和肉體結合,擁有理性的感知和動物的感官,後果是一旦狂化就會變成一堆沒有靈魂的朽木,到那個時候,誰也回天乏術,好在,這選擇的路,是他自己為自己挑選的,接受著祝福誕生的人,自然也會接收著祝福安詳死去,想必那個時候回到山神面前,他也無愧終生。
此時他用自己畢生所學,為一個迷了路的女孩子點燃了豆藤掛起的明燈,在高大的槐樹下一起吹奏起明媚的葉笛,願他不留遺憾的祝福,能夠永遠佇立在天涯的彼方,他的心中充滿了自我的克制,脾氣好的被朋友戲稱為櫫娘娘,願他的心境,能夠像山神所說的那樣,一切都是該被祝福和稱讚的美好。
好在這樣一個時代,也將馬上來臨。
魔邪:
誕生花:白紋草
花語:責任與信賴
赤紅色如鳶鳥的尾翼般華麗而鮮艷的長髮,華貴而一塵不染,那冰藍色的冷冽清眸,像是摻了凍的雞尾酒般清香而醉人,三角形的標準鼻樑挺拔而高瘦,兩邊顴骨高高架起在清俊的兩腮。
他是成熟男性兼大哥哥一樣的角色,在早早就脫離父母的兄妹兩人並肩為生存而努力的時候,魔邪很好的做出了擔當的表率,他無私的履行著作為家人的責任,任勞任怨亦無怨無悔。
幽冥雖然豪爽但惟獨缺根筋,缺乏理性的思考卻總是經不起別人的哀求,自生下來便帶有一種分秒必爭的特點,這點兩兄妹高度契合,只可惜妹妹卻用錯了地方。
大鶴望蘭的高調綻放,總是少不了曠野的歌唱,少不了庇護種子的矮草。
魔邪就是那顆永遠堅強的小草,即使知道了自己的妹妹會比自己更加強大,也會無私的讓出一片天地,他所履行的,是幽冥的先父交給他父親的重任,他毫不猶豫的接下了沉重的接力棒,並為生存作著無比艱辛的努力。
白紋草生來的使命是庇護那些沒有自衛能力的樹種,等到樹種發芽之後,他們便會成群在春天變成萎葉,即使這個季節他們已經等待了幾個年頭甚至幾十個年頭。
無論是草還是樹,都在無比期待著春天春雨的降臨,而白紋草卻能夠頑強撐過烈日炎炎的夏日和多雨多風變幻不定的秋日,和被雪覆蓋了一個季節的冬日,卻唯獨在最美的季節望著自己的守護長成了參天大樹和旋轉開俊俏的爭奇鬥豔的花瓣,他欣慰的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將在此刻終結,帶著隱約的不甘埋入泥土,在幾十年以後再次復甦。
無論守護也好,堅強也好,這種沒有背負,沒有被迫的心甘情願,是最美的一廂情願,哪怕小矛盾,不愉快,也將一併煙消雲散。
玂獄禍斗:叛逆的小神仙。
誕生花:紫色丁香。
花語:不滅之火。
禍斗的出身,本是說高不低,說低了又讓凡人羨慕無比的天上,自幼有著仙班的物資保障,衣食無憂的在沒有感情的冰冷的鳥籠里學習著仙人的理解。
成年之後,他被分配在雷神的身邊當做小跟班,時不時還會變成寵物狗逗樂身邊的人,他好像一個小丑一樣,能給嚴肅而沒有自由的天庭帶去最無邊的快樂。
他桀驁不馴,且不信邪,禁酒是罰酒他愣是不信,愣是想犯一次法嘗嘗好奇的各種新鮮,可曾想那酒一喝再也戒不掉,並會不斷增長酒量,從此禍斗百喝不醉,日益增大的酒量讓他渴求著人間的美酒。
有朝一日當他聽說了人間有很多沒嘗過的水果酒,他便耐不住性子問雷神下次何時下凡人間,雷神沒有耐心的告訴他一年以後,人間一年,天上一日,三百六十五天也就是三百六十五年,這樣他又怎能甘受不自由的煎熬,無奈之際禍斗用了最下流的機會犯下重罪貶入人間,要求天上一百天地下一百年,將他貶入戰亂最頻繁的夏朝末年去體驗奴隸的感受,怎想卻陰陽差錯的貶到了新野,與櫫獳相遇並結拜。
日後又陰陽差錯的碰上了懷孕的柯堇,並與其是一見鐘情,懷孕的人自然也有男人,那個男人是廣陵的貴族,有著沾花惹草的花花公子的風範,自幼看不慣仗勢欺人的禍斗在廣陵戰爭之後將倉皇撤離的寧權好好教訓一番之後娶走了柯堇,並發誓愛她並愛她肚子裡的孩子,即使這個孩子不是自己的,也比跟著一個罪孽深重的父親,要好得多。
天神是無法生育的,這點禍斗自然也明白,好在他如今有了一群打打鬧鬧的兄弟和一個半路的妻子,還有一個看似輕浮脫線卻又意外靠譜的上司,這個不算太完整的家庭也算的上是圓滿了。。。
伊芙利特·斯多普尼堪:忠誠的心,曾經曾是一個人,如今,願意為一個人示愛永恆。
誕生花:冬青。
花語:先見之明。
她是愛琴第一朝的諸多公主殿下之一,愛琴遭遇波塞冬之怒之後被摧毀過半,伊芙利特為了活命不得不與卡斯特簽訂契約成為魔族並跟隨其來到東方大陸。
愛琴人典型的特徵,一頭太陽顏色的金髮,左眼如海水一般遼闊的水藍,右眼卻是被魔化的猩紅。
卡斯特限制了她的自由,限制了她的能力,企圖要求她永遠為自己效力。卡斯特的宗旨是:“你們去尋找人類並分開契約,但利用完了可以自行處理,吃掉他們!”
但當其他的下屬都已經找到食用人類,伊芙利特卻還沒有找到,不是因為她太挑剔,而是,她實在難以看穿人的欲望潛在何處,她不是純粹的魔族,更不熟悉這片東方大陸的人們,她只能顯得拘謹。
卡斯特的最後通牒下發之後,狠心將她丟在大街上揚長而去,又冷又餓的她遇見了年僅八歲還穿著女裝的勾曜,二人相遇,勾曜僅僅是出於熊孩子對外界事物的好奇,不等伊芙利特說完便要求契約,伊芙利特自然沒有二話。
西方人對於契約的忠誠,在卡斯特所謂墮落西方文化的政治策略影響下,被其他魔族認為是愚蠢。
她遠遠的保持著距離,除了必須的任務之外從未與契約者勾曜大人有過任何的接觸,甚至沒有肢體。
就這樣默默的站在一旁,看著勾曜成長,長大成人,她默默的看著勾曜對關雪茗情有獨鐘,自己只是沒有勇氣,更是因為契約的隔閡,我們只是工作關係,她這樣勉強自己道。
她默默的為他們祈禱,像是冬青花撐起三角半圓傘似的站在阡陌的雨點下,靜靜的守護著和諧與安寧,衷心祝願著他們喜事天成,一切安好。
隨後契約解除,他也邂逅了自己喜歡的那個人,那個有點反應遲鈍,愛憎分明嫉惡如仇的笨蛋,那個愛好美食性格靦腆的男人。
勾曜:我對你的愛,亦願意帶你,走遍輪迴,即使下一世,我依然不會認錯。
誕生花:仙人掌
花語:燃燒的心
那個出身貴族卻桀驁不馴的男子漢,瞳孔中像是燃燒著永遠不會熄滅的火焰,永遠充滿活力的自豪與威嚴,像是抖擻精神的獅王一般衛冕著自己的權利。
自幼高貴的出身讓他自豪,同時也讓他苦惱,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過上浪跡天涯的浪人生活,而不是錦衣玉食的在太守的宮殿里滿腦子的政治條文,在案牘前幾個小時勾勾圈圈。(而且政治還不是自己的,說起來太守這個職位也實在憋屈,上面有丞相有皇上還有太監督導隊,下面萬民等待著自己的恩惠,看著嚴肅的身邊的太監皇上的寵兒的臉,實在有愧於蒙受欺騙的百姓。)
不過好在現在的皇上是自己最喜歡的女孩,又擁有著無與倫比的家世,自然他富可敵國,不可一世。
他豪邁的氣概不怒自威的尊嚴讓所有小人都無法直視他光輝燦爛的沒心沒肺的笑容,但只有一種真實的笑,他只會留給一個女人,寧可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也要為了一個女人而活著。
他誕生在最熱烈的夏季,是剛褪去雨水的乾柴烈火燃燒的最猛烈的七月下旬,與生俱來從骨子裡透出的滿腔豪情,與不顧一切的衝勁讓關雪茗看到了脫離封建的人的怒放的熱烈。
此刻他不用擔心自己的熱情會將對方衝散,因為對方也正巧到了最喜歡談戀愛的妙齡,當初春的細雨碰上三伏的烈日,愛情的結果將是我們無法想像的出乎意料。。。
朱彥隝徯:禁獸之子
誕生花:天竺葵
花語:決心
他是十三禁獸順位第五的朱彥羽一生下來的獨子,他誕生在遙遠的漠北平原,那是被詛咒的涸土,是無人涉足的絕境,四處堆滿了人為的枯骨,滿是絕境的哀傷與嘆息,或許其中一個枯骨曾經的靈魂,就是轉世的他。
發色是令人窒息的夜空的顏色,漆黑中透出點點深紫,雙眸中沁著一絲仇恨的血紅久久揮之不去。
屬於夜空的翼族,當濃密的黑色降臨人間,帶有風的窒息感摩擦在每一個路人的心臟上,稍不留神便是從天而降的死神,以恩賜般的青睞使其暴斃。
朱彥幼年聽過太多父親殺人的故事,心中的矛盾一直沒有解開,直至親眼所見。。。
他的父親是為夷國效力的將領,是將領中為數不多的戰績佼佼的英武之士,只不過,統治者總是對英雄有那么一點小小的要求,政治將最美好的前途斷送的那一天,他們默然點頭,朱彥羽一利用權力將妻兒送往遠在千里的漠北,自己轉身赴死,他也知道,政治的代價是什麼,或許立功的獎賞在歸來時,只有那個薄殼棺材屬於自己。
好在他與家人的最後一面,他贈予了親生兒子最重要的禮物,封印住他的力量,即使將影響他的反應,對於經歷那些屠殺的人來說,節制緊鎖能力,是為數不多的奢侈。
當朱彥在卡斯特門下,意外的聽說了是卡斯特間接害死他的父親的時候,復仇的傲火又怎能不愈演愈烈,跟小卡斯特商量之後,他同意叛逃,在夜色的掩護下,他永遠的逃離了殺父的仇人,但他終有一日會親手宰殺那個挑撥離間的人,所有血債不會沒有結局,欠下的債終究還是會被償還。
他就好似是那紅的似火的天竺葵,帶著誘惑似的香氣,花瓣緊鎖,卻又顯得淒淒迷人,看似嬌弱,卻有著能將絨毛勒緊成為針一般鋒利的能力,慣用莖針來武裝自己封閉的內心,而又有誰,能夠青睞他的美麗,賜予他最真摯的微笑,他也終究會自行拔下禁錮的莖針,收穫一份美好的幸福。
魘魃:無名無姓僅僅只是稱謂,我也有我存在的意義。
誕生花:銀邊吉祥草
花語:滿載希望
黑色的短髮乾淨利落,如浩瀚奔騰的浪花沖洗的岩石一般的曜石銀色的瞳孔,散發著智慧的睿光。
他在赤聯所擔任的雖然是水軍將領,卻有著像救火隊員一般的責任,他不苟言笑,話少事多,嘗嘗忙的不可開交卻又井井有條,笑看一群粗心的兄弟姐妹,用自己的方式點醒每一個歧途上漸行漸遠的人。
曾經的他,與禺京齊名,是魔族最血腥的戰士,他們不效忠任何信仰和組織,只為出高價的人去尋找那金錢所指的目的,亡命旅途是他的自嘲,不要追問是他的紀律,一絲不苟是他永遠的態度。
因過度疲勞而沉睡的他,可曾想會有一日被新的主子所喚醒,他竟奇蹟般的感到這個世界要比以前的舊世界要好得多,他便許下效忠的諾言,甘願為自己新的主子效力永恆,而收效甚微,或者收穫一個民主而自由的世界。
他就如同是那好管理的銀色吉祥草,不需要太多的看管可以自行律己,沒有太多的欲望和追求,只需要有一個有規律的世界,他就可以自己頑強的生長,而這個世界,有充足的水分和泥土,可以帶來他想要的希望。
賀蘭杜澤&賀蘭嘉黎:不是親人,勝似親人。
誕生花:臘梅&剪秋羅
花語:高尚的心靈&機智
他是桐柏縣精靈族中位置不高,卻有著僅次于山神的權威,擁有與生俱來對植物的感知能力,會製造一些“黑科技”類型的迷之藥物,雖然經常被養女鬧出烏龍,但終究還是心存善意。
她是自小因為血統而被遺棄的孩子,親生父母中有一位隱藏了魔族的血統,卻在孩子誕生後血統畢露無遺,她親生父親是那種對迷信忠誠不二的信徒,對這樣一個異族表示無法接受,隨後拋棄了母女。
四歲那年,父母居住的村落遭遇野火,被全部焚毀,她被庶查司的好心人領養,並在七歲那年被賀蘭杜澤所收養。
賀蘭杜澤本想要一個小男孩來幫助自己上山下野,代替自己日益的腿腳不便,可誰知庶查司里僅僅只剩下未成年的少女,且只有嘉黎一人健康,其餘無不是先天的殘疾。
當命運封鎖住了親情的大門,封建的苦難殘酷的隔閡了本該相見的親人,也會有非親非故有緣人,來再續這斬斷的緣分。
她本性是溫吞乖巧又纖細敏感的少女,與櫫獳的相遇並因為同族帶有的安全感的吸引,使她對外界充滿了好奇,養父用假死來刺激她的堅強,但隨後養父的謊言卻成了笑話,不過不管怎樣,總算是有了一個不算完整的家庭,可供疲勞的旅人依偎守護棲息取暖的光火。
以賽·奧加斯:迷途的忠犬。
誕生花:海桐
花語:自重
他本是斯巴達神學時代的一名普通但極為忠誠的騎士,性格嚴謹自律,按規矩辦事,不折不扣的原則主義讓他的道路並不順暢,甚至錯愛了一個逆賊的女兒,甘願放棄自己的原則為了博取岳父的歡心,而走上了刺殺主教的道路。
刺殺失敗之後慘遭砍手之刑,隨後流血而死,被卡斯特救活並安裝義肢,用殺戮來武裝自己,從此變成了不折不扣的仇恨聚斂器,他永遠只會效忠一個主人,但主人是會變的。。。
猩紅如血如蒼老的古木般的發色與瞳孔,濃的可以迷失人的本性,也像極了他的內心,是迷失在血潭之中的一隻忠義的狗,永遠效忠是他作為騎士所宣誓的那樣,不會對婦女動手也是他畢生所遵守的教條,但卻為了摯愛,而無論是任何交易,都能欣然接受,哪怕是賣身的不平等契約引導走向歧途的鴆毒,哪怕是知道了結局,也會義無反顧的走下去,至少他知道現實容不得他來改變。
像是龐大而莊嚴的海桐,日夜板著同一副面孔,用倉促的華麗來笑對暖陽的洗禮,花開即黃,即黃即敗,如此不祥的讖言與注定悲慘的命運交相輝映。。。注定了他命運的悲慘,不過這依然不代表注定的結局,即便是他不想去改變,有些抱怨不公的人,正在做著無比艱辛的努力,想必他終究會明白存在的意義,無非生與死的極端。。。
克法·撒魯姆森:罪孽的噩夢,不甘心被詛咒,也想拼盡全力讓罪孽塵封於心。
誕生花:美女櫻
花語:和睦、一切安好
他是古埃及第十三王朝法老王阿門埃瑪特朝時期到賽索斯特里斯時期的生命體,當時的他,和櫫獳一樣是植物身,只不過,被法老王發現了沙棘的功效里,有一種細菌能夠加速傷口感染,用來當刑具的話會讓犯人痛苦萬分。
後來,這一恐怖行徑驚醒了貓神貝斯特拉,貝斯特拉降下雷電和暴雨來懲罰人類,可曾想一道雷電擊中銅柱上的犯人,犯人被劈的焦黑,那根沙棘便是後來的克法,此時,他因為雷電的力量,而進化出了人形,無知的他被卡斯特的自由所吸引,然後,成為了令人聞風喪膽的時空沙棘僱傭者,為埃赫戰爭服務。
埃赫戰爭中殺人無數的恐怖魔物便是他,自此,埃及人打敗了西臺人的進攻,隨後賽索斯特里斯去世(死時不滿三十歲,也是罪有應得),繼位的是培羅斯法老,這位法老膽子略小,年齡略小,害怕父親時期的一切魔物會對自己造成影響,於是下令驅逐,克法被驅逐出境之後,到了東方,繼續被人為僱傭,直至卡斯特沉眠之後,才被重新召喚出來,並第一次以正常人的面貌示人。
衛冕和平的道路上,有偉大的勝利就一定有偉大的死亡,克法不是第一,更不是最後,衛冕需要成千上萬的志願者慷慨赴死,這是時代的鐵律,罕有不流血的革命,或是說,所有真理的詮釋都是用血換來的。
他的存在,就好比是早春三月匆匆爬上枝頭的美女櫻花,急於綻放,毫不在意天氣是否乍暖還寒,不在意是否適合盛開,他所在乎的只有對自由的渴望,急不可耐的高調的在枝頭舞蹈。
櫻花是注定充滿了悲傷的花朵,繁華盛雪,難掩淒涼與嬌柔,獵獵盛放,灼灼其華之後,總會在最美的時候,被和煦的春風吹過後,凋零成滿地的碎片。
克法·撒魯姆森,與諸多對自由懷揣夢想的志願者一樣,為了推翻封建帝制,否定奴隸制與獨裁君主集權,寧願最早的盛開在嚴寒之中,不畏懼封建的侵蝕和凍結,為了不朽的信念和堅定的意志,哪怕香消玉殞在完美盛開的地方,也無所畏懼。
科爾雅·維根·瑪格達:與政治永遠絕緣,只為謀求心理的寬恕。
誕生花:旅人蕉
花語:大無畏精神
她出身富貴,是維根王朝末期的公爵之女。
耀眼如白金在太陽下的璀璨光輝一般的白色長髮,幽藍的瞳孔中一絲鬼魅的淺紫游弋在瀚海般的視野之中,水滴狀的鼻樑是北歐中部地區人特有的象徵,連同那幽藍色的瞳孔,都是為之驕傲而自豪的象徵。
年少的她早早的經歷過了國家敗落,親人死於國政者之手,僅僅是平白無故的牽連與莫須有,就能隨便踐踏忠直之人的忠心,哪怕天地可鑑,也無濟於事。
失去了父親的她流浪在丹麥王朝統治下的德黑蘭島,沒有親人和依靠,只能乞討或者靠撿拾垃圾賺取僅有的為數不多的黑麵包。
而迦賽爾與母親的出現,卻好似是打開了一扇幸福的大門,只可惜這扇門關閉的又太早。
她不知道或者依然沉浸在自責之中,是自己為他們帶來了威脅,在墓地祭奠那天,是卡斯特的出現讓她第一次擁有了力量,卻也是卡斯特毀掉了她剛剛信任的母子二人。
迦賽爾的母親特洛托科索夫人,用死亡在她的心底植入了感情和幸福的種子,用獻身讓她明白了家人的作用,哪怕悲劇來的太過突然,她也只能在沒有力量的時候悄然接受,裝作毫不知情。
被帶到東方之後,安排在空幽的手下,在漠北靠恐嚇牧民換取羔羊作為保護費。
其實這一切無不是空幽的所作所為,他重傷科爾雅唯一的非血緣的弟弟,來恐嚇科爾雅用羊來換取他的生命,被蠱惑的她只能照做,空幽還不滿足,又將科爾雅的靈魂在睡覺的時候抽走並綁定在樺木上,從此她便植入了精靈族的體質,依靠樹木作為本體的精靈,雖然不完全是,但殘忍的改變,對於沒有力量的他來說,還只能是接受。
空幽又讓雪魁來製造謠言,謠言不脛而走,每一個牧民都遭受到了類似的恐嚇宣傳,相傳倘若不交羊的話,那么雪災會將村莊吞沒,看似無力的謊言,實為宛如一頂以死亡的人性加冕的罪之冠冕,讓科爾雅再也不願意服從這一道指令,她屢次放走到手的獵物,寧願連聲道歉也不願意用魔的力量強壓人類,對於空幽雪魁他們來說,這便是愚蠢,好在廣陵戰役之後卡斯特的老巢慘遭毀滅性的打擊,而空幽在撤離的途中被我們的主角們合夥擊斃,雪魁到處亂竄,逃到位於商洛的墓穴營地。
而科爾雅被櫫獳勸說放下屠刀,欣然接受一份和平,她說她永遠與政治絕緣,因為她不會忘記那是殺害父親的利器,永遠埋藏在心底的仇恨,會在最後一刻醞釀出怎樣的衝動。。。
德黑蘭的旅人蕉,雖說是外來且屈指可數,但同時又如她可貴的內心在這個世界上顯得珍貴而脆弱無比,喜好溫暖卻被移栽在殘酷的冰原,命運的不公讓她有了她的信念和她的奉獻,以及對他的始終堅守,終將會將千年沉澱的冰雪化作一股心裡流淌的暖泉,她是否能放下塵封的悲哀枷鎖,欣然接受這一份快樂。
請一定要相信,不管過去怎樣黑暗,所有的黑暗僅僅只是在襯托黎明的璀璨,因為太陽需要夜的開幕,才能更加盛大壯麗而輝煌,否則平白無故的成功將顯得太過做作且浮華喧囂,沒有深刻的含義會成為過往的雲煙被人所恥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