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不起的蓋茨比》劇照
點開社交分享平台和購物軟體,我們總是會被鋪天蓋地的種草推文和直播間裡激昂的倒數聲沖昏了頭腦,按下“立即購買”的按鍵。消費似乎已經入侵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毛孔中,有人對此感到了警惕。
在一個叫“不要買 | 消費主義逆行者”的豆瓣小組中,組員們會互相分享商品“勸退”的心得體會,從而實現“不購買”的目標。
但是,存下來的錢是不是終究要為消費存在呢?我們購買的時候,買的究竟是商品本身的功能還是它的符號?產品實質上是類似的,為何同類商品又有如此多琳琅滿目的選擇?我們不購買非必要物品,就能逃脫消費主義的陷阱嗎?今天的硬核讀書會,帶你走近這個充滿陷阱的消費社會。
✎作者 | 王一恪✎編輯 | 張文曦
一個下午,你從午睡中醒來,蜷縮在去年夏天花費三倍於平均價格購買的網紅夏日空調被中,點開社交分享平台,首頁推薦的是一款具有流暢幾何外形的極簡風畫框。你心動了,往下滑動,發現評論區點讚最多的一條是“這是消費主義陷阱”。
你開始思考,這個畫框似乎並不是生活的必需品,有沒有它,生活都不會有多大變化。這筆錢似乎是一筆可有可無的開銷。“那確實是一個想要騙我錢的陷阱,”你心想,“那這床被子是不是也是消費主義陷阱?”看著家裡的一切,那台將近兩萬塊卻只用來碼字的電腦、成堆的一次性擦臉巾、買回來一年多隻帶出去過三次的相機,以及衣櫃裡一半連吊牌都沒有拆過的新衣服。
突然之間,你感覺自己生活在一個由陷阱編織的網中。但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這一切非必要的開銷都是消費主義陷阱,那隻購買生活必需品,存下絕大多數收入,這些錢要用來做什麼呢?它們不就是為消費存在的嗎?購買生活必需品也是一項消費,它是消費主義嗎?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一切非必要的消費都被扣上了“消費主義陷阱”的帽子?

/Unsplash

消費主義的蔓延
在法國學者安東尼·加盧佐的《製造消費者:消費主義全球史》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消費主義如何像蜘蛛網一樣悄悄爬滿我們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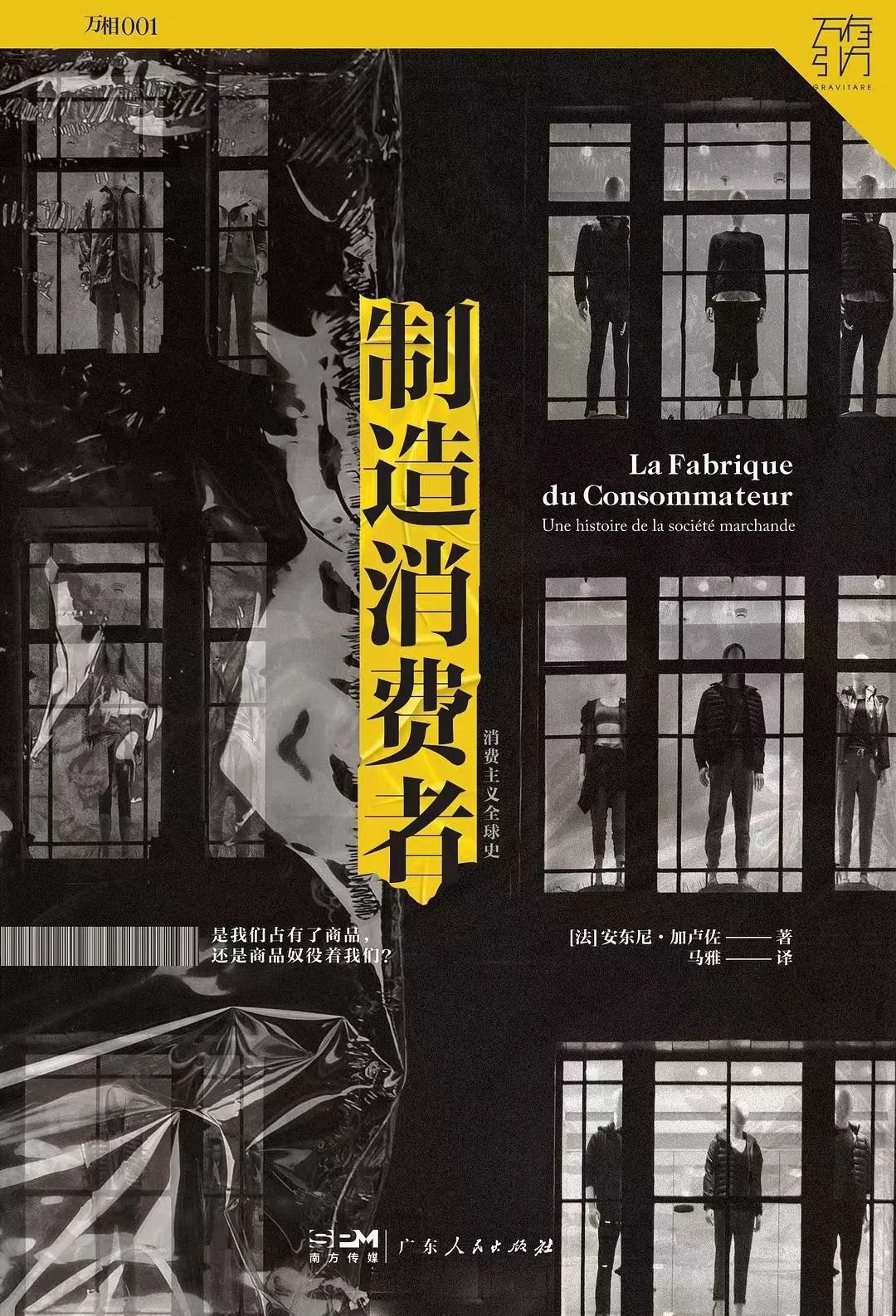
《製造消費者:消費主義全球史》
安東尼·加盧佐 著,馬雅 譯
萬有引力 | 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6
如果說我們現在的世界是一個消費社會,與之相對的,在19世紀以前,世界還是一個小型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人們自己生產自己所需要的物品,這些需求在村落中基本上都可以得到滿足。最重要的是,在這樣的小型社會中,人們知道自己使用的工具、送進胃裡的食物和身上的衣服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
從農業社會到消費社會的背後,是技術的變革。19世紀,蒸汽機的效率大大提高,蒸汽機車的誕生使得穩定的長距離運輸不再是一個夢想。朱西甯在《鐵漿》中描繪了一個小鎮通行火車的故事。通車前,人們想:“鐵路鋪成功,到北京城只要一天的工夫。那是鬼話,快馬也得五天,起早兒步輦兒半個月還到不了。”而通車後,“火車帶給人不需要也不重要的新東西;傳信局在鎮上蓋了綠房屋,外鄉人到來推銷洋油、報紙和洋鹼。”

距離不再是商品流通的障礙,人類也就在物質追求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Unsplash
傳統的生活方式被先進的技術所終結,新的生活方式建立在過剩的生產力之上。商品運輸的阻礙被消滅了,剩下的就是怎么把商品賣給本不需要它的人了。如加盧佐語,當“速度戰勝了距離,距離不再是商品流通的障礙,人類也得以擺脫了自然條件的束縛,在物質追求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在消費社會中,這種物質追求僅僅是對物品本身的崇拜,而物品背後生產過程中的勞動都被隱藏了起來。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根據小麥的味道,我們嘗不出它是誰種的,同樣,根據勞動過程,我們看不出它是在什麼條件下進行的:是在奴隸監工的殘酷的鞭子下,還是在資本家的嚴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納圖斯耕種自己的幾畝土地的情況下,還是在野蠻人用石頭擊殺野獸的情況下”。

消費者被隔絕於生產過程,難以感知背後的勞動。/《摩登時代》劇照
但這種拜物情結是脆弱的。正是因為看不到商品背後的生產過程,我們無法對商品的成本、價值、質量作出合理的判斷。以前人們相信自己的雙手,相信自己的眼睛可以看見水稻如何種植、成熟、收割,最後端上餐桌。然而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只剩下一具物質的空殼。

當商品不只是商品
當空殼被包裝得足夠美麗,它就在暗示我們為其付出的一切是值得的。法國社會學家讓·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認為,構成消費社會的不是購買這種行為,而是商品所代表的符號的力量,即商品本身並不是商品,而是本身無法被具象化的那些真的重要的東西的代表。

《消費社會》
讓·鮑德里亞 著,劉成富、全志鋼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10
如卡爾維諾所描述的:
“就連商販在貨攤上陳放的商品的價值也不在於其自身,而在於作為符號代表其他什麼東西:繡花的護額帶代表典雅,鍍金的轎子代表權力,阿威羅伊的書卷代表學識,腳鐲代表淫逸。”
而購買者也沉浸在這種由轉譯構造的假象中:“你的目光很難停留在一個物體上,只是在認出它是表明另一事物的符號時才會駐目觀察。”

鮑德里亞用一則寓言來描述我們和商品之間的關係:我們看見商品就如同美拉尼西亞的土著人看見飛機,土著人通過布置燈光和用樹枝、藤條模擬的飛機,來等待飛機的著陸;而消費社會中的人們則通過擁有豐盈的商品來等待幸福的降臨。
《製造消費者》中,加盧佐指出商品對美好生活的許諾是通過圖像傳播的。19世紀中葉開始,得益於廉價的印刷技術,商家開始通過圖片來宣傳產品。
這種利用直觀的視覺衝擊給消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宣傳效果是無與倫比的。品牌的誕生最初是為了解決產品生產背後的信任問題,但隨著廣告的力量越來越強大,品牌的形象早已不只代表“信任”。加盧佐發現:“品牌不僅僅能給人安全感,還有其神秘力量,能通過符號工程將商品和社會文化價值聯繫起來。”
我們今天會在超市貨架上遭遇數十種不同品牌的相似產品,從中選擇出最適合自己的那一款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因為我們擁有的信息只有可憐的原料表以及一個由深諳認知科學的團隊設計出的品牌標誌。
在這樣的信息差下,我們的選擇與其說是對商品的挑選,不如說是對自己社會身份的定位。在這樣的環境裡,“人們可以通過消費來‘發明’自己的身份”。

人們通過消費來“發明”自己的身份。/pixabay
但是人們還是不可自拔地沉迷於這場貼標籤的遊戲中。不需要創造任何東西,只是通過消費就可以獲得對自己獨一無二的定位。
加盧佐在對於消費心態的論述中,提到了過去的集體秩序和集體精神本質上是反消費的。大多數人的生存離不開自己所在的社群,同時貨幣是用來救急,而不是生存的,因而不消費是一種美德。
然而到了今日,我們已經習慣了用自己的勞動換取金錢,再利用金錢通過市場滿足自己的需要。市場的存在使人不必把自己的生存寄托在一個社群中,一個人也可以滿足所有生存的需要。同時大量的消費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多物品被生產出來,享樂主義占了上風。
現在的人從過去真實的社群解放了出來,加入了由消費品所定義的想像中的社群里。這也意味著一個人可以隨心所欲地變換自己的身份。齊格蒙特·鮑曼在《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中如此描述這種性質:“重要的是一個人能做什麼,而不是應該做什麼或已經做了什麼。富人普遍受人愛戴是因為他們選擇自己生活的神奇能力(居住的地方、共同生活的伴侶),並能隨心所欲、不費吹灰之力地改變它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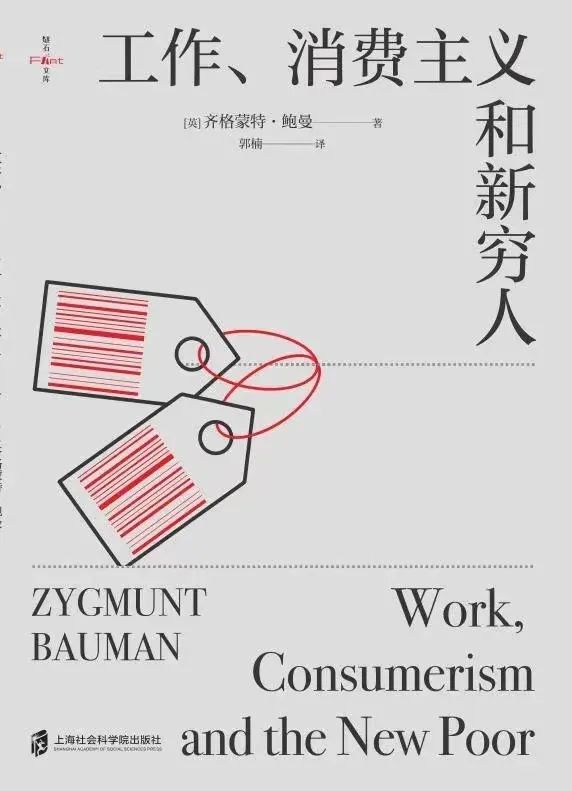
《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
齊格蒙特·鮑曼 著,郭楠 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9
如此多的選擇被擺放在我們面前,我們還能奢望什麼呢?

個性的悖論
年輕人是商業社會永遠關注的中心。從00後成為大學新生主力軍後,關於Z世代的商業研究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層出不窮。
然而Z世代對這些研究卻嗤之以鼻,他們對於這種研究的態度很明確——我不需要任何人來定義,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表我,甚至“Z世代”這個標籤也是毫無意義的。

不想被定義的Z世代。/維基百科
然而一個殘酷的事實是,每一個消費社會的原住民都曾是追求個性的年輕人,而每一代年輕人都無法逃離被擁有更多信息和豐富經驗的商家收割錢包的命運。
加盧佐在《製造消費者》中以“漫長的60年代”為例,展現了年輕人對主流文化的反叛是如何再次成為資本累積的助推手。
在以符號物劃分的想像社群的社會中,與主流文化劃清界限的方式“只有通過對符號物的展示和擁有”。這種對符號物的占有恰恰又是一次消費的過程,就像是在一個封閉的迷宮中不停地打轉。這種反叛和“不想吃西瓜,所以要吃草莓”可能並沒有本質差別。在鮑德里亞看來,“對差異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別喪失的基礎之上”。
“細分市場”這一概念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被提出,或許可以說,人們對於獨特的追求催生了一大批品牌。如同寶潔、聯合利華這些大型公司所做的那樣,利用廣告,推廣上百個不同定位的品牌,然後把這些化學成分類似的日用品賣給對自己的定位完全不同甚至對立的人。
如同加盧佐所說的那樣,“反主流文化的‘情緒’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強化劑,它打破了保守主義的秩序、刺激了商業。同時,這些藉助符號物展開的鬥爭和人們對自我的追求卻並沒有對政治產生真正的影響,人們不斷強調這些意識的解放,但是卻對革命最基本的價值問題、制度問題、生產和利潤的分配問題避而不談,顯得不痛不癢。”

不“買買買”就可以獨善其身嗎?
消費可能真正地做到了“像水一樣”,普通、平凡、隨處可見,卻又是我們生活的基石。可能除了空氣,食品、衣物、水,這些我們賴以維生的必需品都已經被消費浸沒。沒有人可以逃脫這個詛咒。我們或許可以如此認為,我們消費的任何東西,都一定程度上把符號賦予了我們。
不“買買買”,獨善其身也似乎並不可能。在加盧佐看來,這不過是“魯賓孫式文學”,是“不切實際的自我欺騙,仿佛人可以擺脫社會主導,擺脫一切外界約束”。
在上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中,20歲左右的美國青年們遊蕩在街頭。在瓊·狄迪恩筆下“市場穩定,國民生產總值高,多少人慷慨陳詞,表達自己崇高的社會理想”的環境中,“青少年們在外遊蕩,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如同長蛇蛻皮;孩童懵懂無知,也再無機會了解維繫這個社會的遊戲規則。人們銷聲匿跡。孩子不知去向。父母人間蒸發。被地下的人們漫不經心地填寫完失蹤報告,然後自顧自地繼續活下去。……我們見證了幾個手無寸鐵、可悲可嘆的孩子,正在孤注一擲地努力,想在這個空虛社會中創造一個社區”。

《製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劇照
然而更加荒謬的是,投身於嬉皮士運動的人,大多數都來自中產階級家庭,他們想要擺脫“中產階級弗洛伊德式的煩惱”。這種對於自我的探索本身就是一種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的奢侈的煩惱。然而,靠左腳踩著右腳,永遠也無法飛上天空。
在種種誘惑和本能的驅使下,我們最終走到了這一步。回到社交媒體上鋪天蓋地的對消費主義陷阱的批判,就算避開了這些所謂的陷阱,不買“智商稅”的高價日用品,避開了超市冰櫃裡的“雪糕刺客”,生活的底色依然是消費。降低欲望,躺平“擺爛”所獲得的抽離,不過是假象罷了。
參考資料:1.《製造消費者》2.《消費社會》3.《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4.《向伯利恆跋涉》5.Davi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69: 82. ISBN 0-521-094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