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鐸王朝處於英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關鍵時代,因而其實施的各項政策也極具時代特色。都鐸時期英國的政體性質十分獨特和複雜。一方面,都鐸王權空前強大,在國家權力結構、政治法律體制和君主的統治行為方面都呈現出不可否認的專制趨向 ;另一方面 ,都鐸諸王基本上是遵照“政治程式”行使其統治權的 ,因而又處處表現出明顯的法治特徵。結果 ,原本根本對立的專制和法治不合邏輯地共存於都鐸政體中,形成奇特的“都鐸悖論現象。它是從中世紀向近代過渡時期建立民族主權國家的時代需要和英國獨特的憲政法制傳統共同導致的必然結果。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都鐸悖論
- 性質:概念
- 所屬時代:都鐸王朝
- 所屬國家:英格蘭
王朝簡介,專制趨向,法治特徵,專製法治之間,
王朝簡介
都鐸王朝(Tudor dynasty),是1485至1603年間統治英格蘭王國和其屬土的王朝。歷時118年,共經歷了五代君主。始於亨利七世1485年入主英格蘭、威爾斯和愛爾蘭,結束於1603年伊莉莎白一世的去世。
專制趨向
在都鐸之前的中世紀,英國國王雖是國家權力的中心,而且比之歐陸各國的王權都更為強大,但是,在它的周圍同樣存在著三大難以超越的制約力量:一是貴族集團,二是教會勢力,三是中產階級。
英國的貴族就個人力量而言,當然是無力與王權抗衡的,但貴族們的聯合力量卻足以與王權分庭抗禮,而且正是因為前一條原因,英國的貴族為了維護和擴大自己的封建權益,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聯合一起與國王鬥爭,並屢屢獲勝,迫使國王俯首讓步。1215年《大憲章》和1258年《牛津條例》的訂立就是兩個最典型的事例。英國天主教會作為龐大的國際宗教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憑藉羅馬教廷的強大後盾和自身控制的約占全國1/3的土地資源以及思想文化領域的壟斷地位,始終在中世紀英國的權力舞台上扮演著一個顯赫的重要角色。由農村鄉紳和城市市民組成的中產階級是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崛起於13世紀的一支新生力量,儘管那時它的政治功能和影響明顯弱於貴族和教會,但它手中的巨額財富和蒸蒸日上的發展潛勢,特別是作為國家主要稅源的不可替代的特殊財政地位,決定了它必然成為一支不容王權忽視的政治力量。在這樣一種多元型的力量對比結構中,中世紀的英國王權雖然較為強大,足以維持國家的政治統一,但絕無可能超然凌駕於其他三大勢力之上而建立君主專制。
進入都鐸時期,英國的政治力量對比結構根本改變。貴族集團在玫瑰戰爭中元氣大傷,勢力銳減,許多名門望族身死家滅,殘留的貴族世家屈指可數,就總體而言,貴族集團呈江河日下之勢,再也無力在政治舞台上“興風作浪”,個別貴族甚至不得不靠仰王權之鼻息而苟延殘喘。教會勢力在宗教改革中遭受致命打擊。教產被沒收,修道院被解散,修士被勒令還俗,教皇勢力被驅逐。主教必須根據國王的提名選舉產生,宗教大會制定的法規須經國王批准才能生效。教會法庭不得違反國家法律和國王命令,不得把案件抗訴羅馬。獨立的神權王國被摧毀,國王成為僧俗兩界共同遵從的最高首腦。保持近千年的王權與神權並立、教會與世俗政權對抗的二元社會結構被神權服從王權、教會隸屬國家的一元社會結構所取代,英國變成了一個以國王為化身的真正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這時的中產階級(即形成中的資產階級)雖然隨著資本主義的長足發展其經濟勢力進一步增強,但尚未強大到對王權提出挑戰的地步,更沒有產生奪取統治權的政治要求,相反,他們仍然需要王權羽翼的保護,因此,這個集團還不是王權的異己力量,而是王權的支持者。
正是在上述新的政治力量對比結構下,都鐸王朝順利地通過埃爾頓所說的“政府革命”,從政治體制上強化了王權。在中央政府中,原先的因受制於貴族的宗派之爭而鬆散無力的諮議會被新成立的樞密院取而代之。樞密院由國王欽命大臣組成,他們多出身社會中下層,對國王忠貞不二,而且精明幹練,辦事迅捷,是都鐸專制王權最得力的統治工具。議會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權力實體繼續矗立在王權身邊,在國家政治上層建築中仍然占據著不可動搖的重要一席,但它的政治脾性似乎略有改變,與前兩個世紀相比,議會與王權之間的對立衝突減少了,合作與支持增多了,在宗教改革、王位繼承、對外戰爭等重大決策中,國王的意見都能輕而易舉地取得議會的贊同,難怪某些西方學者把都鐸議會稱作“奴性十足的國王馴服工具”。在地方政府中,都鐸王朝擴大了各郡治安法官的職權,把他們變成了中央王權的“雜役女傭”,全權負責一切地方管理。為防範治安法官的地方主義,都鐸王朝創設了郡尉制,每郡設郡尉一人,通常由樞密大臣兼任,他們除負責徵集、訓練、指揮民兵外,還有權推薦治安法官人選,監督其工作。在郡以下,都鐸王朝把過去的教會組織教區改造為一級行政組織,取代了自治性較強的百戶區和村鎮,原有的教區大會已形同虛設,權力集中於由教區執事、濟貧員、公路檢查員組成的小型教區會議手中,而教區會議又處於治安法官的嚴密監督和控制之下。這樣,一套帶有明顯專制主義傾向的政治體制建成了,王權的觸角從橫向說擴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縱向說伸展到最基層的普通居民。
如同政治體制一樣,都鐸時期的司法體制也發生了趨向專制主義的變化,這集中體現為一系列特權法庭的建立。它們包括:一是刑事特權法庭即星室法庭,它由樞密院大臣和王座法庭、普通訴訟法庭的首席法官組成,不用陪審制,而採用流行於大陸各國的糾問式審判法,並可以對被告或證人進行刑訊逼供。二是民事特權法庭即懇請法庭,它原是諮議會的一個委員會,後獨立出來,演變為一個專職法庭。三是財政特權法庭,包括土地沒收法庭、監護法庭、王室地產檢查員法庭和首年俸法庭等專門法庭。四是宗教特權法庭,包括高等代理法庭和高等委任法庭兩種。前者主要受理主教法庭和大主教法庭的抗訴案件,後者則是一個貫徹宗教改革法規、鎮壓宗教異端的初審法庭,類似於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它們都是由國王任命的特別專員組成。五是地方特權法庭,即威爾斯邊區法庭和北方法庭,它們是上述兩個特定區域的全權統治機構,但以司法為主。最後,產生於15世紀的衡平法庭大法官庭可算作一個半特權法庭,因為雖然由它實施的衡平法這時已開始走向規範化和體系化,但由於它把公平、正義、道德、良心奉為至高原則,繼續保持著其固有的靈活性,審判方法又較為簡便隨意,因而給大法官保留了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的餘地。特別是大法官作為國王親信、朝廷重臣和樞密院要員,與國王的關係十分密切,因而很容易為國王所利用,充當王權的專制工具。實際上,每當王權與法律之間發生激烈衝突時,大法官及其主持下的大法官庭總是站在王權一邊。
憑藉新建特權法庭和改造後權力更為集中的政治體制,都鐸王朝的政治統治行為呈現出明顯的專制主義特徵。在立法上,都鐸王朝雖說對議會的立法權是尊重的,但也經常採用操縱議員選舉、控制議長人選、蒞臨議會訓話、逮捕反對派議員等手段,施展君威,以影響議會的立法進程和結果。例如,1532年,下院對涉及國王封建權利的一項政府議案提出批評,亨利八世得知後立即召見下院代表,警告他們說:“希望各位適可而止,否則朕會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採取極端行動。”迫於國王淫威,下院通過了該議案。當《禁止抗訴法》在上院遭到高級僧侶的反對時,亨利八世親臨上院,使該議案強行通過。瑪麗女王在這方面比之其父有過之而無不及。伊莉莎白一世對議會採取的是恩威並用的策略,她時常為議會討論劃定範圍,不準越雷池一步。1593年,掌璽大臣警告下院議長說:“陛下讓我告訴你,所謂言論自由就是對議案說‘yeas or no’”在她統治期間,兩院議員基本上都是女王的“馴服臣民”,但偶爾也有不順從的舉動,如在1586—1587年的議會上,清教徒議員們提出了“一個具有革命性的議案”,企圖以長老會代替國教的主教管理機構,這是對教會最高首領國王決定宗教事務之專有權力的公然挑戰。女王聞訊後大怒,下令將議案的提出人彼得·溫特沃思等5名議員全部投入倫敦塔監獄,並派幾位樞密院大臣去下院“就清教徒的議案會發生的後果作了說明。這就用一種強制與說理相結合的手段粉碎了清教徒在議會的中此次行動。”可見,那時威脅到國王利益的議案是很難通過議會的。如果與議會發生尖銳衝突,國王還可以動用議會解散權使審議過程中的議案中途夭折,或者行使否決權將議會通過的法案扼殺於生效之前。在伊莉莎白一世時期,幾乎每屆議會都有法案被否決掉,其中1597年被否決12項,1601年被否決8項。
都鐸王朝的專制主義特徵在司法領域表現得更為明顯。國王特權法庭不時藉口“案情特殊”或“無先例可循”,把案件從普通法法庭中奪走,置於自己的自由裁量權之下。如果在特權法庭和普通法法庭之間發生司法許可權之爭,樞密院往往以仲裁人的身份出現,並總是站在特權法庭一邊。有時樞密院藉口國家安全需要,直接命令法庭擱置、推遲某一案件的審理,或具體指示案件應如何判決。一個典型的案例是,1591年樞密院命令某監獄長拒絕執行法庭的人身保護令狀,並要求該監獄長在給法庭的回執中聲明逮捕是根據女王的特別命令進行的。如果案件涉及政府官員,樞密院則以他們是“國王的僕人”為由出面保護。有一次,一個國王優先採買員強行低價購買居民的木材,被普通法法庭定罪,此人聲稱“如此處理將使國王蒙受恥辱”,轉而求助於樞密院,結果免除了懲罰。特殊情況下,國王甚至親自出馬,干預司法,如1517年的某一天,亨利八世親臨王座法庭,命令把倫敦塔的所有犯人帶到他面前,並“寬恕了他們”。
都鐸司法的專制趨向更突出地體現在嚴刑峻法上面,特別是在與王位繼承和國王個人利益密切相關的政治性案件審判中。例如,亨利八世的第二位妻子因說了一句“國王從未贏得她的心”而以叛國罪被處死刑;其第五位妻子凱瑟琳因出嫁時不是處女而被斬首;埃塞克斯伯爵因沒有預先告訴亨利八世其第四位新娘“相貌醜陋”而被判處叛國罪;薩里斯伯利伯爵夫人因兒子接受了羅馬紅衣主教而被判極刑。伊莉莎白一世時期,女王身邊的情人和寵臣們始終生活在生命危險的陰影中,稍不留神便招致鐵窗之苦,甚至殺身之禍。女王的情人哈特福伯爵因擅自結婚,被女王宣布為非法,罰款15000鎊,伯爵逃亡國外,他的妻子被監禁, 當這位伯爵回國後也被關進倫敦塔。阿倫德爾伯爵在成為女王情人後因繼續與原配保持夫妻關係,結果被判極刑,多虧幾位老臣拚命相救才倖免一死。
在都鐸時期的刑事案件審判中,嚴刑拷打司空見慣,尤其在特權法庭中,鞭打、割耳、斷肢、頸首枷都是常用方法。伊莉莎白一世曾下令對一個猶太犯人施用拉肢刑架;首席法官雷有一次直言不諱地承認,經他審判的一個犯人完全是憑刑訊取得的口供而定的罪;甚至連空想社會主義者托馬斯·莫爾在任大法官期間也拷打過犯人。有時法庭不惜採用卑鄙的誘供手段,或根據莫須有的傳聞即可定罪,羅徹斯特主教約翰·費舍一案就是典型的一例。這位主教因對《至尊法》態度曖昧, 未置可否,被關進倫敦塔。一天,靠阿諛奉承而升任總檢察長的理察·里奇假裝探監,對獄中的費舍說,希望當面聽聽他的真實想法,並謊稱國王已許諾決不將他們的談話內容泄露出去。信以為真的費舍毫無顧慮地表示反對《至尊法》,說該法案等於宣布上帝不再是上帝了。數日後,法庭開庭,判處費舍死刑,唯一的證據就是他和里奇的獄中談話。對蘇格蘭瑪麗的審判則完全是一場荒唐鬧劇,其罪名是她曾寫信請求西班牙國王幫助她奪取英國王位和在英國恢復天主教,而這封信實際上是一名謊稱西班牙國王信使的政府密探誘騙她寫的。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都鐸時期尖銳的宗教衝突加劇了司法的殘酷性。亨利八世時,天主教徒慘遭迫害。那時的大法官托馬斯·奧德利是個宗教偏執狂,他制定了一批嚴厲的法律,凡是承認教皇至上者皆被砍頭,異教徒通通被燒死。除上面提到的費舍外,莫爾和倫敦的一位修道院長都是因為拒不同意國王是教會最高首領而被處死的。到瑪麗女王時,天主教徒重新得勢,新教徒又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據統計,該時期被處以火刑的非天主教徒達300多人。原有的新教徒法官為保全性命,紛紛違心地皈依天主教。著名法官詹姆士·黑爾斯最初猶豫不決,後在同僚的勸說下勉強接受了天主教,但一直遭受著良心的譴責,後來沉湎於酒,憂鬱而終。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法治特徵
都鐸王朝的專制主義特徵是不容否認的,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從另一方面看,都鐸王朝的統治又表現出濃厚的法治傾向,因為從總體上說都鐸諸王基本上都是遵循當時的法學家蘭巴德所說的“正當法律程式”進行統治的。在英國,所謂“正當法律程式”指的是經過長期歷史積澱形成的規範國王政府統治方式的基本政治法律原則。依“正當法律程式”行事,意味著都鐸王朝是一個尊重法律的王朝。
在立法上,國王雖占據主導地位,但所有重大立法只有藉助議會的參與和同意才能完成。都鐸議會曾多次否決國王政府的提案,甚至連愛德華六世親自參與起草的12個議案都被議會拒絕。因此,國王要想制定新法律,只能利用、引導議會,而不能繞過、甩開議會,是為立法的“正當法律程式”。當然,國王享有在議會外會同樞秘院發布公告的權力,而且這一權力在1539年得到了議會《公告法》的肯定。《公告法》聲稱,國王為了基督的宗教、王國的發展和人民的安寧,已發布過許多公告,但有些人認為公告是國王個人發布的,所以沒有很好地遵守。鑒於此,特作如下規定:在緊急情況下,根據樞密院的建議,國王可以發布具有議會法規同等效力的公告,並向全國公布於眾;樞密院有權責令治安法官保證公告的落實,有權成立專門法庭懲罰公告違抗者。(W·S·Hold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Vol4,1924,P103.)正是根據這一法規, 某些英國史學家認為都鐸國王獲得了通過公告隨意立法的特權,出現了國王個人立法取代議會立法的趨勢。其實,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因為《公告法》的第二部分明確限定了公告的效力範圍:“國王的公告不得與議會制定法和普通法相牴觸”,不得侵害財產權,違反公告者不得處以死刑。實踐證明,《公告法》頒布後,國王公告的數量、內容和效能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當1547年廢除《公告法》後,也未妨礙國王繼續頒發公告。看來英國學者卡爾的觀點是頗有道理的。他認為,《公告法》披著擴大國王特權的外衣,實際上削弱了國王特權,因為它以肯定國王某項既有權力的特殊方式,含蓄地宣告了這一權力是議會法規授予的,其邏輯結論必然是:國王的個人立法權是低於議會立法權的。
在都鐸時期,以擴大王權之名、行提高議會法規權威之實的立法遠不止《公告法》一項。例如,1504年的一項法規授予亨利七世以利用特許狀廢除1483年以後議會通過的剝奪公權案的“充分權威和權力”;1532年《首年俸法》授予亨利八世以特許狀形式決定該法規全部或部分內容生效的“充分權力和自由”;1534年的“豁免法”授予亨利八世以通過特許狀廢除包括《豁免法》在內的所有法規的“充分權力和權威”,並聲明就像通過議會制定法廢除法規一樣的有效。這些法規和《公告法》一樣,名義上是擴大王權,實際上卻成為王權的“阿基里斯的腳跟”,其客觀後果是樹立起了梅特蘭所說的“法規的絕對優勢”或埃爾頓所說的“法規的無限主權”。雖然不敢斷言上述法規制定者的初衷就是如此,但可以肯定他們是堅信議會法規具有至上權威的,因為在《豁免法》的序言中明確寫道:“根據自然平等和充分的理性,國王、上院和下院可以中止這些法規和所有其他的人為法律;可以授權某人不受這些法律的約束;可以廢除、補充、削減這些法律和所有其他的人為法律。”一句話,由國王、上院和下院組成的廣義議會是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
在行政上,都鐸王朝儘管不乏個人專橫行為,但基本上也是遵循歷史上形成的“正當法律程式”,即通過與議會協商行使其統治權的,這突出表現在與議會協商徵稅和決策上。
在徵稅方面,都鐸王朝雖然有時指示地方當局向居民強制貸款,拒絕者和貸款數額不足國王要求者甚至被樞密院所傳訊,有時藉口國防需要向沿海地區徵收船稅,但這些非議會稅收只有在特殊需要情況下才偶爾一用。就總體而言,都鐸王朝從未拋開議會強行徵收過一次全國性賦稅。據記載,1496年,諮議會曾擅自決定徵稅12萬鎊,但它同時宣布該決定只有經下屆議會批准後才能生效;1529年,首席大臣沃爾西曾試圖不經議會向僧俗兩界攤派動產稅,結果除了招致“破壞法律和自由”的責罵外一無所獲。1593年,當有人建議在重新估產的基礎上按年徵稅時,伊莉莎白一世通過宮廷副總管宣布,她無意改革賦稅制度,而寧肯“維持舊制”。因此,在徵稅問題上,都鐸王朝很少與議會發生衝突。
在決策方面,都鐸王朝從一開始就認識到,與議會協商既可以集思廣益,又能披上一件“公意許可”的合法外衣,從而有利於政策的順利執行;在處理某些棘手的外交問題時,還可以打出“議會不同意”的旗號,拒絕外國政府的無理要求。因此,都鐸諸王都樂意與議會協商共同治理國家。亨利八世在費勒一案中公開承認,當他與議會在一起時,其權力遠大於他在議會外單獨享有的權力。瑪麗女王於1554年在吉爾特大廳鄭重宣告:“除了有利於臣民的事情,她決不打算做任何事情,將來也是這樣”,並特別許諾“沒有議會的普遍同意,她決不結婚”。伊莉莎白一世在1558年11月說:“朕是上帝的創造物,注定要遵從上帝的任命,在目前我在的位置上成為上帝神聖意志的執行者。雖說根據上帝的旨意朕要統治整個國家,但朕只是一個普通的人,所以朕希望得到你們全體的幫助。……朕的意思是,你們通過良好的建議和協商指導朕的所有行為。”在實踐上,都鐸王朝在制定政策時,通常以議案的形式預先提交議會協商討論,經議會同意後再付諸實施。協商事項十分廣泛,大到宗教改革、解散修道院、變更王位繼承人選、修改叛國罪法、改造政府機構、規範度量衡和幣制,小到鋪設城市輸水管道、禁止夜間在塞文河上擺渡、保護魚卵、禁止射殺益鳥等區區瑣事,均列入與議會協商討論的範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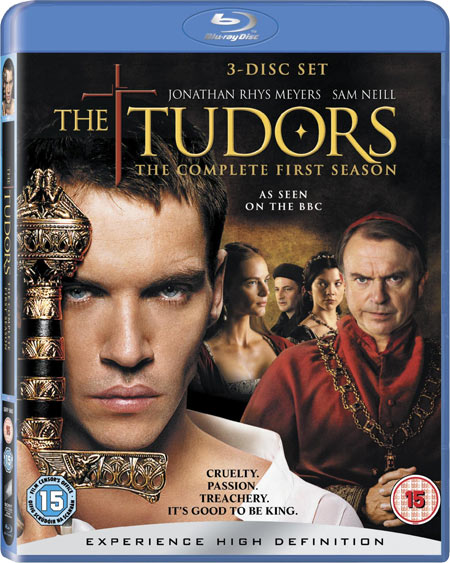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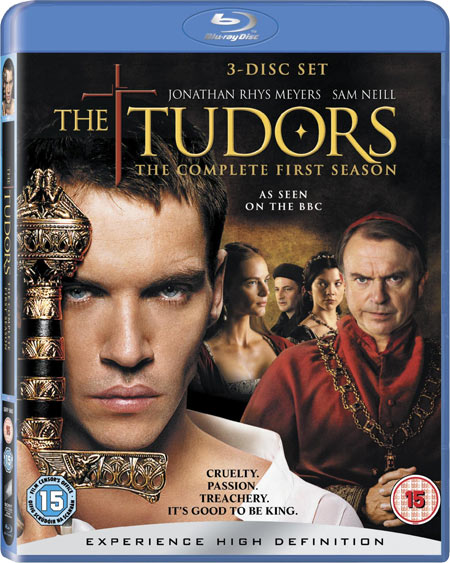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如果說在立法和行政方面都鐸英國的法治特徵集中體現在國王政府按“正當法律程式”進行統治的話,那么,在司法方面則主要表現為普通法和普通法法庭繼續保持著其主導地位和相對獨立性。
形成於12-13 世紀的普通法由於主要源於約定俗成的習慣和法官判例的積累,因而自產生之日起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對獨立性。而且,普通法作為歐洲歷史上第一套成熟的民族國家範圍內的法律體系,較早建立起一套覆蓋全國的專職法庭組織,它由三大中央法庭,即固定於威斯敏斯特的普通訴訟法庭、王座法庭、財政法庭和定期巡迴全國的巡迴法庭組成,到中世紀後期,由治安法官組成的各郡季會法庭的建立,使得這套司法組織體系更加完善。普通法還有訓練有素的職業法官和律師隊伍,有富於成效的法律教育和人才培訓機制,有健全的自治性行業組織。藉助於這些當時其他法律體系都不具備的優勢條件,普通法得以始終保持著其主導地位和相對獨立性。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到16世紀普通法已深深地融入英國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傳統中,受到社會大眾的普遍鐘愛。都鐸早期威尼斯駐英大使對此深有感觸,他說:“如果國王試圖改變任何一條原有的(普通法)既定法律原則,那么,每一個英國人都將視之為是剝奪自己的生命。”學者們普遍認為,16 世紀正是英國普通法教育的黃金時期,四大律師學院生源劇增,許多學員在學院內租不到公寓,不得不寄宿校外。由它們培養出來的職業律師和法官已成為一支強大的社會力量,“沒有一個郡、城、鎮,也很少有一個村沒有他們(律師)。”這個法律職業階層以訴訟為生,視普通法為安身立命之本,他們本能地維護普通法的主導地位。雖然普通法法庭的高級法官由國王任命,但法官的薪俸主要來源於法庭的訟金收入,而非國王提供。因此,受理的訴訟越多,法官和律師的訟金收益就越大。利益驅動使他們必然努力豐富普通法的內容,拓寬其調節範圍,以便儘量多地招攬訴訟。在這方面的一個突出例證就是,在中世紀時,商業案件都是由適用商法的城市商事法庭審理的,普通法法庭從來不加干涉。但進入16世紀後,普通法法庭開始吸納商法,把它作為普通法的一部分, 從而逐步確立起對商業案件的司法管轄權。而且,普通法法庭還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大陸國家的國際性商法,這就進一步拓寬了它的司法管轄範圍和適應性。
誠然,衡平法的發展、特權法庭的出現的確對普通法和普通法法庭構成一定的威脅,但並未動搖其主導地位,因為衡平法和特權法庭只是作為普通法和普通法法庭的一種補充而存在。星室法庭的主要作用之一是保護普通法法庭執行法律,懲辦蔑視法庭、抵制司法判決等行為,它從未企圖受理叛國罪和重罪案件。在其他刑事審判中,都鐸王朝始終堅持的一條基本原則是:只要普通法法庭有能力伸張正義的案件,就保留給普通法法庭處理;凡是向星室法庭投訴的當事人,必須提出充足理由,以證明其案件在普通法法庭上難以得到公正審理。因此,星室法庭所受理的案件主要是因當事人過分強大而普通法法庭無力將其繩之以法的案件、直接涉及國王利益或國王僕人的案件及普通法上缺乏明確規定的誹謗、偽證、造假等案件。懇請法庭設立的主旨之一是解決普通法法庭訴訟費用昂貴所產生的貧民無力起訴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北方法庭和威爾斯邊區法庭的建立有助於提高普通法的權威,因為正是它們真正把普通法推廣和落實到西南和北部邊陲地區。衡平法和大法官庭的主要作用也是彌補、匡正普通法和普通法法庭的不足和缺陷,它們始終處於依附於普通法和普通法法庭的從屬地位,這一點從當事人投訴時對兩種法庭的選擇順序就能看得一清二楚:16世紀時,三個普通法中央法庭和大法官法庭都設在威斯敏斯特大廳,各占據大廳一邊。當事人一般首先向普通法法庭申訴,只有當他認為在普通法法庭中無法討得正義時,才穿過大廳向適用衡平法的大法官法庭尋求救助。當然,樞密院可能認為特權法庭有權越俎代庖,受理本應屬於普通法法庭審理的案件,但它從未打算以特權法庭取代普通法法庭,甚至不希望出現特權法庭完全獨立於普通法法庭之外的情景。1598年,樞密院接收了大法官埃傑頓的觀點,申明北方法庭決不能妨礙普通法中央法庭中任何案件的審理。總之,都鐸時期的特權法庭無論其地位多么顯赫,無論其權力多么寬泛,都不過是普通法法庭的補充,它們無力也無意動搖或取代普通法法庭的主導地位。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從總體上看,除了涉及宗教改革或王位繼承等問題的少數特殊案件外,都鐸時期的普通法法庭基本上是按照“正當法律程式”進行案件審判的,即使亨利八世處死兩個王后和罷黜克倫威爾也是嚴格按照法律程式完成的。法官因政治原因而被蠻橫罷免的事屈指可數,有據可查的可能只有瑪麗女王時期因參與改變王位繼承人選陰謀而被免職的首席法官喬姆利和蒙塔古和因宗教信仰而遭監禁的黑爾斯。除此之外,都鐸時期的政治和宗教變化很少影響法官隊伍。伊莉莎白一世即位後,保留了瑪麗女王的所有法官,其中幾個雖被懷疑為天主教徒,仍然官居原職,直到退休。而且,都鐸時期法官趨炎附勢、貪贓枉法的醜聞極少發生,相反,法官不畏權勢、堅持自己有獨立解釋、適用法律之權利的事例卻不勝枚舉。例如,1550年, 當樞秘院蠻橫無理地下令中止某一訴訟的審判時,法官里斯特、布朗利、波特曼聯合抗議說,他們已經宣過誓,根據正當程式實施法律,如果半途中止案件的審理,將違背自己的誓言;1591年,所有法官一致反對樞密院隨意拘押犯人的行為,並要求限制樞密院的斟酌處理權。對於法庭的尊嚴,法官們更是珍愛有加,不允許任何侵犯。據說,伊莉莎白一世的寵臣塞西爾有一次攜帶佩劍準備進入普通訴訟法庭時,首席法官戴爾把他擋在門外命令說,如果要進入法庭,必須把佩劍放在一邊。隱藏在戴爾此舉背後的一句潛台詞就是:法庭是正義的聖壇,是講法講理的地方,是不允許象徵暴力的刀光劍影玷污的。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實際上,都鐸歷代國王從不敢妄稱自己高於法律之上。亨利八世雖把上帝法踩在了腳下,但並不否認普通法和議會制定法的至上權威。當時的溫徹斯特主教伽德納寫道:“任何行為(自然包括國王的行為在內--引者按)都不得違背議會制定法和普通法。” 當愛德華六世加冕時, 大主教按法定程式問道:“除了按習慣經您的人民的同意制定有利於上帝的尊嚴與光榮、有利於共和國利益的法律外,您同意不制定任何新的法律嗎?”國王回答道:“我同意和答應。”瑪麗女王時期,表面看來女王的政策占了上風, 但它們都是按法定程式由“在議會中的女王”制定的,即使燒死異教徒和發動對法戰爭也未違反政治法律原則。當時,有一個叫弗利特伍德的絕對專制主義者,曾上書規勸女王像威廉一世那樣採用“征服者”稱號,擺脫法律束縛,獨斷專行,被女王斷然拒絕。據說,當時瑪麗女王曾為此人的耿耿忠心所感動,但她仍然將其上書當眾付之一炬。伊莉莎白一世時期專制王權達到頂峰,但在當時的倫敦主教約翰·艾爾默看來,“首先不是她在統治,而是法律在統治,因此,執行者是她的法官。……除了通過議會法庭,她不能制定任何法規和法律。如果你的統治從屬於女王的意志而不是服從於成文法律,如果她可以不用議會單獨頒布法令、制定法律,如果她根據自己的判斷而不是在法規和法律的限制下定罪量刑,如果她可以單獨決定戰爭與和平,……那么,我就會對這個女人的統治感到擔憂。”很清楚,在艾爾默看來,伊莉莎白女王是一個依法治國的君主。
專製法治之間
綜上所述,都鐸時期的英國可以說是王權和法律的權威同步提高,專制和法治趨向並行不悖,結果,本是相互排斥的兩種對立因素奇妙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英國史學家鄧納姆所說的“都鐸悖論”現象。這一不合邏輯的奇特現象,曾經令許多西方法學家和史學家感到困惑不解,因為在他們看來,專制和法治作為兩種根本不同的國家統治形式,是不可能和平共處於同一個政治共同體內的。如果單從理論上講,這種困惑不是沒有道理的。
不過,“都鐸悖論”現象並非是不可思議的,它是特定時代的歷史需要和英國獨特的法制傳統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產物。在16世紀,建立民族主權國家是整個歐洲的時代主題。在當時的條件下,能夠滿足這一時代要求的唯一途徑就是擴大王權,建立強有力的君主專制制度。因此,專制主義在歐洲各國普遍興起。在這個大方向上英國自然不會例外,於是,出現了都鐸專制王權。但英國有其特殊歷史條件,這就是從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並且從一開始就結下不解之緣的普通法和議會,二者相互合作,並駕齊驅。議會藉助普通法學家的技術幫助,迅速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運行程式,鞏固了自己作為一個權力實體的地位;普通法學家依靠議會的權力支持,成功地維護了自己的法律至上主張和司法相對獨立的法制傳統。到16世紀,二者的同盟關係進一步加強。議會面對國王和樞密院權勢迅速膨脹的威脅,更加把普通法視為自身權力的法律基礎,而普通法在特權法庭和羅馬法復興運動的內外壓力下,也更加把議會視為保持自身相對獨立性的權力依託。因此,該時期法學家們不再堅持普通法是不可改變的,給予了議會的最高立法權以充分的承認;反過來,議會對於它認為沒有必要改變的既有法律(主要是普通法),對於普通法法庭的主導地位,總是竭力予以保護。二者的強大聯盟是橫在都鐸專制王權面前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所以,專制主義趨勢在英國沒有(也不可能)走向極端。
在這裡,與大陸國家作一比較似乎很有必要。在大陸各國,中世紀時也曾出現類似英國的代表機構和專職司法機構,如法國有三級會議和巴黎法院,西班牙的阿拉貢和卡斯提爾有議會和中央法庭,但這些大陸類似機構在該時期非但未能遏制君主專制勢力的無限膨脹,反而最終成了專制王權的犧牲品。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大陸類似機構本身具有明顯弱點。如前所述,大陸各國的代表機構都是純粹的封建性等級機構,其組成方式和表決機制均存在重大缺陷,缺乏效能,無法適應近代民族主權國家的需要,因而注定要隨著中世紀向近代的過渡而走向衰亡。大陸各國的法庭都是控制在一小撮特權貴族手中的寡頭式機構,法官職位是用錢買來的,而且可以世襲,這種封閉性使它們始終懸浮於社會上層,未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因而最終必然被歷史所淘汰。第二,大陸各國的代表機構和司法機構從未建立聯盟關係,猶如兩股道上跑的車,始終相分相離,甚至彼此嫉妒和對立。因此,在專制主義興起之初,儘管代表機構有時也發出要求限制王權的呼聲,法律家們有時也擺出一副維護法律至上權威的樣子,但不可能形成有效抗衡王權的聯合力量。所以,當法國國王著手壓制三級會議時,巴黎法院冷眼旁觀,不聞不問,因為在它的心目中,三級會議百無一用,而且時常打著“國民代表”的旗號,搞封建分裂活動;反過來,當國王創建新的行政法庭以取代巴黎法院時,三級會議同樣採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因為在它看來,巴黎法院是一個不得人心的特權機構。西班牙的情況與法國十分類似。結果,在大陸各國,以國王為首的行政機構能夠通過“各個擊破”的方式,順利地把一切大權集中於自己手中,建立起絕對的君主專制統治。難怪西方學者阿姆斯特朗在總結法國憲政發展步履維艱的原因時說:“司法機關和立法機關之間的嫉妒一直是法國憲法自由道路上的絆腳石。”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
都鐸王朝相關人物油畫通過以上比較,我們會更清楚地認識到,英國的“都鐸悖論”現象是有其歷史合理性的。然而,這種合理性僅僅具有暫時意義。因為專制和法治畢竟是根本對立的,這決定了“都鐸悖論”體制是一個隱含著巨大對抗張力的矛盾體。在它的軀體內,以君主特權為依託的國王、樞密院、特權法庭代表著專制趨勢,以普通法為基礎的議會、普通法法庭代表著法治傾向。雙方之所以能夠和諧相處,是因為建立民族主權國家的時代任務的強大壓力所使然。一旦這一任務完成,暫時處於蟄伏狀態的內含張力就會像鬆了綁的彈簧一樣迅速膨脹開來,專制和法治之間的潛在衝突必將公開爆發。實際上,在都鐸王朝末期,雙方衝突的端倪已開始顯露出來。那時,衝突圍繞國王濫發專賣特許證問題展開,但鬥爭的實質是專制和法治之間的對抗,正如當時的下院議長所說:“這是通過法規法和議會中的女王體現出來的王國權威與通過特許狀行使的國王權威之間的衝突”。面對憤怒的下院,女王伊莉莎白做出了適時的讓步,鬥爭很快偃旗息鼓,但根本問題並未解決。所以,在其統治的最後數年內,女王只能依靠個人威望和靈活嫻熟的統治策略,才勉強維持了“都鐸悖論”體制內部不穩定的平衡。1603年後,當熱衷於王權無限論的斯圖亞特王朝試圖建立大陸式的絕對君主專制統治時,平衡被徹底打破,專制和法治之間的衝突遂全面展開,而且愈演愈烈。歷經一個世紀的生死搏鬥,議會和普通法的強大聯盟最終戰勝了專制王權,法治獲得了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