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介紹,作品,
介紹
衛宣利,女,河南洛陽人,生於七十年代末,河南省作協會員,《青年文摘》等雜誌簽約作家,擅於用文字來訴說生命中愛的奇蹟。常用筆名:安一萱,萱子,千江飛雪。作品見於《讀者》,《青年文摘》,《女報》,《意林》,《婚姻與家庭》,《人生與伴侶》,《戀愛婚姻家庭》,《小小說選刊》等數百家期刊報紙,作品被各類圖書轉摘並獲獎。出版小說集《有愛不覺天涯遠》,《我一個人疼你就夠了》,長篇小說《再婚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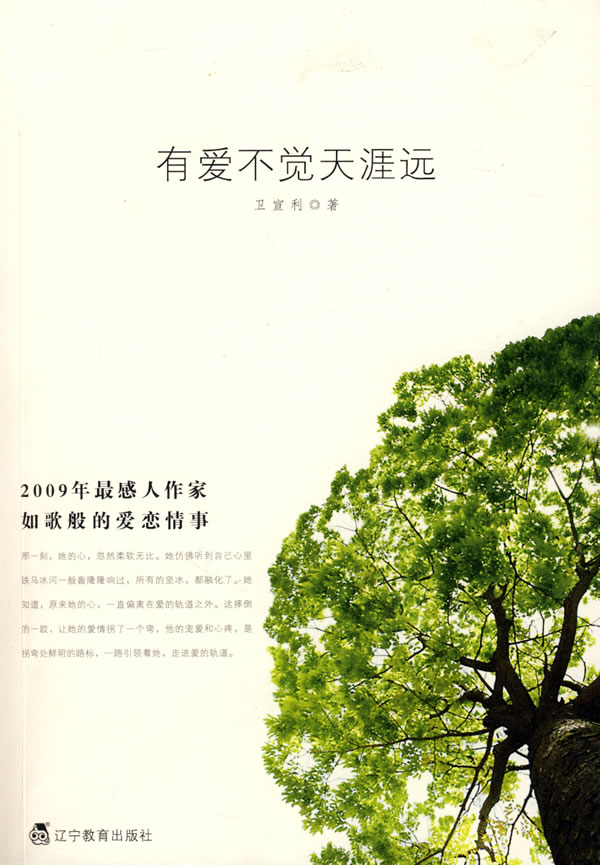 《有愛不覺天涯遠》
《有愛不覺天涯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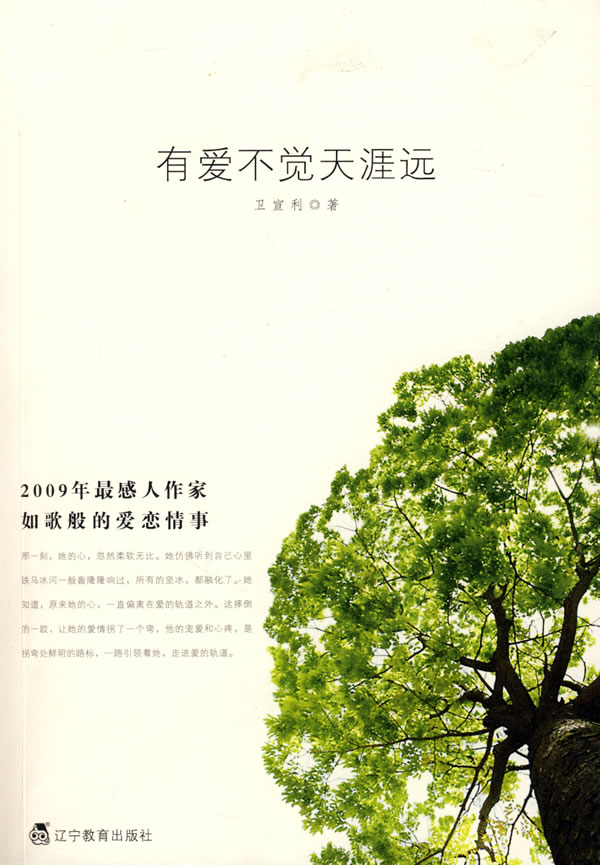 《有愛不覺天涯遠》
《有愛不覺天涯遠》作品
一段路,三個人
作者:衛宣利
一
他倆都老了。
最近兩年,她很健忘,炒菜時會放雙份的鹽,泡好的花生米總是忘了吃;睡到半夜醒來,會重新穿好衣服,去各個房間裡檢查窗戶和燈有沒有關好;買菜時付了錢卻忘了拿菜。她還多疑,半夜起來,摸黑到爸爸的房間裡,幾聲叫不醒他,便慌忙伸手去探他的鼻息,直到爸被折騰醒了,她才放心地回房去睡。她有糖尿病,視力下降得很厲害,有時會趴到我的電腦螢幕上想看看我寫的字,只能看到一團模糊,她便很生自己的氣。她總是突然感到憂慮:要是有一天你被哪個地方調走了,我們老了,不能跟你去,誰來照顧你?
他的脾氣還是那么暴,媽熬的粥糊了鍋底,他一聞味兒就摔筷子。有時他故意挑刺,菜淡的時候說鹹,鹹的時候又嫌淡,非吼上幾嗓子才舒服。他的記憶力衰退得厲害,看過的電視情節第二天就忘了,代我去銀行取錢,光密碼就打電話問了三次。他好像越來越膽小,心口痛一下就很惶恐,平時精神很足卻忽然貪睡,也讓他感到不安。有一次他推著我去逛商場,在男裝櫃檯看中一套淺灰色西服,換上後去照鏡子,他被鏡子裡那個一頭灰白頭髮,臉上布滿皺紋的老頭嚇了一跳,轉身問我:“妞兒,爸爸已經這么老了嗎?爸爸從前穿上這樣的衣服很帥呢。”然後就傷感地說:“不知道爸爸還能陪你多久……”
是的,他倆都老了。看著他們一天天走向衰老,是件殘酷而無奈的事情。我無法計算他們還能陪伴我的時間,只覺得這樣的每一時每一分,都是上天對我的恩賜。
二
二十多年來,我和他倆分開的時間屈指可數。
那時候,我是夢想要逃離的。年年第一的好成績,不過是為了給自己一個離開的機會。到縣城讀高中後,耳邊沒有了她的嘮叨和他的怒吼,忽然之間世界變得如此安穩靜好。我走在桂花飄香的校園裡,腳步都是愉悅飛揚的。
可是,僅僅兩年之後,我便被打回原形——讀高三那年,在過馬路時,我被一輛車給撞了。
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聽著她在門外哭得肝腸寸斷,看著他蹲在我床邊一聲不響,我心裡充滿絕望。從此不再奢望離開,因為我的腿成了擺設,再不能給我行走離開的機會。上帝用這樣一種方式,再次將我擱置在他們中間,似乎是在考驗他們:這樣一個孩子,你們還要不要?
她還是那么邋遢,大清早蓬頭垢面出去為我買早餐。他脾氣還是那么壞,那次一個新來的護士給我輸液,針頭連換了5個地方都沒找著血管,他便惱了,一把推開人家,拿著熱毛巾敷在我手上,回頭沖護士嚷:“瞧瞧把妞兒的手紮成啥樣了,你以為那是木頭啊?”
他背著我,去五樓做脊椎穿刺,去三樓做電療,再去一樓的健身房,在雙槓旁邊練習走路。五十多歲的人了,一趟下來累得氣都喘不過來。我趴在他背上,在他耳邊說:“爸,以後要是沒人要我,你可得背我一輩子。”他笑我:“你這么重,不趕緊學會自己走路,誰背得動啊?”她跟在後面,想幫忙又使不上勁,嘴裡咋咋呼呼的,讓他抓緊我的腿,讓他停下來歇歇,讓他注意腳下路滑。他和我都聽得不耐煩,免不了頂她兩句,她便賭氣不理我們。但不到兩分鐘,她又嘮叨開了。
三
以前,他靠著一手電焊的手藝,開了個電氣焊維修鋪,給人修修補補,日子也還過得去。我病了以後,他倆帶著我東奔西跑看病,錢花光了,鋪子沒人打理,也關門了。可是還得生活,他就在建築工地上給新建的樓房焊樓梯和鋼架結構。工頭開始不要他,嫌他年齡大,不能上腳手架,也怕活重他支撐不下來。他百般懇求,仗著手藝好,才留下的。
每天早上5點,他倆準時起床,一起陪我練習用雙拐走路。然後他上工地,她在家照顧我。晚上他從工地上回來,臉都顧不上洗,先奔到我的房間裡,看我好好的才放心。他一個月掙的錢,全都給我買了藥。沒完沒了的中藥西藥,直喝得我後來看見藥就想吐,卻一點效果都沒有。
我不能再去學校了,每天坐在房檐下,看天看地看牆角的螞蟻,心越來越敏感,怕見人怕天黑,容不得他們對我絲毫的忽略和怠慢。有一次她給我倒水,水太燙,我抬手就掀翻了床頭櫃,水壺茶杯藥瓶嘩啦啦碎了一地。她受不了我突然變壞的脾氣,一把扯下身上的圍裙摔在地上,委屈的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沖我嚷:“就是你雇的保姆也不能這么粗暴吧?老娘我還不伺候了……”
她真的走了,沒有她拖拖拉拉的腳步聲,聽不到她絮絮叨叨的抱怨,家變得一片沉寂。我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心一點一點跌入黑暗的深淵。我突然害怕起來:她不會真的不要我了吧?
然而她很快就回來了,捧著一堆舊雜誌,若無其事地對我說:“在外面遇見一個收破爛的,我看這些書興許你還能看,就買回來了。十幾本呢,才花了三塊錢……”她很為自己討了便宜而得意。
那天晚上,我遲疑地問她:“要是我再惹你生氣,你會丟下我不管嗎?”她答非所問:“我根本沒走遠,怕你有事叫我……”
他們倆都沒念過幾年書,沒什麼文化,可是我喜歡書。他在工地上看到誰有書,一定會死乞百賴地跟人家借回來給我看,她看見別人包東西的報紙,也會揭下來帶給我。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學著寫東西,渴望用一種方式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
我慢慢開始發表一些文字,他們便拿著有我文章的雜誌四處跟人炫耀:“別看我家妞兒天天在家裡坐著,可比你們知道的多呢。這書上的字就是她寫的……”他們倆都成了我的超級“冬粉”,我也確確實實成了他們最寵愛的寶貝。有一次我跟她說我要寫長篇小說,然後又說寫長篇很費精力,有個作家就是寫小說累死了。她便很緊張,連說那咱不寫小說了,人沒了,寫得再好有什麼用?
四
就這樣,一段路,三個人,相扶相攜,磕磕絆絆,到今天已經走了29年。
他們的身體一直都不太好,他血壓高,心臟也有問題;她糖尿病十多年,最輕的感冒都能引發一系列病症。那次陪他們去醫院看病,在醫院門口,他將代步車停在向陽的地方,把自己的外套脫下來蓋在我腿上,又叮囑我在車上等著,不要著急,才和她相扶著進了門診部。
我看著她挽著他的胳膊往前走,很相愛的樣子。可是,那蒼老的背影遲緩的步履,還是把我的心深深刺痛。旁邊一起看病的老人,都是由子女攙著進去。而我卻只能這樣坐著,等他們回來。我想像著他們一個一個視窗挨著去排隊,掛號,化驗,檢查,互相安慰,等待結果,謙卑地笑著跟人打聽化驗室在幾樓,忐忑不安地躺在CT機上……心就火辣辣地痛。
有淚從眼角慢慢溢出來,無可扼制。
請相信女兒,我一定可以學會自己能學會的一切,到了那一天,好好地照顧你們,就像今天你們照顧我一樣。
“ 番茄太陽”蘇教版四年級下冊12課
作者: 衛宣利
明明生下來眼睛就看不見,她以為太陽就像番茄,又大又圓。其實,她那天使的笑容才是真正的“番茄太陽”,給我溫暖和光明。----題記
那年,我24歲,為了逃避父母安排的婚姻,在和父親大吵一次後,賭氣從家裡搬了出來。父母無力阻攔我,又不放心他們雙腿癱瘓了的女兒獨自出來闖蕩,只好讓小妹跟出來,照顧我的生活。
在一棟灰舊的樓里,我們租了很小的一間房,長長的走廊,並排住了很多家,大都是這個城市的窮人。他們在通道里堆滿散煤、爐渣或者木塊兒,常為柴米油鹽拌嘴。
妹妹在超市做營業員,每天從早上8點一直站到晚上9:30,回來就把自己扔在床上,不想再動。我每天待在那間光線昏暗的小屋裡,暈頭暈腦地寫字,做著一個縹緲的作家夢。
生活很艱難,小妹的薪水很低,加上我微薄的稿費,付了房租,生活費所剩無幾。稿子投出去,又多半音信杳無,我遙遙無期地等待著,心情灰暗無比。
附近一個小型菜市場,有對年輕夫妻帶著個女孩兒守著攤位。那女孩5歲左右,是盲童。每次從菜場經過都能看到那家人,夫妻倆忙碌,女孩安靜地坐著,說話聲音細細柔柔,特別愛笑。
我總是熬夜寫作,去菜場差不多是中午了。這時攤上沒什麼人,那位年輕的父親拉著小女孩的手,在面前各種蔬菜上來回撫摸,耐心地說:“這是黃瓜,長長的,皮上有刺。豆角呢,扁扁的,光滑點。番茄很好看,圓圓的……”小女孩一面用手摸,一面咯咯地笑,媽媽也在旁邊笑。
每次看到這一幕,我的心就覺得溫暖起來。
時間久了,就和這家人熟了。小女孩叫明明,生下來眼睛就看不見。當時夫婦倆就傻了。一想到孩子永遠看不到太陽,看不見世上的一草一木,甚至永遠看不到自己的父母,他們就痛苦萬分。聽親戚說城裡大醫院可以換角膜,讓孩子復明,他們就帶著孩子到城裡來了。
如果不是盲童,明明挺漂亮的,烏黑的頭髮,象牙色的皮膚,精緻的眉和下巴,笑起來像個天使。看著她,讓人隱隱心疼。
明明突然問我:“阿姨,你是用雙拐走路的嗎?”
我一愣,這聰明的孩子,她一定聽出了我拐杖的聲音。
我笑笑說是。她又問:“阿姨,你小時候是不是也不聽話,才不能好好走路了?媽媽說我就是因為不聽話才失明的……”
我的心酸酸的,不知道怎樣向她解釋命運的無常。明明卻在大聲笑,說:“原來阿姨以前也是一個不聽話的孩子……”
接連下了幾場雨,終於晴了。陽光很好,碧空如洗,樹葉綠得發亮,明明的媽媽感嘆道:“天氣真好啊!”“是啊!太陽總算出來了。”我說。
明明好奇地問:“阿姨,太陽是什麼樣的?”
我想了想:“太陽很溫暖,很大很圓。早晨和傍晚是紅色的……”我忽然想到明明根本不可能知道顏色,就住了口,不知道該怎么說下去。
明明的爸爸挑了一個大大的番茄放在明明手上,說:“太陽就是這樣的,你摸摸看。”
明明一面用手摸一面笑:“真的嗎?太陽像番茄嗎?那我就叫它番茄太陽。”明明咯咯的笑聲銀鈴樣清脆,一串一串地追著人走。
日子暗暗的,明明像小屋裡的光線,是惟一帶給我快樂的人。她問我許多奇怪的問題,比如天上的雲怎么飄的,雨什麼形狀……我耐心地回答著她,看著她的笑臉,覺得那就是最美的“番茄太陽”。
有一天我去買菜,明明的媽媽興高采烈地告訴我,他們要走了,有人為明明捐獻了眼角膜,醫生說復明的機會很大。
我從口袋裡掏出一大把錢來,零零碎碎的,卻是我的全部。我說,別嫌少,給孩子一個看太陽的機會吧。明明媽媽推辭著說,你也不容易,一個女孩子住在這樣的地方……
要走的時候,明明輕輕地拉住了我的袖子說,阿姨你過來,我和你說句話。我彎下腰,她附在我的耳邊輕聲說:“阿姨,媽媽說我的眼睛是好心人給我的,等我好了,等我長大了,我把我的腿給你,好不好?”她的小嘴呼出的溫熱氣息拂過我的面頰,我的淚嘩地一下子流了下來。
那個正午我坐在視窗,看城市滿街的車來車往,眼前總浮現出明明天使般的笑臉。如同一輪紅紅的“番茄太陽”一直掛在我的心中,溫暖和光明永不會落。
——已選入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四年級下冊語文課本
母親的聲音
作者:衛宣利
父親去世那年,她10歲,弟弟8歲。生活就像一幅緩緩展開的畫卷,才剛剛露出幸福的顏色,便被突然襲來的暴雨打濕,一切的快樂和安寧,都被浸染得一塌糊塗。
溫柔賢良的母親,從此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狂燥,暴戾,她很小心打碎一隻碗,也會被母親聲嘶力竭地訓上半個小時。就是從那時候開始討厭母親的聲音的吧,那種尖細而乾裂的聲音,粗暴地打磨著她的耳朵,一點點地浸透到她的生命里去。她想不明白,為什麼母親原來甜潤柔美的聲音,一下子全變了味兒了呢?
其實那時候,母親也才30多歲,成熟飽滿如一枚盛夏的果實。許多人來提親,卻都被母親潑婦一樣給罵跑。
母親在菜市場爭到一個攤位,每天早上4點起床,登著三輪車,從城北的家到城南的蔬菜批發市場,再到城北的菜市場。這樣的路程,等於把整個城市繞了一圈。風裡雨里,飽滿成熟如一枚盛夏的果實的母親,很快便風乾成了一枚瘦小乾癟的乾果。
16歲,她長成一個沉默而內斂的姑娘,讀高一,成績優秀。每天中午,她從學校跑回來,飛快地做好飯,提著飯盒,騎腳踏車穿過5條馬路,去給母親送飯。常常,在人聲嘈雜的菜市場,母親一邊飛快地往嘴裡扒飯,一邊用粗大的嗓門和人講價錢。有一次她去的時候,母親正和人吵架,母親尖銳凌厲的聲音,充滿了她的耳膜。對方是個胖而驕橫的女人,吵不過,便叫了男人來,那男人,蹦跳著要去打母親。陽光下,她看得見母親飛舞的唾沫星和著眼淚,一點一點,濡濕了她的青春。
22歲,她大學畢業,沒有繼續考研。因為小弟也在讀大學,而母親,身體已經一天不如一天。第一個月的工資交到母親手上,厚厚的一撂,在母親乾裂粗糙的手中抖動,如一群飛舞的蝶。她靜靜地望住母親,低低的聲音說:"以後,不要去賣菜了。"
母親笑,聲音不再尖銳,沙啞而厚重,滿是艱辛和滄桑的味道。第二天早上,仍然是在菜市場找到的母親。隔得老遠,就聽見母親響亮的聲音在說:"我女兒,大學畢業了,在外國人開的公司里上班……"她從母親的聲音里,聽出來一個詞:揚眉吐氣。
28歲,她有了自己的女兒。月子裡,孩子整夜整夜地哭,母親便也整夜不睡,抱著孩子,悠著哄著。有一天晚上她從夢裡醒來,忽然聽到母親輕柔的聲音在唱,她沒敢睜眼,靜靜地聽,是搖籃曲。竟然是那般甜美柔和的聲音,她呆呆地聽著,18年的時光,仿佛一下子倒流過來。她用被子蒙住臉,淚水卻潮水一樣涌了出來--她終於找回了母親的聲音,找回了從前的母親。
可是幸福,從來都是那么短暫。
早上7點,母親做好飯,喊她起床。8點,她上班,母親推著孩子出去玩兒。10點,她趕到醫院時,母親躺在重症監護室,已經不能夠再說話。
是高血壓引起的中風,偏癱,失語。母親一直昏迷著,她的手撫過母親蒼白的臉龐,淚水滴落在母親臉上。她多么想再聽聽母親的聲音啊,哪怕是那種尖銳粗礪的叫罵聲,卻已是,再聽不到。
第二天中午,母親在昏迷中悄悄去了。
一個月後,她收拾母親的遺物,在一個小箱子裡,放著兩雙線拖鞋。鞋面是淡黃色柔軟的毛線,鞋底是母親自己納出來的千層底。這種線拖鞋母親以前給她做過好多,腳穿進去很舒服,唯一的不足是走路的時候腳步聲很響,所以每雙她都是只穿幾天,便丟棄一旁。
她把鞋穿在腳上,從陽台走到廚房,從臥室走到客廳,"噠噠噠",腳步聲仍然很響。她在響亮的聲音悄然落淚,她知道了,那是母親留給她的最後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