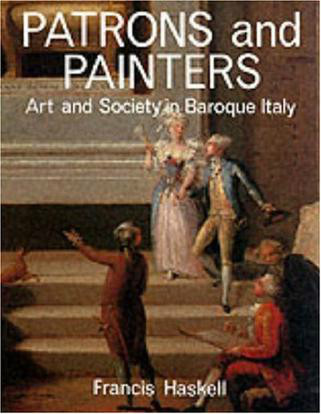歷史定論
幾年前,在
貢布里希爵士的書房裡,這位年逾90高齡的西方藝術史泰斗曾對我說,假如他年輕10歲,真願寫部研究哈斯克爾的專著。 他說:“我從
弗朗西斯的著作里獲益匪淺,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們時刻警示我,一切歷史問題,往往比我們所料想的要複雜得多,因而我們永遠不套用簡單的方式和籠統的理論去對待它們。”繼爾,他概括了哈斯克爾著作的三個特點:富於原創性,充滿否定性結論,文筆清 晰而優美。
貢布里希所說的哈氏著作特點中的前兩個特點互為因果。創見源於理性批評精神。哈斯克爾畢生致力於“否定”歷史研究中的教條成 見,懷疑抽象概念和體系,強調殊相與個人的重要作用。眾所周知,在藝術史中,這類空泛理論最易滋長的兩個地方是藝術與社會、藝術與歷史的關係研究。而哈斯克爾正是在這兩個領域裡,以無可辯駁的 事實,推翻了一個又一個的公認理論,揭示了一個又一個被忽視和遮蔽的歷史真相,從而刷新了我們對往昔藝術的認識。換言之,哈斯克爾深信藝術並非是一個獨立自足的實體,因而必須將其放到為之誕生、 為之存在、為之消亡的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但他對贊助制度、圖像在歷史解釋中的價值以及博物館和藝術展覽的影響等開.放性探究,無不表明,並不存在任何可以解釋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的普遍法則。任何尋求整一的歷史體系的企圖,實質上是對歷史學科自身存在理由的否定。
我們只要將哈斯克爾跟社會學派代表人物如弗雷德里克·安托爾 的藝術贊助研究略作比較,就可明了此點。
安托爾依據階級劃分而提出了贊助制度理論:貴族定製的藝術作 品必然有別於中產階級。當然,我們無法否認,貴族贊助人的趣味可 能不同於中產階級,但這種理論是無法在任何令人信服的理論或史實基礎上受到證偽的。顯然,將這類模式用於歷史研究,是拿已知答案去尋求例證,實質上是逾越了歷史學範疇而進入了抽象推理的領地。 在這裡,歷史事實只不過是用於建造預設的歷史哲學體系的材料而已。 與之相反,哈斯克爾的藝術贊助研究則旨在揭示藝術是怎樣在不斷變化的物質和贊助條件下產生的。他依據原始材料,對贊助人和收 藏家的不同動機與趣味,以及藝術市場機制變化進行了深入的考察,由此而作出的說明總是具體的,可以證偽的。他的第一部書《贊助人與畫家》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在西方藝術史上,
巴洛克藝術是“耶穌會精神的表現”早已成了不刊之論。當哈斯克爾著手研究這個問題時,他撇開公認的理論,僅 從具體的相關人物和塵封的耶穌會檔案材料入手,力圖弄清當事人之所說,所想與所為。他很快發現,耶穌會教派當時嚴重缺乏資金,根本無力雇用任何有影響的藝術家,為了裝飾教堂,他們不得不經常? 求富人,特別是乞求羅馬王公貴族的襄助。而有權有勢的贊助人往往不顧耶穌會的意願,將自己的想法強加於人;他們不但自選畫家與建築師,而且對作品的題材、媒介、用色、尺寸大小,乃至安放位置等 都橫加干涉。因此,將耶穌會教堂中所見的一切作品都說成是耶穌會精神的表現,顯然是無稽之談。
長期以來,義大利
巴洛克藝術一直受到輕視,其原因就在於人們 相信一般性理論。由於它被說成是耶穌會藉以籠絡人心的工具,或用 泰納的話來說,是“迷醉靈魂的甜蜜舞會”,所以,在人們眼裡,
巴洛克藝術是一種頹廢的風格。雖然,在上世紀初,一些藝術史家,如沃爾夫林等,曾竭力為其平反昭雪,但終因未能連根拔除那深入人心 的“
巴洛克藝術即耶穌會精神的表現”這個理論而失敗。只有推翻這個概念,
巴洛克藝術才能重放異彩。事實上,跟流行的看法相反,意 大利
巴洛克藝術家進一步完善了文藝復興的成就,在透視、明暗和色彩技巧上精益求精,創造出了更為複雜更為驚人的錯覺效果。但是,在這個時期,的確沒有出現其聲名堪與委拉斯克斯、
倫勃朗、魯本斯 和普桑等相比的個體藝術家,這是什麼原因呢?哈斯克爾的答案是:前所未聞的宗教和世俗的贊助熱情抑制了藝術個性和獨創性,迫使其就範於一種“公共風格”。像這樣的風格,在19世紀以來日益強調自 我或個性表現的時代里,遭受蔑視,是理所當然的了。順便提一句,《贊助人與畫家》的第一章,堪稱是西方追溯“個性表現”觀念的較 早的精彩篇章之一。
《贊助人與畫家》的問世,不但徹底改變了西方世界對
巴洛克藝 術的看法,而且改變了西方藝術史家的思維方式:即從訂購人而非藝術家的角度來看待歷史。這也激勵了哈斯克爾自己去重新看待19世紀的法國藝術。依照標準的藝術史,這是一個印象主義對抗並最終戰獨占藝苑的是學院派畫家,他們跟
巴洛克藝術家一樣,後來才被打入冷宮,直到70年代末,尚無人問津。就此哈斯克爾決心要搞清這樣一個問題:即為什麼一種藝術受到輕視而另一種藝術取而代之這類情況會發生?對這個問題的追究,產生了他的《藝術中的再發現》、《? 味與古物》以及現已收入《藝術與趣味中的過去與現在》中的大多數論”,諸如新古典主義藝術代表貴族階級的趣味,而喜愛精雕細作的 風格則是新興的中產階級的嗜好等等。其翔實的論證告訴我們,實際情況正好相反。
趣味時尚
在研究趣味史時,哈斯克爾特別關注“趣味”與“時尚”的交迭作用。可以斷言,除了
貢布里希以外,藝術史家都未認真思考過這個重要的社會和歷史問題。一般說來,他們對“時尚”一詞都較忌諱,生怕沾上它會使自己的研究顯得膚淺,儘管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無不證明,時尚總是促進趣味變遷的主要動機。不過,在哈斯克 爾看來,時尚與趣味是有本質區別的:趣味可無關他人介入而存在,時尚則必然牽涉他人———不是自己跟從別人,就是設法讓別人跟從 自己。如果裁縫做出一套“趣味”高雅的服裝,但卻不能使別人喜歡, 那便徒勞無功了。可以說,趣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獨立於他人意見的東西,就如有人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看見某件東西,他大可依據自己的判斷,或說此物妙不可言,或說此物俗不可耐,根本不用顧忌 他人是怎么想的,也用不著去說服他人。“時尚”則不然。
在藝術史上,趣味與時尚的互動作用,促成了藝術風格的連續和 斷裂,構成了趣味變化的歷史。那么,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變化的呢?哈斯克爾同意
貢布里希的理論,即一旦人們認識到,某種藝術風格不再適應他們所期望達到的目的,那么,斷裂就會發生。例如,在17世 紀的某個階段,人們明顯地感到,
巴洛克以前的那種藝術,對於說服民眾信仰某種宗教觀念,已不十分奏效了,藝術家意識到,有必要做出與前人、甚至與同代人不同的新東西才能達到目的。這便促成了風 格的斷裂。
然而,研究趣味與時尚,的確有其危險性。哈斯克爾的《藝術中 的再發現》和《過去與現在》就遭致了兩種誤解。一是說他有相對主 義傾向,二是說他把歷史看成了不斷以現時形象重塑自身的過程。
我認為,第一種批評混淆了歷史學家自持的價值觀念和往昔實際 發生的“發現”或“再發現”事實。今天,不論藝術史家個人是否喜歡波提切利,誰都不會否認他是一位偉大的畫家,但是,他曾是一位被長期遺忘的畫家,到了19世紀才被重新發現。那么,以客觀的歷史態度,重構這一被遺忘、被再發現的史實,能算是相對主義嗎?波提 切利名聲的升降沉浮表明,名噪一時的畫家,有可能在未來湮沒無聞,而默默無聞的藝術家,有可能在未來名聲鵲起,這是歷史的事實,是不以藝術史家的個人趣味為標準而轉移的。承認這種難以預料的嚴酷 的歷史現實,本身就暗示出一種可貴的價值觀念。
不久前,有人問哈斯克爾,在20世紀晚期,哪種藝術形式最富有 活力,他的答覆是電影。他知道,這樣說會引起很大的爭議,但這恰恰說明他絕不是價值相對論者,他斷言:在西方,從1914年之後,沒 有出現過真正偉大的畫家。但這不等於說,藝術家沒有創造出好畫,而是說,諸如波羅克之輩的畫家,其才幹和偉大之處都無法跟
畢卡索、馬蒂斯和布拉克這代藝術家相比,至少是絕對不能跟拉菲爾這樣的真 正的古代大師相比。
哈斯克爾是從歷史的觀念出發來肯定現代電影成就的,這也並不 能說他放棄了價值標準:
如果有人問我,我是否偏愛我們時代偉大的電影導演的作品…… 毫無疑問,我會覺得它們更令人激動。我們很難確切地說明其原因,除了說:在1920和1930年代的某個階段,電影得到了驚人的發展,許多真正有天賦的人都被吸引過去了。而這些天才人物,若在17世紀, 可能會被吸引去創造繪畫與雕刻,因為那時這兩門藝術正以各種新穎而激動人心的方式發展著。
同樣,哈斯克爾使之“復活”的法國學院派畫家,諸如德拉羅什、
梅索尼埃、熱羅姆、
布格羅和
卡巴內爾,其盛名一度被那些為所謂的 20世紀先鋒派鋪墊了道路的印象派藝術家所淹沒,這不等於說,這種情況的發生是由歷史學家一手導演的。
不過,關於19世紀藝術中的“再發現”是如何發生的這一觀念, 其問題出在:藝術史家常將該觀念與藝術家千方百計設法震驚大眾的念頭混為一談。毫無疑問,印象主義畫家的確試圖創造新的東西,但是,可以肯定,倘若莫奈和畢沙羅從一開始就大獲成功,他們絕對會 感到高興。在哈斯克爾為牛津大學歷史研究生所作的19世紀法國藝術的講座里,他批駁了印象派專家雷瓦爾德等人所構築的印象派蓄意對抗學院派的神話,他以大量的第一手新材料說明,
馬奈和莫奈等“叛 逆者”其實跟許多學院派畫家交誼頗深,對其繪畫技巧羨慕不已。是 他們在沙龍的失敗,才使其感到懷才不遇,遭受了時代的嘲弄。
這個念頭日益膨脹,最終產生了對現代藝術史和藝術創造影響最 為深遠的觀念:即要成為一名偉大的藝術家,首先必須被嘲弄。不言 而喻,這種觀念對趣味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它使藝術史家和藝術家惶惶不可終日,擔心自己錯失天才,落後形勢,被冠上保守派的臭名。哈斯克爾極度不贊成把德拉克羅瓦甚至印象主義畫家說成先鋒派的做 法。他認為,該稱號應留給那些處心積慮地要向現狀提出挑戰的藝術家。
歷史讀解
然而,上述業已存在的現代觀念,不論對錯與否,對整個20世紀 的藝術,乃至20世紀讀解歷史的方式,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如 今,它已被運用到各種極不恰當的場合,例如,用以描述
卡拉瓦喬這 樣的藝術家。在哈斯克爾看來,
卡拉瓦喬的確發明了一種新風格,但在他有生之年,有錢有勢的人紛紛向他訂購作品,他絕對為之高興。所以,當接到委託時,他總是如風似箭地完成任務。因此,把卡拉瓦 喬描述為革命性的畫家,有意要觸怒觀眾,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儘管如此,哈斯克爾不想否定,就20世紀的發展而言,先鋒派這一違背 歷史實情的觀念本身是具有歷史意義的。
它對史學所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是進一步將圖像推到了歷史研究 的中心。先鋒派觀念產生於黑格爾主義的藝術反映社會和時代精神的 學說,而它反之又為這一理論添加了強烈的激素:藝術預示未來。哈斯克爾在《歷史及其圖像》中對這些問題作了系統的闡述。他的研究表明,藝術家既非是時代的反映者也非預言家。與其說藝術反映時代, 倒不如說時代反映藝術。
①哈斯克爾指出,雖然藝術家本人喜歡別人說他的作品反映了時代 的精神,但他卻不知道,這種榮譽實際上貶低了其創造性。因為,它暗示,藝術家先有意識地外出,測量時代的氣溫,然後趨炎附勢地為時代創造作品。即便如此,藝術家也成不了時代的反映器。我們如今常看到形形色色的展覽,難道這些作品都是“我們時代的準確無誤的 反映”嗎?跟這個反映論相關的另一個流行說法是:②藝術家走在時代 的前列,他們的作品能夠預示未來。在西方,這種說法在社會動盪和 戰爭年代尤其盛行。例如,人們一度普遍相信,
畢卡索和布拉克的立體主義打散了形體,這種解構便預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在轟炸中解體的現實。這當然是一派胡言,根本經不起事實的反駁。然而? 不可否認,藝術家喜歡預言家的稱號。據說,在戰爭期間,
畢卡索? 見一列列偽裝卡車駛過巴黎街頭,於是喊道:“我們發明了這個東西!? 對哈斯克爾來說,這條逸聞趣事意味深長,形象地反駁了“反映論” 和“預言說”。
可見,這兩種論調本身,從不同的角度貶損了藝術家的尊嚴。聲稱一位藝術家的作品僅僅反映他的時代,等於扣除了他的創造行為, 這對他不公平。因此,哈斯克爾願說,時代有時反映藝術。
那么,時代是如何反映藝術的呢?在近代,有些真正革命性的藝 術家所創造的藝術對文學和音樂產生了明顯的影響。例如,美國先鋒 派女作家斯泰因就在小說中有意識地吸收了立體主義藝術的觀念。? 有許多更早的實例,說明人們完全依據現存的藝術類型描述他們心? 中的聖母與聖徒的形象。哈斯克爾認為,在歷史上,這種情況時常? 生,在某個時代,某種藝術會特別昌盛,例如,在中世紀,泥金手稿是重要的形式,到17世紀,雖然它並未全然消失,但已被另一些藝術形式所取代。百年之後,人們若要弄清什麼是1914至1990年間(隨意選個日期)的偉大的視覺藝術形式,其結論很可能是電影作品。他們也許會承認,雕刻和繪畫仍然繼續存在,但正如我們已忘記17世紀所 有的泥金手稿藝術家的名字那樣,我們的後人很可能也會忘掉20世紀 晚期的畫家和
雕刻家的大名。這種現象,加上其他種種因素,也許是 引起人們認為藝術反映時代的錯覺,造成歷史形相誤置的根本原因。
總而言之,藝術介入歷史給史學研究性質傾注了新的複雜因素。 它也加劇了對什麼是歷史的問題的論爭;那場曠日持久的關於歷史究 竟是科學還是藝術,是真實復現還是修辭虛構的論戰,恐怕也與此不無瓜葛。頗有興味的是,我們將從哈斯克爾的史學實踐中看到,這場論爭的緣起與擴散,恰恰說明了爭論雙方對歷史研究的性質、方法和 任務的曲解,說明了他們無意中忽視了歷史本身是一種“智性形式” 而非往昔的被動復現這樣一個客觀現象。
在歷史寫作中,哈斯克爾堅定不移地繼承了偉大的19世紀歐洲史 學遺產,誠如人們所說,他是該傳統在20世紀寥寥可數的最優秀的後 裔之一。他“飽學多聞,所寫之書,總是講述故事,有趣而值得一讀”。 哈斯克爾固守這一傳統,因為,他深信,這是重構歷史真相,實現歷史終極目標即“讓往昔復活”的最有效的手段。就在他生命的最後時 刻,他重申了自己的立場:
關於什麼是歷史,存在著許多理論,我雖然喜歡閱讀有關這方面 的所有論著,但我最信奉的歷史觀念(它的威力在19世紀比今天遠為強大)是:歷史學家的職責之一就是要讓往昔復活,即使其真實可見…… 我的至高無上的理論是:藝術史家必須讓讀者看見往昔的人物(藝術 家、贊助人、收藏家和藝術愛好者等)的實際面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總能做到這一步,但我將之奉為原則。讓往昔恢復生命,這肯定是我總是努力在做並真正是自覺想做到的。
遵從真理
這番話,加之他常公開說,“沒有理論,歷史照樣可以留存”,難免引起一些人的誤會,以為哈斯克爾是位實證論者,而其著作必定缺乏理論。事實上,在歷史研究中,哈斯克爾反對各種理論( theories)的霸權,恰恰是出於他對思想(ideas)的熱愛。他總是把思想與理論區別開來,認為前者充滿活力,而後者則是“被誇張被凍 結了的思想形式”。凍結的思想易於淪為教條。上面提到的藝術史中的一些“等號式理論”便屬此類。
兩件鮮為人知的事可以充分說明哈斯克爾對理論的懷疑並非等於他沒有理論(其實,宣稱沒有理論本身就是一種理論)。
這裡指的是哈斯克爾與著名小說家E.M.福斯特(E.M. Forster)和偉大的思想家以賽亞·伯林(IsaiahBerlin)的私交。
50年代初,哈斯克爾在劍橋國王學院讀書時,加入了以福斯特為 核心而復興的秘密精英小組“使徒社團”。在頻繁的交往中,他與福斯特成為至交。在晚年,哈斯克爾還常說國王學院是他的精神之家。可以說,哈斯克爾那純似經驗主義的歷史觀念是福斯特的劍橋所給予 他的一份精神遺產。而這份遺產的本質就是思想上的懷疑主義,知識上的不可知論和人生上的寬容。福斯特在《最長的旅途》這部小說的開篇所描述的場合實際上真實地反映了使徒社團周六聚會時激烈辯論 的情景。他們的討論,坦率、幽默,時而伴隨著譏諷、挖苦,但社員之間,始終相互尊重,時刻願意聽取不同意見。總而言之,不拘一格的友誼和堅定的懷疑主義是他們的精神基礎,或用福斯特的話來概括, 他們論辯的唯一原則就是“遵從真理,而非為了取勝”。
那么,什麼是“真理”呢?它不是宗教、哲學和人生的教條,它是“寬容、溫和、善良與同情心”。誠如福斯特在1939年那篇驚世駭俗的文章“我信仰什麼”中所說的那樣:
我不相信信仰。但這是一個信仰的時代,人們被如此眾多的富於 戰鬥性的信條所包圍,為了自我防衛,人們必須形成自己的教義…… 寬容、溫和、善良與同情心———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倘若人類不想垮台,它們就得儘快站到前沿來……我的立法者是伊拉斯莫斯和蒙 田,不是摩西和聖保羅。我的神廟不是屹立在莫賴厄山上,而是在那 片甚至不道德的人都可進入的樂園之中。我的座右銘是:“主啊,我不信———幫助你,我的無信仰。”
從知識界看,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崇尚時髦學說的時代。如果說哈 斯克爾有任何信仰的話,那么,抵制形形色色的“知識時尚”,反對 各種各樣的教條主義,就是他矢志不移的準則。兩年前,哈斯克爾向我提到福斯特追念另一位“使徒社團”成員、藝術批評家
羅傑·弗萊的悼詞。福斯特說,弗萊相信理性,拒絕權威,藉助直覺但卻疑心直 覺。無疑,這三句話同樣可用來概括哈教授的學術品質。
哈斯克爾與伯林的牢固關係,是他們在漫長的牛津教學生涯中建 立起來的。哲學家伯林似乎對福斯特本人並無多大好感。但他自己一 生都在努力摧毀那個自柏拉圖以來一直統治著西方世界的頭號教條:即人類的所有問題最終可由某個理性答案加以解決。因此,在反教條主義上,他和福斯特可算是同一戰壕里的戰友。當然,這更是聯結哈 斯克爾與伯林的一條重要紐帶。在數十年里,哈斯克爾與伯林經常見面,通過談話交流思想。因而歷史並沒有記錄他們交流的內容。但他們所交換的幾封信中,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伯林這樣的哲學家會跟 哈斯克爾這樣的歷史學家相處得如此默契。
我們知道,跟美國觀念史家洛夫喬伊一樣,對浪漫主義的研究占 據了伯林的大半生時間。雖然伯林厭惡浪漫主義者所鼓吹的“超人” 或“超級自我”的觀念,但他堅信,浪漫主義思潮對西方現代思想和行動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它動搖了統治西方 兩千餘年的一元論的基礎,從而為思想的多元化鋪平了道路。可以說? 伯林最富原創性的思想即關於“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論述? 是受浪漫主義思想的啟示而形成的。難怪,一向對自己的寫作不滿的伯林認為自己最好的論文是“浪漫主義意志禮讚:對理想世界的神話 的反叛”。但是,從1985年11月11日伯林致哈斯克爾的一封回信中,可見哈斯克爾對伯林的某些論點提出了反駁,以事實迫使伯林放棄了他那“並非很有原創性的命題”。
我們還可再舉一例。伯林曾依據法國歷史學家米什萊個人對拿破倫的痛恨而理所當然地推斷他也反對拿破倫三世,為此,哈斯克爾跟他進行了激烈的辯論。1993年8月21日,伯林最終致函哈斯克爾,承認自己的武斷,他寫道:“我投降。我對米什萊的整個看法都改變了: 那個激烈反對拿破倫三世的英雄形象已煙消雲散……對於這個痛苦的啟迪,我對你深感謝意。多年來,我一直在傳播這個錯誤信息,我將停止這一切。”
我引用這兩個例子,僅想藉以說明哈斯克爾不僅熱愛思想,而且 關注理論,不然,伯林是不可能與他討論這些問題的。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過這些事例,使我們更明確地認識到理論在歷史與哲學研究中的不同地位:歷史學家應把理論退居到他所重構的史實的後方,而哲學家則必須將理論推向前線。換言之,理論之於歷史學家就如偵察小組和後援兵力之於主力部隊,而歷史之於哲學家則如嚮導之於大部隊。
當然,正如人們所說,伯林的偉大之處在於將哲學和歷史相結合,也就是說,他善於從歷史的角度來思考哲學問題。難怪,他與哈斯克 爾共享的一個信念是:在歷史上,有些被遺忘的思想家和藝術家往往比那些家喻戶曉的人物更有助於我們理解往昔。伯林重新挖掘出了維科、赫爾德及其老師哈曼等重要思想家,而哈斯克爾所關注的是“? 術中再發現”的人物和事件。伯林在去世前不久,又一次談到維科? 可以說,這段話代表了他和哈斯克爾共同的歷史觀念:
維科希望理解歷史知識的性質,理解歷史本身的性質:就外部世 界研究而言,依賴自然科學,無可非議。但是,自然科學可為我們提 供的只不過是一個對岩石或桌子或星星或分子的行為記述而已。在思考過去時,我們超越行為;我們希望理解人類曾是怎樣生活的,也就是說,理解他們的動機,他們的恐懼、希望和抱負,他們的愛和恨—— 他們向誰祈禱,他們是如何通過詩歌、藝術和宗教來表達自己的情感的。我們能做到這一點,因為我們自己也是人,能夠從這些角度理解我們的內在生命。我們知道一塊石頭或一張桌子的行為,因為我們對 它們進行了觀察,提出猜想,然後驗證它們;但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那岩石希望成為它現有的樣子———的確,我們認為它沒有希望的能力, 或沒有其他任何意識能力。不過,我們的確知道為什麼我們會成其為 我們,我們尋求什麼,什麼使我們失敗,什麼表達了我們內在的情感與信仰;關於我們自己,我們所知道的比我們能掌握的關於岩石或? 流的知識更多。
真正的知識是關於為什麼事物會成其為現有樣子的知識,不單? 是它們是什麼的知識;我們越是深入這一點,我們就越是認識到,荷馬時代的希臘人所提出的問題不同於羅馬人的問題,而羅馬人的問題不同於人們在基督教中世紀,在17世紀科學文化時代,或在維科自己的18世紀所提出的問題。問題不同,答案不同,志願不同,人們使用的語言和象徵符號也不同。對一組問題所作出的回答並不能解答其他文化的問題,也不一定與此相關。
正是為了理解往昔不同文化和不同時代的問題與答案,哈斯克爾 不僅將自己的研究領域從16世紀擴展到20世紀初,從義大利擴展到法 國、英國、西班牙和德國,而且將以往相對“靜態的”藝術史轉化為 一門“動態的”學科,大大地改變了我們看待藝術的方式,拓展了我們思考藝術的角度。如今,當年輕的藝術史家面臨一件藝術作品時,他不再局限於下列問題:“這是誰的作品?”“是何時何地創作的?” “它屬於哪個流派?”“與前人或同代人在風格上有何相異之處?” “它表現的是什麼內容?”“有什麼象徵意義?”他可以進一步追問: “它是為誰創作的?”“藝術家在創作時有多大的自由與限制?” “是誰為此而付的錢?”“訂購人和他的同代人及後人是怎樣看待它的?”“它在歷史上與其他收藏者有什麼關係?”一言以蔽之,“它 在多大程度上表達了與之相關的人們的特定思想、抱負、希望、恐懼、 愛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