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研究》是200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圖書,作者是劉旭。
基本介紹
- 書名:底層敘事:從代言到自我表述
- 作者:劉旭
- ISBN:978-7-208-11532-3
- 類別:社會科學
- 頁數:300
-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3.7
- 裝幀:平裝
- 開本:1/32
定義,中國底層研究的特點,中國底層研究成果,底層研究專著,劉旭《底層敘事:從代言到自我表述》,劉旭《底層敘述——現代性話語的裂隙》,滕翠欽《被忽略的繁複》,
定義
“底層”一詞的最早出現於義大利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葛蘭西(A. Gramsci)的《獄中札記》中,他用了Subaltern Classes一詞,可譯成“底層階級”,從書中看來,葛蘭西用“Subaltern”來意指歐洲社會裡那些從屬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會群體,他的“底層階級”主要指馬克思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這么推究,農民的生活向來比工人水平更低,所以農民也理所當然地歸於底層。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底層必然又有了新的內容,容納了更多的邊緣群體。
底層作為社會學研究範疇,在美國產生於1961年,比印度的底層研究早了20年。18和19世紀的美國,社會下層被稱為“不值得救助的窮人”(undeserving poor),1961年,人類學家及社會學家奧斯卡·劉易斯(Oscar Lewis)在《桑且和他的孩子們》中第一次用“under class”取代了當時流行的“lower class”,他通過對貧民窟中一個墨西哥人女性戶主家庭的研究,首先使用“底層階級”這一概念,使之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群體研究。
中國底層研究的特點
從底層問題在中國的逐漸顯現來看,中國知識界最早真正對底層的關注實際從作家開始的。農村小說從80年代中期就開始關注農民的利益問題。時代造就了作家朦朧的底層意識,但卻沒引起太多注意,因為底層問題還不明顯。真正的關注在於1993年前後社會學上的資料。
一些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如溫鐵軍、李昌平、曹錦清等人的研究集中在“三農”領域,對城市底層的研究也集中在外來打工者的研究,對三農的研究有較多的成果,如溫鐵軍在進行鄉村建設實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很有建設性的意見,對城市打工者的研究幾乎沒有進展,一直停留在打工者的苦難式的研究,而且對現代性缺乏反思,對制度性的根本性問題沒有觸及,反而容易把打工者的命運的改變寄望於經濟體制乃至政治相關的進一步美國化,試圖以更“現代”的方式解決打工者的問題,與美國的威爾遜等人的從社會結構研究和經濟政策角度入手相比,中國的城市底層研究相當粗淺且缺乏章法,當然許多研究者提出了較好的建議,如加強對打工者的保護,進行相關立法並嚴格執行,在城市中多方面地給打工者以平等的待遇等,但對現代性的反思一直是不到位。
從整體上看,中國當代小說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注意到農村底層和城市問題,90年代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啟動並取得相應成果後,社會學和經濟學研究發現了與80年代以前不同的階層分化現象,並引起較大的反響,才引起了文學界及批評界的注意,然後沿及其他學科。真正形成一種焦點性研究是在1990年代末至新世紀初。此時對現代性的思考也進入了一個劃時代的階段,與世界的底層研究及反思現代性同步。
中國底層研究成果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底層”一直是中國當代人文學者高度關注的研究對象。早在1994年,由朱光磊主編的《大分化新組合——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一書,就曾藉助大量的客觀數據,分析了中國社會階層的分化特點及其趨向,尤其是對社會底層群體(包括失業人員、農業勞動者、鄉鎮企業職工、藍領等)的生存狀況,給予了密切關注。隨後,圍繞著“三農”、城市階層分化等問題,以《讀書》、《天涯》等雜誌為核心的媒介,發表了大量頗具影響的文章,各類專著也不斷湧現。[1]這些著述不僅有效地梳理了90年代以來中國底層社會的演變狀況,而且對底層群體的生存境域給予了多方位的探討,對貧富分化日趨明顯的社會結構進行了深研。
文學也對此作出了迅速反應。早在1996年,文學評論家蔡翔就在《鐘山》第5期上發表了《底層》一文。在此文中,作者深情地回憶了自己當年在上海底層以及下鄉時的生活,並進而指出,儘管“底層仍然在貧窮中掙扎,平等和公平仍然是一個無法兌現的承諾”,但是,“貧窮並未導致道德的淪喪,相反,我的底層牢牢恪守著它的道德信條,他們對貪污和盜竊表示出一種極大的憎惡和輕蔑”,“幾乎所有的道德要求最終都將落實到底層,底層將這個世界默默托起,同時遵守著這個世界對它發出的全部的道德指令”。[2]與此同時,作者亦對90年代以來底層社會的變化——尤其是純樸和善良逐漸消失的底層現實發出了真切的喟嘆。它既展示了中國底層社會的裂變,也分析了其中的利益化和欲望化的現實根源。
1998年,《上海文學》在第7期發表了燕華君的小說《應春玉蘭》。該期“編者的話”以《傾聽底層的聲音》為題,明確地說到:“我們的確是到了應該認真聽一聽底層人民的聲音的時候,我們必須正視底層人民的利益所在,我們必須尊重底層人民的感情。”“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應該忽略底層人民的利益。少數人的財富如果建立在對底層的掠奪之上,那么,這就是犯罪,就是腐敗,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正。如果認為社會的進步必須以付出底層人民的利益為代價,那么,這不僅是一種糊塗的觀念,而且,在道義上顯得非常可恥。”與此同時,他們還注意到,“有一種聲音應該漸漸強大起來,那就是底層的聲音。必須堅持平等和公正的立場,必須懲惡揚善。在任何時候,我們都應該認真傾聽來自底層的聲音,應該知道底層正在想什麼,底層人民正處在一種什麼樣的生存狀況之中。對底層的關心,並不是什麼‘慈善事業’或者所謂的‘慈悲心’。任何一種居高臨下似的憐憫,都是對底層人民的侮辱。我們堅持的,是一種平等和公正的立場,而平等和公正的問題,在今日社會,正愈來愈被人們所關注。它不僅涉及到底層的利益和情感所在,而且關係到我們整個社會的健康肌理。一個不公正的社會,必然充滿骯髒和罪惡,它最後毀滅的,必然是社會本身。所幸的是,我們的社會正在平等和公正的道路上繼續前行,而在這種時候,底層的聲音成了堅持平等和公正的一種強大力量。”這篇“編者的話”,與其說是對燕華君小說的積極推介,還不如說是對“底層寫作”的一種高調倡導,其意圖顯然是藉此機會,大力強調作家們必須對底層生存的變化和一些普世價值的動搖給予高度的關注。
2001年,李師東主編出版了小說集《生活秀》。在序言中,李師東對“底層寫作”的意義同樣給予了高度肯定:“作家們不知不覺地把自己逼進到一個特定的視角,一個十分生活化的視角:他們由衷的關心普通人的現實人生,尤其是底層人們的現實人生。我們看到,作家們的視角正在下沉之中。‘從生活的內里寫起’,正成為作家們自覺的創作行為。”“說到底層生活,人們會自自然然地把它與受苦受難、不幸而又不爭聯繫到一起。底層就是底層。人們或許還會欣慰的感嘆自己如何如何的走出了生活的底層。但是,如果意識到我們都是在生活的內里,那么你對生活的表層底層就不會那么著意了,事實上,這就是你的生活,你的人生。你的人生里有苦有難,有不幸之處,也有不爭之時。而這一切,並不因為你不在所謂的‘底層’就消失了;同樣,你的快樂,你的幸福,你的滿足,也洋溢在生活的底層之中,如同在你的生活之中。”[3]
至此,“底層寫作”漸漸地浮出水面,並迅速成為當代文學的一個熱點現象。2003年,張韌、蘇童、李伯勇等評論家和作家,或通過對話,或發表專論,紛紛以肯定性的言辭,密切關注這一寫作現象。但是,“底層寫作”作為一種文學思潮並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研究對象,還是從2004年開始。2004年,隨著劉旭的《底層能否擺脫被表述的命運》,蔡翔、劉旭的《底層問題與知識分子的使命》,高強的《我們在怎樣表述底層?》,蔡翔的《底層問題與知識分子的使命》,羅崗的《“主奴結構”與“底層”發聲——從保羅·弗萊雷到魯迅》,摩羅的《我是農民的兒子》,顧錚的《為底層的視覺代言與社會進步》,吳志峰的《故鄉、底層、知識分子及其它》,李雲雷的《近期“三農題材”小說述評》,王文初的《新世紀底層寫作的三種人文觀照》……等一大批文章的出籠,“底層寫作”便成為當代文壇的思考焦點。這些文章或依據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現狀和矛盾,或圍繞創作界出現的“打工文學”和底層小說,對90年代以來出現的底層群體的生存困境、精神需求以及審美籲求均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並從知識分子的人文情懷上強調了“底層寫作”的重要性。
2005年,有關“底層寫作”的研究獲得了進一步的拓展,出現了像丁帆的《“城市異鄉者”的夢想與現實——關於文明衝突中鄉土描寫的轉型》、南帆等人的《底層經驗的文學表述如何可能?》、張清華的《“底層生存寫作”與我們時代的寫作倫理》、蔣述卓的《現實關懷、底層意識與新人文精神——關於“打工文學現象”》、丁智才的《當前文學底層書寫的誤區芻議》等重要文章。這些文章緊密聯繫當時的創作實際,分別從不同角度對“底層寫作”進行了頗為深入的研究,同時提出了一些具有反思意味的思考。像丁帆和蔣述卓都論及了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所遭受的各種精神困頓,以及作家所應持有的人文主義立場;南帆則從作家作為代言者的角度,分析了底層經驗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同時還指出了表述形式的重要性;張清華更明確地說到:“‘底層生存中的寫作’,我意識到,這是一個包含了強烈的傾向性、還有‘時代的寫作倫理’的莊嚴可怕的命題。”[4]而丁智才則認為,當前一些書寫底層生活的作品卻以“苦難”為視窗,窺視“底層”的欲望,甚至人為地扭曲這些苦難,從而掏空了苦難本身所具有的悲劇價值,作品只保留著作者窺視的眼睛和冰冷的文字。他們寫底層女性,“大多從事三陪或變相地做雞,以此來突出底層女性的苦難境遇”,用過多的文字堆砌感官刺激。“底層”似乎只有麻木、骯髒、陰暗、猥瑣、屈辱而沒有美好和光明的一面。這樣的作品名曰“底層寫作”,實則是對底層苦難生活的極度扭曲與漠視,對底層人性的侮辱。[5]所以,要想使“底層文學”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創作出具有豐厚審美價值的作品,作家們就必須清醒地看到這一寫作誤區。
2006年到2007年,《人民文學》、《小說選刊》、《北京文學》等重要文學期刊開始以積極的姿態,主動倡導具有“底層寫作”審美傾向的作品,從客觀上進一步催化了“底層寫作”思潮的發展。與此同時,“底層寫作”研究也出現了多元觀念的碰撞與爭鳴。這些碰撞和爭鳴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如何界定“底層寫作”的概念。究竟哪些群體可以視為底層?“底層寫作”的主體是誰?是“底層人的書寫”還是“書寫底層人”?像王曉華、梁鴻、洪治綱、騰翠欽等人都曾質疑這一概念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二是“底層寫作”中是否存在著道德價值與藝術價值之間的不平衡?有不少學者認為,由於創作主體“中產階級趣味”的介入,導致了“底層寫作”中道德價值明顯高於藝術價值,如南帆的《曲折的突圍——關於底層經驗的表述》、李運摶的《底層敘事的道德誤區》、劉復生的《純文學的迷思與底層寫作的陷阱》等都涉及了這一問題。但也有不少學者從具體作品分析入手,提出不同看法,像王光明的《底層經驗與詩歌想像》、孟繁華的《底層經驗與文學敘事》、吳思敬的《面向底層:世紀初詩歌的一種走向》等,通過具體的文本印證自己的判斷。三是“底層寫作”與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傳統是否存在著精神上的關聯?李雲雷、劉繼明、白亮等人就從“左翼文學傳統”角度,強調“底層寫作”與中國現代文學傳統保持著緊密的精神同構;而賀紹俊等人則從“新國民性”角度,提出這種文學思潮是新的歷史語境中城鄉衝突的審美表達,“新國民性是在計畫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體制相互矛盾、相互碰撞、相互妥協、相互調整的文化語境下生成的”,[6]對這種生存現狀的表達,隱含了一種現代性的審美訴求。圍繞這些爭鳴,這兩年里,出現了40多篇具有一定影響的論文,其輻射範圍幾乎涵蓋了雜誌、報紙和網路等多種媒介。
2008年,有關這一創作思潮的研究依然方興未艾。一方面,學者們緊跟創作現實進行實證性的評析,像張清華、柳冬嫵對“打工詩歌”的研究,徐德明、邵燕君等對賈平凹的《高興》等作品的評述,都是通過實際創作進一步闡釋“底層寫作”的相關思考;另一方面,有關“底層寫作”中所包含的現代性問題、“新左翼”傾向以及意識形態化傾向等,其研究也獲得了進一步的深化和拓展。特別是像何言宏對“新左翼文學”與“底層寫作”的論述;劉思謙對“底層寫作”主體精神困境的辨析和超越方式的思考;江臘生對“底層寫作”中所體現出來的“民工、城市、鄉村卻大都是一種簡單化的想像性表述”的批評,以及創作主體因為“居高臨下的文學視角造成了打工作品難以真正地走進底層生活,因而缺乏審美的哲思和藝術的批判”的論析,都體現了研究者們對這一思潮的較深思考。此外,《探索與爭鳴》也在第5期上推出了一組“底層寫作:未完成的討論”的文章,孟繁華、賀紹俊、張頤武、陳福民等學者各持己見,進一步分析了這一思潮中所蘊含的各種重要的文學命題。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還陸續出現了一些對“底層寫作”研究本身進行總結和反思的重要文章。像李雲雷對2007年“底層寫作”研究的回顧和總結,王堯的《關於“底層寫作”的若干質疑》、白浩的《新世紀底層文學的書寫與討論》、梁鴻的《通往“底層”之路》等文對新世紀以來有關“底層寫作”研究的辨析和反思,儘管各有側重,觀點亦不相同,且不乏一些尖銳之詞,但都體現了當代文學研究者們對這一思潮進行理性化和系統化思考的精神姿態,也顯示了有關“底層寫作”的文學討論正在不斷地走向深化,並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前沿問題。
底層研究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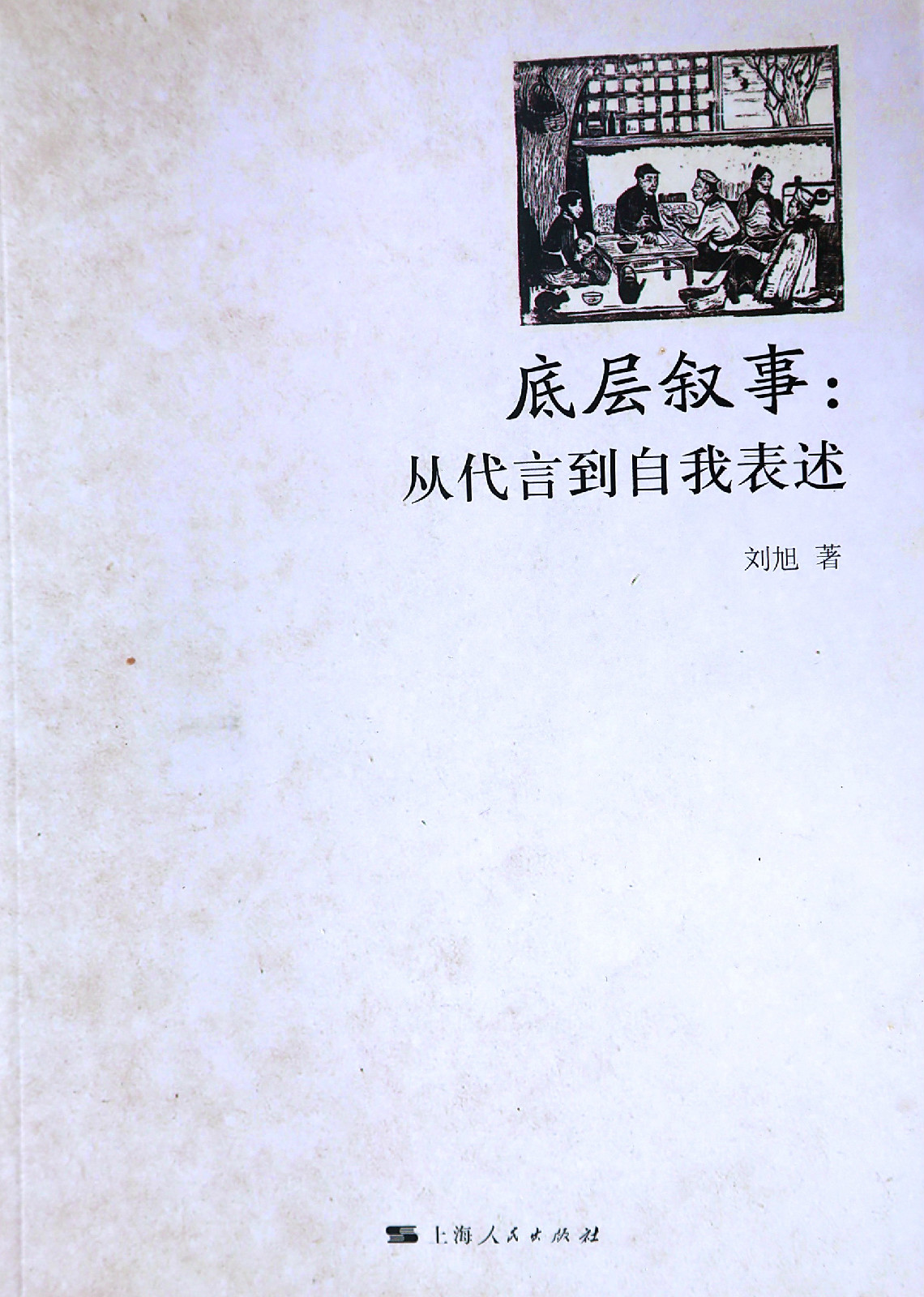
劉旭《底層敘事:從代言到自我表述》
《底層敘事:從代言到自我表述》主要研究了1976年至2010年間當代文學中的底層形象,首先從理論上梳理了海內外對底層的各類研究,特別是分析了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印度底層研究的思想與方法的演變,將精英與底層之間的“代言”關係用十分尖銳的方式表達出來了,為後面兩個文學研究的部分提供了一個較為開闊的理論視野,無論是對作為精英的作家如高曉聲、余華和王安憶在處理底層形象時所面臨的困境所做的細緻的解讀,還是對“底層寫作”不能不面臨的純文學焦慮和中產階級趣味的討論,都顯示出作者一方面堅持從文學出發,但另一方面又不自限於文學,而是寄希望於將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思想史研究結合起來,既可以把握住文學自身的藝術、形式和形象的問題,又能將這些文學問題放到一個更大的社會歷史脈絡中加以理解,從而拓展了當代文學研究的視野與方法。
目錄
導論
序章 海內外底層研究概況
第一部分 文學、精英與現實
第一章 從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到印度底層研究
第二章 精英意識分析與批判
第三章 現代性籠罩下的底層“富”想像
第四章 當代三農文學與知識者的自我病態化
第二部分 當代文學中的底層形象的背後
第一章 苦難歷史的終結?
第二章 “國民性”籠罩下的陳奐生:論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
第三章 與底層的遊戲:余華的兩重世界
第四章 抽象化底層:王安憶小說的敘事特色分析
第五章 自我底層化與“跨國底層”
第六章 底層審美觀:作家的精英意識與審美觀的偏移
第三部分 “自我表述”的可能
第一章 底層寫作的困境:代言與純文學問題
第二章 打工文學:底層的自我表述?
第三章 與現代性糾結的底層日常生活
第四章 現代性內外:反思西方中心主義
結語
參 考 文 獻
劉旭《底層敘述——現代性話語的裂隙》
現今出版的底層研究專著為劉旭《底層敘述——現代性話語的裂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目錄為
序章 現代性話語籠罩下的底層
第一部分
第一章 近現代底層形象的變遷
第二章 彩票:底層致富幻像一種
第三章 吃飽之後怎樣
第四章 底層婚姻:在現代與封建之間
第五章 底層人格:在可愛與可恨之間
第二部分
第六章 文學中的底層形象與精英意識
第七章 “落難精英”與“勞動”女性
第八章 遠離農民的高曉聲
第九章 市民小說:高度庸俗化的精英敘述
終章 底層的“真”表述
附錄一:對蔡翔的訪談
附錄二 對王曉明的訪談
參考文獻
後記
本書致力發掘當代文學中底層形象的建構過程和方式。本書認為現代性話語在“自由”、“發展”的名義下對底層面目的遮蔽是空前的,精英意識/精英主義與現代性話語的直接關係極大地影響了底層的面目。本書前半部分分析現代性話語下底層的生存狀態,下半部分為作家作品中的精英意識分析。
序章梳理了底層概念的沿革,界定底層的主體為工人、農民和其他下層勞動者。之後分析了現代性話語的對社會的強大控制力量,它的可怕之處正在於對人的思想的無形控制,金錢和物質成為衡量人的價值的主要尺度,它使人們在不自覺中喪失了主動權,在個體性的掩蓋下奴役著人的思想和肉體。底層問題正是現代性敘述的最大的裂隙。然後具體分析底層形象的建構過程及方式:①梳理了近現代底層形象的變遷。本書認為從近代的小說界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從梁啓超到毛澤東,對底層的表述都是工具化的,即要動員底層,以集中全民的力量實現國家的現代化。②分析了底層的“富想像”,從彩票、股票、傳銷等入手,分析底層被吸引其中的現代性原因。社會不平等的加劇造成了當前的封建、資本、社會主義共存的“斷裂”狀態,但在現代性話語的誘惑下,不論是公務員、老闆、白領、教師、乃至底層的致富標準都達到了驚人的統一,千萬富翁成了人們共同的人生理想。③從余華的小說《活著》等來分析底層人物的精神狀態。余華認識到了底層也是有靈魂的、有生存權利的個體組成的群體。④分析底層的婚姻狀態,農民的婚姻不但遠未實現“現代”,而且越發得“封建”,莫言《憤怒的蒜苔》中人們對買賣婚姻的集體認同顯露了當前農民的婚姻也只能徘徊在封建和現代之間,貧窮之下生存就是他們的道德,他們必須以一種“反現代”的方式維持自己的生存。⑤通過對莫言小說的分析透視出完整的底層人格和生存常態。莫言他筆下的底層有著同等的可愛和可恨之處,他的作品還揭露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無論是在社會主義的“現代”,還是在資本主義的“現代”,都沒有改變底層受壓迫的命運。
⑥分析精英主義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改革開始之後,大多數作家在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不斷宣傳中接受了現代化發展理論,對底層問題的解決,大部分作家都要求底層要“自強”、“發展”,實現“現代化”被當成解決底層問題的根本途徑。⑦通過對“右派”“反思小說”的分析昭顯在工農被抬高為國家主人公的時代,底層的在知識精英心目中的實際地位。他們在“反思”的過程中只是痛苦於自己的落難遭遇,底層民眾的勞動特徵從一開始就未被重視過,小說中重點塑造的下放地的紅顏知己都被剝離了“勞動”特徵。勞動者只是作家自我中心的陪襯物。⑧通過對“農民作家”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分析,發現高曉聲從一開始就拋棄了現實中的農民,他成功的同時也是他失敗的開始,他筆下的農民成了靜態的存在,永遠停留在他成功的70年代末,他自己卻在現代化道路上不斷前進,不斷“發現”著新的視角來批判或嘲諷80年代前的“舊”農民。⑨從女作家池莉和張欣成功前後的變化分析市民小說家的更強的精英意識。池莉以《煩惱人生》一舉成名,張欣也由《愛由如何》等反映平民艱難生活的小說獲得好評,但在文壇聲譽日盛的同時是精英意識生長,對底層的同情被“發展”的冷漠代替,為“現代化”而瘋狂成了時代的最強音。
⑩回到原點:代言與底層自己發言的問題。問題仍在於那些自稱是“底層話語”的東西有多少是“底層的”話語,就是底層的真正思想到底是什麼?底層怎么才能自己說話?這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最終本書落點於知識分子必須為底層代言,但方式需要反思,尤其需要反思現代性話語下的精英意識。
滕翠欽《被忽略的繁複》
滕翠欽《被忽略的繁複——當下“底層文學”討論的文化研究》,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