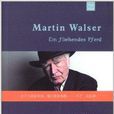本書是德國著名作家馬丁?瓦爾澤的中篇作品集,包括《驚馬奔逃》和《梅斯默的想法》兩篇。《驚馬奔逃》是一部反映“人到中年人生危機”的作品。中學和大學時代的同窗好友赫爾穆特和克勞斯分別與妻子在博登湖畔度假。克勞斯向赫爾穆特傾吐了苦悶遁世的心態,為自己的社會地位感到憂慮,更擔心失去年輕漂亮的妻子。後來,克勞斯掉入了波濤洶湧的博登湖。赫爾穆特死裡逃生,向克勞斯的妻子報喪。誰知克勞斯的妻子在悲痛之餘又向赫爾穆特夫婦敘述了心中的苦悶,並慶幸自己終於擺脫了克勞斯的羈絆……這部小說注重人的內在精神的表達,而且通過散文化的語言把生活的危機和失落展示得細膩而又微妙。
基本介紹
- 書名:外國中篇小說經典:驚馬奔逃
- 作者:馬丁·瓦爾澤 (Martin Walser)
-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 頁數:161頁
- 開本:32
- 品牌: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外文名:Ein Fliehendes Pferd
- 譯者:鄭華漢
- 出版日期:2013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2149865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戰後德國文壇巨匠馬丁·瓦爾澤“最成熟、最出色的一部作品”!
這本書包括《驚馬奔逃》和《梅斯默的想法》兩個中篇。《驚馬奔逃》是一部“反映人到中年人生危機”的作品,講述了中學和大學時代的同窗好友赫爾穆特和克勞斯,分別與妻子在博登湖畔度假,兩對夫婦偶然相遇,回憶過去的美好時光。《梅斯默的想法》由許多微型故事和箴言警句組成,被評論界認為是作者最美的一部散文作品。書中的主人公梅斯默無疑就是作者的第二個自我,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寫出“自傳的第四維”。
這本書包括《驚馬奔逃》和《梅斯默的想法》兩個中篇。《驚馬奔逃》是一部“反映人到中年人生危機”的作品,講述了中學和大學時代的同窗好友赫爾穆特和克勞斯,分別與妻子在博登湖畔度假,兩對夫婦偶然相遇,回憶過去的美好時光。《梅斯默的想法》由許多微型故事和箴言警句組成,被評論界認為是作者最美的一部散文作品。書中的主人公梅斯默無疑就是作者的第二個自我,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寫出“自傳的第四維”。
作者簡介
作者:(德國)馬丁·瓦爾澤(Martin Walser) 譯者:鄭華漢 李柳明 朱劉華
馬丁·瓦爾澤(Martin Walser),1927年3月24日出生於德國南部與瑞士和奧地利交界的博登湖畔的瓦塞堡。十一歲時父親去世,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在母親的餐館裡幫工。1944年應徵入伍。1946年至1951年在雷根斯堡和蒂賓根大學攻讀文學、歷史和哲學。1951年以研究奧地利作家卡夫卡的論文獲博士學位。其後,在斯圖加特任南德意志電台、電視台導演。1957年成為職業作家,定居在博登湖畔的努斯多夫。博登湖風景如畫,不僅為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創作環境,而且給予作家豐富的創作素材,他的許多作品均以這裡的生活為背景。瓦爾澤多次短期到美國和英國的大學講學,講授德國文學和創作課程。他是德國四七社成員、國際筆會德國中心理事、柏林藝術科學院院士、德意志語言文學科學院院士。
馬丁·瓦爾澤(Martin Walser),1927年3月24日出生於德國南部與瑞士和奧地利交界的博登湖畔的瓦塞堡。十一歲時父親去世,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在母親的餐館裡幫工。1944年應徵入伍。1946年至1951年在雷根斯堡和蒂賓根大學攻讀文學、歷史和哲學。1951年以研究奧地利作家卡夫卡的論文獲博士學位。其後,在斯圖加特任南德意志電台、電視台導演。1957年成為職業作家,定居在博登湖畔的努斯多夫。博登湖風景如畫,不僅為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創作環境,而且給予作家豐富的創作素材,他的許多作品均以這裡的生活為背景。瓦爾澤多次短期到美國和英國的大學講學,講授德國文學和創作課程。他是德國四七社成員、國際筆會德國中心理事、柏林藝術科學院院士、德意志語言文學科學院院士。
圖書目錄
驚馬奔逃
梅斯默的想法
瓦爾澤與他的小說《驚馬奔逃》
梅斯默的想法
瓦爾澤與他的小說《驚馬奔逃》
後記
在德國戰後文學史上,馬丁·瓦爾澤與海因里希·伯爾、君特·格拉斯、西格弗里德·倫茨,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四位作家。
馬丁·瓦爾澤(MartinWalser)於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生於德國南部與瑞士和奧地利交界的博登湖畔的瓦塞堡,十一歲時父親去世,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在母親的餐館裡幫工。一九四四年應徵入伍,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一年在雷根斯堡和蒂賓根大學攻讀文學、歷史和哲學。一九五一年以研究奧地利作家卡夫卡的論文獲博士學位。其後,在斯圖加特任南德意志電台、電視台導演。一九五七年成為職業作家,定居在博登湖畔的努斯多夫,博登湖風景如畫,不僅為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創作環境,而且給予作家豐富的創作素材,他的許多作品均以這裡的生活為背景。瓦爾澤多次短期到美國和英國的大學講學,講授德國文學和創作課程。他是德國四七社成員、國際筆會德國中心理事、柏林藝術科學院院士、德意志語言文學科學院院士。瓦爾澤曾獲多種文學獎,其中有四七社獎(1955)、黑塞獎(1957)、霍普特曼獎(1962)、席勒促進獎(1965、1980)、畢希納獎(1981)、荷爾德林獎(1996)、德國書業和平獎(1998)、阿勒曼尼文學獎(2002)、坎佩獎(2002)、科尼訥文學獎(2008)等。
瓦爾澤是一位主要以現實主義方法進行創作的作家,擅長描寫人物的內心世界,往往通過人物的自我內省反映社會生活的變遷。他主要的文學成就在小說和戲劇方面,此外,他還從事詩歌、評論、小品文、廣播劇、電視劇的創作。迄今為止,瓦爾澤已出版了二十多部長篇和中篇小說,重要的有《菲利普斯堡的婚事》(1957)、《間歇》(1960)、《獨角獸》(1966)、《愛情的彼岸》(1976)、《驚馬奔逃》(1978)、《天鵝之屋》(1980)、《激浪》(1985)、《多爾勒和沃爾夫》(1987)、《狩獵》(1988)、《童年的抵抗》(1991)、《沒有彼此》(1993)、《芬克的戰爭》(1996)、《進涌的流泉》(1998)、《愛情的履歷》(2001)、《批評家之死》(2002)、《愛的瞬間》(2004)、《恐懼之花》(2006)、《戀愛中的男人》(2008)、《寶貝兒子》(2011)、《第十三章》(2012)等。
瓦爾澤的小說主要反映德國的現實生活,主人公大多是中下層知識分子,作者揭示他們尋找個人幸福以及在事業上的奮鬥,側重於描寫人物的精神生活和感情糾葛。瓦爾澤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認為文學創作應該參與推進社會的進步,使其更加民主。他一方面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一方面吸取現代派的手法和技巧,尤其推崇普魯斯特。他的作品長於心理分析,以借喻、譏諷、注重細節描寫見長,充滿濃郁的鄉土氣息。瓦爾澤被譽為“駕馭語言的能手”(德國著名文學評論家馬塞爾·萊希一拉尼茨基語),他的小說被稱作優美的散文作品。在敘述中插入對話是他的小說的一個特色,這些對話不加引號,讀者必須細心閱讀方能辨出說話者。瓦爾澤稱自己是古代阿雷曼人的後裔,因此他的作品中常有方言出現。他的不少小說在情節上雖然並無上下承接關係,但是一個主人公常常出現在幾本書里,如《間歇》(1960)、《獨角獸》(1966)和《墮落》(1973)中的昂塞姆·克里斯特萊因,《愛情的彼岸》(1976)和《致洛爾特·李斯特的信》(1982)中的弗蘭茨-霍恩,《驚馬奔逃》(1978)和《激浪》(1985)中的赫爾穆特·哈爾姆,《天鵝之屋》(1980)和《狩獵》(1988)里的房地產商格特利布·齊日姆。因此也有人將它們稱作三部曲或姐妹篇。六十年代初,在《菲城婚事》(1957)和《間歇》(1960)等小說獲得成功之後,瓦爾澤又開始創作劇本。他的劇作多以政治、歷史題材為內容,他善於運用布萊希特敘事劇的表現手法,描寫靜態的現實和難以改變的狀況,劇本的基調是嘲諷和悲傷的。在一些劇本中,他用超現實主義和一些怪誕的手法批評社會制度,並再現了當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衝突。他的重要劇作有:《橡樹和安哥拉兔》(1962)、《比真人高大的克羅特先生》(1964)、《黑天鵝》(1964)、《母豬遊戲》(1975)、《在歌德的手中》(1982)、《耳光》(1986)等。
《驚馬奔逃》(EinfiehendesPferd)這部小說是作家在一九七七年夏天僅用了兩個星期完成的,是一部反映“人到中年人生危機”的作品。小說的情節非常簡單:中學和大學時代的同窗好友赫爾穆特·哈爾姆和克勞斯·布赫,分別與妻子在博登湖畔度假,兩對夫婦偶然相遇。他們回憶起過去的美好時光,不勝感慨,昔日的優等生赫爾穆特,如今成績平平,而當年的調皮鬼克勞斯,今天則已功成名就。克勞斯在林中勇攔驚馬的壯舉,贏得了赫爾穆特的由衷欽佩。湖上泛舟時,克勞斯敞開心扉,向赫爾穆特傾吐了苦悶遁世的心態,作為事業上的成功者,他日感精力不濟,為自己的社會地位感到憂慮,更擔心失去年輕漂亮的妻子。談話當口兒,湖上驟起風暴,赫爾穆特失手鬆開了船舵。舵柄將克勞斯打入波濤洶湧的博登湖。赫爾穆特死裡逃生,向克勞斯的妻子報喪。誰知克勞斯的妻子在悲痛之餘又向赫爾穆特夫婦敘述了內心苦悶,並慶幸自己終於擺脫了克勞斯的羈絆。突然,克勞斯出現在他們面前,他聽到了妻子講述的一切,備感羞愧。兩位故友經過幾天的交往,彼此似乎都有了新的了解,兩人無言以對。假期結束了,這兩對夫婦分別離開了博登湖畔,返回各自的城市。全書的結尾是一句與小說的開頭完全相同的話,作者似乎在暗示:一切依然照舊,他們的生活又將從頭開始。
《驚馬奔逃》一書在一九七八年春出版之後在聯邦德國文壇引起轟動,它不僅躋入當年十大暢銷書之列,而且獲得評論界幾乎眾口一詞的讚揚。萊希一拉尼茨基在聯邦德國最有影響的日報《法蘭克福匯報》文學版上發表文章,他寫道:“我認為,馬丁·瓦爾澤的中篇小說《驚馬奔逃》是他最成熟、最出色的書。這個描寫兩對夫婦的故事是這些年來德語散文的一部傑作。”瓦爾澤本人對這部小說也非常得意,他曾獨自或與人合作將小說分別改編成劇本(1985年7月19日梅爾斯堡海默勒工廠小劇場首演,烏爾利希·庫翁導演)、廣播劇(1986年3月17日巴伐利亞電台首播)和電視劇(1986年3月26日電視一台首播,彼得·波瓦斯導演)。
《驚馬奔逃》是一部中篇小說(Novelle),一般來說,德國的Novelle,都是寫一件非同尋常的事件(unerhorteBegebenheit),篇幅介於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之間。一八七○年,德國作家保爾·海澤提出德國中篇小說Novelle的鷹理論。按此理論,在中篇小說里要有一個動物,它在小說的情節轉折上起著重要作用,既突出本篇,使之有別於其他小說,而且又對全篇小說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作者聲稱,他“在這部小說里幾乎完全按此理論行事”,《驚馬奔逃》中的翻船落水自然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件,而驚馬則是畫龍點睛的“鷹”。
小說的篇名得自於作者女兒的一幅畫。當時,瓦爾澤剛剛寫完這本書的初稿,偶爾在女兒那裡發現了一幅畫馬的水彩畫,他很喜歡這幅畫。他想,書中有一處描寫了一片廣闊無邊的大森林,不妨讓一匹馬在林中飛奔。於是就補寫了驚馬奔逃和克勞斯攔住驚馬的場面。他想通過驚馬來表示一種與周圍環境不相融的含義。“這是一個受環境影響、使神經失去本性的比喻,我把它作為主題,並擴充了內容,所以我選了這個書名,我也比較喜歡這個書名。”(瓦爾澤語)《驚馬奔逃》與作家的生活關係密切,故事發生的地點是他熟悉的博登湖畔,書中主人公哈爾姆身上有許多作家本人的痕跡,而克勞斯則是以作家大女兒的男朋友為主要原型。
《驚馬奔逃》的中文譯本最早發表在《世界文學》一九九。年第三期,當時筆者負責選編“馬丁·瓦爾澤專輯”,刊登了他的兩部代表性作品:中篇小說《驚馬奔逃》和劇本《橡樹和安哥拉兔》。瓦爾澤先生獲悉筆者在選編“專輯”之後,特意寄來了他剛剛出版的並有他親筆簽名的文集《神聖的碎片》(HeiligeBrocken,1988),書中收集了作家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六年的部分散文和詩歌,因此,“馬丁·瓦爾澤專輯”里也同時發表了幾首詩歌的中文譯文。其實,詩歌並非馬丁·瓦爾澤擅長的文學樣式,其數量在他的作品中也僅占很小的比重,它們大多散見於期刊、多人詩選和作家本人的文選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瓦爾澤先生以及聯邦德國蘇爾坎普出版社當年為“專輯”的發表不僅免費提供著作權,而且予以資助,瓦爾澤先生還專門撰寫《致中國讀者》一文,他親筆手寫的德文信和中文譯文同時發表在“專輯”的最前面。《驚馬奔逃》的譯者李柳明和鄭華漢,當年剛從德國進修歸國,他們在德國期間曾經採訪過瓦爾澤先生,因此不僅承擔了翻譯工作,而且將採訪錄音整理出來,摘要以《博登湖畔一席談》為題發表在同期《世界文學》。這一期《世界文學》的封面是由前主編高莽根據瓦爾澤的照片以傳統中國畫技法為其“造像”,或許由於使用的照片較舊,許多德國作家都認為更像另一位德國作家阿爾弗雷德·安德森,刊登在文中作家小傳里的鋼筆素描肖像,是高莽按照作家寄來的簽名近照所作,可以說是惟妙惟肖。封二上還刊登了那幅讓《驚馬奔逃》這部小說得以冠名的奔馬水彩畫。
《驚馬奔逃》是第一部在中國大陸正式獲得授權出版的中文版瓦爾澤作品,此後的二十多年裡,瓦爾澤的《在水一方》、《批評家之死》(2004)、《進涌的流泉》(2004),《菲利普斯堡的婚事》(2008)、《戀愛中的男人》(2009)等重要作品被陸續翻譯成中文出版。
二○○八年十月,年逾八旬的瓦爾澤和夫人首次訪問中國。瓦爾澤與中國作家莫言的對談,無疑是中德文壇最高級別的交流。為了這次對談,瓦爾澤認真閱讀了莫言的《紅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等作品,不僅給予莫言很高的讚揚,而且多次在德國媒體大加推薦莫言的作品。二○○九年,瓦爾澤的《戀愛中的男人》榮獲了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聯合主辦的“二十一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微山湖獎”。頒獎之際,瓦爾澤再次來到北京,時任中國出版集團總裁的聶震寧與作家莫言為瓦爾澤頒發了“微山湖獎”。
德國書業協會一九九八年在向瓦爾澤頒發德國書業和平獎的頒獎詞中有這么一段話:“瓦爾澤以他的作品描寫和闡釋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德國現實生活,他的小說和隨筆向德國人展現了自己的祖國,向世界展現了德國,讓德國人更了解祖國,讓世界更了解德國”。把更多的瓦爾澤的書譯介到中國,讓中國讀者有機會深入了解這位通過自己的文學作品向世人展示德國現實生活的偉大作家,是筆者孜孜追求的目標。筆者當年有幸成為《驚馬奔逃》中文譯本的責任編輯,一九九。年來到德國之後,曾經多次見到作者本人,並且榮幸地成為瓦爾澤作品的中文著作權代理人,為讓廣大的中文讀者讀到瓦爾澤的作品盡了綿薄之力。近幾年,已近耄耋之年的瓦爾澤仍然筆耕不輟,幾乎每年都有新作問世。《寶貝兒子》、《第十三章》等最新的長篇小說目前正在翻譯之中,不久即可與中國讀者見面,瓦爾澤這位文學大師一定會給讀者們帶來新的精彩。
蔡鴻君
二○一三年五月三十日於德國小鎮尼德多夫
馬丁·瓦爾澤(MartinWalser)於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生於德國南部與瑞士和奧地利交界的博登湖畔的瓦塞堡,十一歲時父親去世,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在母親的餐館裡幫工。一九四四年應徵入伍,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一年在雷根斯堡和蒂賓根大學攻讀文學、歷史和哲學。一九五一年以研究奧地利作家卡夫卡的論文獲博士學位。其後,在斯圖加特任南德意志電台、電視台導演。一九五七年成為職業作家,定居在博登湖畔的努斯多夫,博登湖風景如畫,不僅為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創作環境,而且給予作家豐富的創作素材,他的許多作品均以這裡的生活為背景。瓦爾澤多次短期到美國和英國的大學講學,講授德國文學和創作課程。他是德國四七社成員、國際筆會德國中心理事、柏林藝術科學院院士、德意志語言文學科學院院士。瓦爾澤曾獲多種文學獎,其中有四七社獎(1955)、黑塞獎(1957)、霍普特曼獎(1962)、席勒促進獎(1965、1980)、畢希納獎(1981)、荷爾德林獎(1996)、德國書業和平獎(1998)、阿勒曼尼文學獎(2002)、坎佩獎(2002)、科尼訥文學獎(2008)等。
瓦爾澤是一位主要以現實主義方法進行創作的作家,擅長描寫人物的內心世界,往往通過人物的自我內省反映社會生活的變遷。他主要的文學成就在小說和戲劇方面,此外,他還從事詩歌、評論、小品文、廣播劇、電視劇的創作。迄今為止,瓦爾澤已出版了二十多部長篇和中篇小說,重要的有《菲利普斯堡的婚事》(1957)、《間歇》(1960)、《獨角獸》(1966)、《愛情的彼岸》(1976)、《驚馬奔逃》(1978)、《天鵝之屋》(1980)、《激浪》(1985)、《多爾勒和沃爾夫》(1987)、《狩獵》(1988)、《童年的抵抗》(1991)、《沒有彼此》(1993)、《芬克的戰爭》(1996)、《進涌的流泉》(1998)、《愛情的履歷》(2001)、《批評家之死》(2002)、《愛的瞬間》(2004)、《恐懼之花》(2006)、《戀愛中的男人》(2008)、《寶貝兒子》(2011)、《第十三章》(2012)等。
瓦爾澤的小說主要反映德國的現實生活,主人公大多是中下層知識分子,作者揭示他們尋找個人幸福以及在事業上的奮鬥,側重於描寫人物的精神生活和感情糾葛。瓦爾澤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認為文學創作應該參與推進社會的進步,使其更加民主。他一方面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一方面吸取現代派的手法和技巧,尤其推崇普魯斯特。他的作品長於心理分析,以借喻、譏諷、注重細節描寫見長,充滿濃郁的鄉土氣息。瓦爾澤被譽為“駕馭語言的能手”(德國著名文學評論家馬塞爾·萊希一拉尼茨基語),他的小說被稱作優美的散文作品。在敘述中插入對話是他的小說的一個特色,這些對話不加引號,讀者必須細心閱讀方能辨出說話者。瓦爾澤稱自己是古代阿雷曼人的後裔,因此他的作品中常有方言出現。他的不少小說在情節上雖然並無上下承接關係,但是一個主人公常常出現在幾本書里,如《間歇》(1960)、《獨角獸》(1966)和《墮落》(1973)中的昂塞姆·克里斯特萊因,《愛情的彼岸》(1976)和《致洛爾特·李斯特的信》(1982)中的弗蘭茨-霍恩,《驚馬奔逃》(1978)和《激浪》(1985)中的赫爾穆特·哈爾姆,《天鵝之屋》(1980)和《狩獵》(1988)里的房地產商格特利布·齊日姆。因此也有人將它們稱作三部曲或姐妹篇。六十年代初,在《菲城婚事》(1957)和《間歇》(1960)等小說獲得成功之後,瓦爾澤又開始創作劇本。他的劇作多以政治、歷史題材為內容,他善於運用布萊希特敘事劇的表現手法,描寫靜態的現實和難以改變的狀況,劇本的基調是嘲諷和悲傷的。在一些劇本中,他用超現實主義和一些怪誕的手法批評社會制度,並再現了當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衝突。他的重要劇作有:《橡樹和安哥拉兔》(1962)、《比真人高大的克羅特先生》(1964)、《黑天鵝》(1964)、《母豬遊戲》(1975)、《在歌德的手中》(1982)、《耳光》(1986)等。
《驚馬奔逃》(EinfiehendesPferd)這部小說是作家在一九七七年夏天僅用了兩個星期完成的,是一部反映“人到中年人生危機”的作品。小說的情節非常簡單:中學和大學時代的同窗好友赫爾穆特·哈爾姆和克勞斯·布赫,分別與妻子在博登湖畔度假,兩對夫婦偶然相遇。他們回憶起過去的美好時光,不勝感慨,昔日的優等生赫爾穆特,如今成績平平,而當年的調皮鬼克勞斯,今天則已功成名就。克勞斯在林中勇攔驚馬的壯舉,贏得了赫爾穆特的由衷欽佩。湖上泛舟時,克勞斯敞開心扉,向赫爾穆特傾吐了苦悶遁世的心態,作為事業上的成功者,他日感精力不濟,為自己的社會地位感到憂慮,更擔心失去年輕漂亮的妻子。談話當口兒,湖上驟起風暴,赫爾穆特失手鬆開了船舵。舵柄將克勞斯打入波濤洶湧的博登湖。赫爾穆特死裡逃生,向克勞斯的妻子報喪。誰知克勞斯的妻子在悲痛之餘又向赫爾穆特夫婦敘述了內心苦悶,並慶幸自己終於擺脫了克勞斯的羈絆。突然,克勞斯出現在他們面前,他聽到了妻子講述的一切,備感羞愧。兩位故友經過幾天的交往,彼此似乎都有了新的了解,兩人無言以對。假期結束了,這兩對夫婦分別離開了博登湖畔,返回各自的城市。全書的結尾是一句與小說的開頭完全相同的話,作者似乎在暗示:一切依然照舊,他們的生活又將從頭開始。
《驚馬奔逃》一書在一九七八年春出版之後在聯邦德國文壇引起轟動,它不僅躋入當年十大暢銷書之列,而且獲得評論界幾乎眾口一詞的讚揚。萊希一拉尼茨基在聯邦德國最有影響的日報《法蘭克福匯報》文學版上發表文章,他寫道:“我認為,馬丁·瓦爾澤的中篇小說《驚馬奔逃》是他最成熟、最出色的書。這個描寫兩對夫婦的故事是這些年來德語散文的一部傑作。”瓦爾澤本人對這部小說也非常得意,他曾獨自或與人合作將小說分別改編成劇本(1985年7月19日梅爾斯堡海默勒工廠小劇場首演,烏爾利希·庫翁導演)、廣播劇(1986年3月17日巴伐利亞電台首播)和電視劇(1986年3月26日電視一台首播,彼得·波瓦斯導演)。
《驚馬奔逃》是一部中篇小說(Novelle),一般來說,德國的Novelle,都是寫一件非同尋常的事件(unerhorteBegebenheit),篇幅介於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之間。一八七○年,德國作家保爾·海澤提出德國中篇小說Novelle的鷹理論。按此理論,在中篇小說里要有一個動物,它在小說的情節轉折上起著重要作用,既突出本篇,使之有別於其他小說,而且又對全篇小說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作者聲稱,他“在這部小說里幾乎完全按此理論行事”,《驚馬奔逃》中的翻船落水自然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件,而驚馬則是畫龍點睛的“鷹”。
小說的篇名得自於作者女兒的一幅畫。當時,瓦爾澤剛剛寫完這本書的初稿,偶爾在女兒那裡發現了一幅畫馬的水彩畫,他很喜歡這幅畫。他想,書中有一處描寫了一片廣闊無邊的大森林,不妨讓一匹馬在林中飛奔。於是就補寫了驚馬奔逃和克勞斯攔住驚馬的場面。他想通過驚馬來表示一種與周圍環境不相融的含義。“這是一個受環境影響、使神經失去本性的比喻,我把它作為主題,並擴充了內容,所以我選了這個書名,我也比較喜歡這個書名。”(瓦爾澤語)《驚馬奔逃》與作家的生活關係密切,故事發生的地點是他熟悉的博登湖畔,書中主人公哈爾姆身上有許多作家本人的痕跡,而克勞斯則是以作家大女兒的男朋友為主要原型。
《驚馬奔逃》的中文譯本最早發表在《世界文學》一九九。年第三期,當時筆者負責選編“馬丁·瓦爾澤專輯”,刊登了他的兩部代表性作品:中篇小說《驚馬奔逃》和劇本《橡樹和安哥拉兔》。瓦爾澤先生獲悉筆者在選編“專輯”之後,特意寄來了他剛剛出版的並有他親筆簽名的文集《神聖的碎片》(HeiligeBrocken,1988),書中收集了作家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六年的部分散文和詩歌,因此,“馬丁·瓦爾澤專輯”里也同時發表了幾首詩歌的中文譯文。其實,詩歌並非馬丁·瓦爾澤擅長的文學樣式,其數量在他的作品中也僅占很小的比重,它們大多散見於期刊、多人詩選和作家本人的文選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瓦爾澤先生以及聯邦德國蘇爾坎普出版社當年為“專輯”的發表不僅免費提供著作權,而且予以資助,瓦爾澤先生還專門撰寫《致中國讀者》一文,他親筆手寫的德文信和中文譯文同時發表在“專輯”的最前面。《驚馬奔逃》的譯者李柳明和鄭華漢,當年剛從德國進修歸國,他們在德國期間曾經採訪過瓦爾澤先生,因此不僅承擔了翻譯工作,而且將採訪錄音整理出來,摘要以《博登湖畔一席談》為題發表在同期《世界文學》。這一期《世界文學》的封面是由前主編高莽根據瓦爾澤的照片以傳統中國畫技法為其“造像”,或許由於使用的照片較舊,許多德國作家都認為更像另一位德國作家阿爾弗雷德·安德森,刊登在文中作家小傳里的鋼筆素描肖像,是高莽按照作家寄來的簽名近照所作,可以說是惟妙惟肖。封二上還刊登了那幅讓《驚馬奔逃》這部小說得以冠名的奔馬水彩畫。
《驚馬奔逃》是第一部在中國大陸正式獲得授權出版的中文版瓦爾澤作品,此後的二十多年裡,瓦爾澤的《在水一方》、《批評家之死》(2004)、《進涌的流泉》(2004),《菲利普斯堡的婚事》(2008)、《戀愛中的男人》(2009)等重要作品被陸續翻譯成中文出版。
二○○八年十月,年逾八旬的瓦爾澤和夫人首次訪問中國。瓦爾澤與中國作家莫言的對談,無疑是中德文壇最高級別的交流。為了這次對談,瓦爾澤認真閱讀了莫言的《紅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等作品,不僅給予莫言很高的讚揚,而且多次在德國媒體大加推薦莫言的作品。二○○九年,瓦爾澤的《戀愛中的男人》榮獲了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聯合主辦的“二十一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微山湖獎”。頒獎之際,瓦爾澤再次來到北京,時任中國出版集團總裁的聶震寧與作家莫言為瓦爾澤頒發了“微山湖獎”。
德國書業協會一九九八年在向瓦爾澤頒發德國書業和平獎的頒獎詞中有這么一段話:“瓦爾澤以他的作品描寫和闡釋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德國現實生活,他的小說和隨筆向德國人展現了自己的祖國,向世界展現了德國,讓德國人更了解祖國,讓世界更了解德國”。把更多的瓦爾澤的書譯介到中國,讓中國讀者有機會深入了解這位通過自己的文學作品向世人展示德國現實生活的偉大作家,是筆者孜孜追求的目標。筆者當年有幸成為《驚馬奔逃》中文譯本的責任編輯,一九九。年來到德國之後,曾經多次見到作者本人,並且榮幸地成為瓦爾澤作品的中文著作權代理人,為讓廣大的中文讀者讀到瓦爾澤的作品盡了綿薄之力。近幾年,已近耄耋之年的瓦爾澤仍然筆耕不輟,幾乎每年都有新作問世。《寶貝兒子》、《第十三章》等最新的長篇小說目前正在翻譯之中,不久即可與中國讀者見面,瓦爾澤這位文學大師一定會給讀者們帶來新的精彩。
蔡鴻君
二○一三年五月三十日於德國小鎮尼德多夫
序言
在中國的當代文學裡,“中篇小說”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長、中、短這樣一個長度順序,中篇小說就是介於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之間的一個小說體類。依照“不成文的規定”,十萬字以上的小說叫長篇小說,三萬字以內的小說叫短篇小說,在這樣一個“不成文”的邏輯體系內,三萬字至十萬字的小說當然是中篇小說。
然而,一旦跳出中國的當代文學,“中篇小說”的身份卻是可疑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常識告訴我們,儘管《阿Q正傳》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說的發軔和模板,可是,《阿Q正傳》在《晨報副刊》連載的時候,中國的現代文學尚未出現“中篇小說”這個概念。
如果我們願意,跳出漢語的世界,“中篇小說”的身份就越發可疑了。在西語裡,我們很難找到與“中篇小說”相對應的概念,英語裡的Longshortstory勉強算一個,可是,顧名思義,Longshortstory的著眼點依然是短篇,所謂的中篇小說,只不過比短篇小說長一些,是加長版的或加強版的短篇。
那一次在柏林,我專門請教過一位德國的文學教師,他說,說起小說,拉丁語裡的Novus這個單詞無法迴避,它的意思是“新鮮”的,“從未出現過”的事件、人物和事態發展,基於此,Novus當然具備了“敘事”的性質。義大利語中的Novella、德語裡的Novelle和英語單詞Novel都是從Novus那裡挪移過來的。——如果我們粗暴一點,我們完全可以把那些單詞統統翻譯成“講故事”。
德國教師的這番話讓我恍然大悟:傳統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學傳統面前,“中篇小說”這個概念的確可以省略。姚明兩米一六,是個男人;我一米七四,也是男人,絕不是“中篇男人”。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小說家需要對西方的文學傳統負責任么?不需要。這個回答既可以理直氣壯,也可以心平氣和。
我第一次接觸“中篇小說”這個概念是在遙遠的“傷痕文學”時期。“傷痕文學”,我們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學”或“訴苦文學”,它是激憤的。它急於表達。因為有“傷痕”,有故事,這樣的表達就一定比“吶喊”需要更多的時間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劍。十年磨一劍,那實在太憋屈了。還有什麼比“中篇小說”更適合“叫屈”與“訴苦”呢?沒有了。
我們的“中篇小說”正是在“傷痕文學”中發育並茁壯起來的,是“傷痕文學”完善了“中篇小說”的實踐美學和批判美學,在今天,無論我們如何評判“傷痕文學”,它對“中篇小說”這個小說體類的貢獻都不容抹殺。直白地說,“傷痕文學”讓“中篇小說”成熟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從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到晚生代文學那裡讀到中篇佳構的邏輯依據。中國的當代文學能達到現有的水準,中篇小說功不可沒。事實永遠勝於雄辯,新時期得到認可的中國作家們,除了極少數,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這樣的文學場景放在其他國家真的不多見。——中國的文學月刊太多,大型的雙月刊也多,它們需要。沒有一個國家的中篇小說比中國新時期的中篇小說更繁榮、成氣候,這句話我敢說。嗨,誰不敢說呢。
說中篇小說構成了中國當代小說的一個特色,這句話也不為過。
當然,我絕不會說西方的中篇小說不行,這樣大膽的話我可不敢說。雖然沒有明確的“中篇”概念,他們的“長短篇”或“短長篇”卻是佳作迭出的。我至今記得一九八三年的秋天:《老人與海》讓我領略了別樣的“小說”,它的節奏與語氣和長篇不一樣,和短篇也不一樣。——鋪張,卻見好就收。
所以說,“合法性”無非就是這樣一個東西:它始於“非法”,因為行為人有足夠的創造性和尊嚴感,歷史和傳統只能讓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然而,一旦跳出中國的當代文學,“中篇小說”的身份卻是可疑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常識告訴我們,儘管《阿Q正傳》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說的發軔和模板,可是,《阿Q正傳》在《晨報副刊》連載的時候,中國的現代文學尚未出現“中篇小說”這個概念。
如果我們願意,跳出漢語的世界,“中篇小說”的身份就越發可疑了。在西語裡,我們很難找到與“中篇小說”相對應的概念,英語裡的Longshortstory勉強算一個,可是,顧名思義,Longshortstory的著眼點依然是短篇,所謂的中篇小說,只不過比短篇小說長一些,是加長版的或加強版的短篇。
那一次在柏林,我專門請教過一位德國的文學教師,他說,說起小說,拉丁語裡的Novus這個單詞無法迴避,它的意思是“新鮮”的,“從未出現過”的事件、人物和事態發展,基於此,Novus當然具備了“敘事”的性質。義大利語中的Novella、德語裡的Novelle和英語單詞Novel都是從Novus那裡挪移過來的。——如果我們粗暴一點,我們完全可以把那些單詞統統翻譯成“講故事”。
德國教師的這番話讓我恍然大悟:傳統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學傳統面前,“中篇小說”這個概念的確可以省略。姚明兩米一六,是個男人;我一米七四,也是男人,絕不是“中篇男人”。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小說家需要對西方的文學傳統負責任么?不需要。這個回答既可以理直氣壯,也可以心平氣和。
我第一次接觸“中篇小說”這個概念是在遙遠的“傷痕文學”時期。“傷痕文學”,我們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學”或“訴苦文學”,它是激憤的。它急於表達。因為有“傷痕”,有故事,這樣的表達就一定比“吶喊”需要更多的時間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劍。十年磨一劍,那實在太憋屈了。還有什麼比“中篇小說”更適合“叫屈”與“訴苦”呢?沒有了。
我們的“中篇小說”正是在“傷痕文學”中發育並茁壯起來的,是“傷痕文學”完善了“中篇小說”的實踐美學和批判美學,在今天,無論我們如何評判“傷痕文學”,它對“中篇小說”這個小說體類的貢獻都不容抹殺。直白地說,“傷痕文學”讓“中篇小說”成熟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從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到晚生代文學那裡讀到中篇佳構的邏輯依據。中國的當代文學能達到現有的水準,中篇小說功不可沒。事實永遠勝於雄辯,新時期得到認可的中國作家們,除了極少數,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這樣的文學場景放在其他國家真的不多見。——中國的文學月刊太多,大型的雙月刊也多,它們需要。沒有一個國家的中篇小說比中國新時期的中篇小說更繁榮、成氣候,這句話我敢說。嗨,誰不敢說呢。
說中篇小說構成了中國當代小說的一個特色,這句話也不為過。
當然,我絕不會說西方的中篇小說不行,這樣大膽的話我可不敢說。雖然沒有明確的“中篇”概念,他們的“長短篇”或“短長篇”卻是佳作迭出的。我至今記得一九八三年的秋天:《老人與海》讓我領略了別樣的“小說”,它的節奏與語氣和長篇不一樣,和短篇也不一樣。——鋪張,卻見好就收。
所以說,“合法性”無非就是這樣一個東西:它始於“非法”,因為行為人有足夠的創造性和尊嚴感,歷史和傳統只能讓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