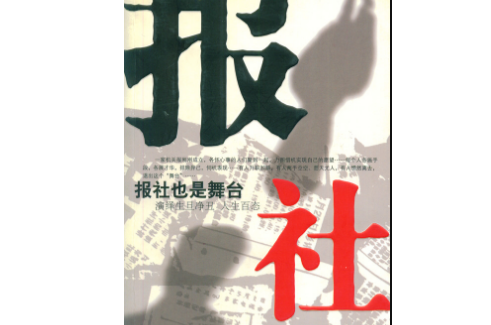基本信息
作者:亞子
出版社:文化藝術出版社
頁數:318頁
字數:215千字
開本:32開
版次:2005年5月第一版
書號:ISBN-7-5039-2761-5/I·1254
定價:20.00元
作者介紹
內容簡介
新聞在當今這個時代,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但是,一條新聞是怎樣產生的呢?一張報紙是如何出爐的呢?這些新聞人,他們的私人生活是怎樣的呢?他們所遵循的遊戲規則,與官場的遊戲規則,與商場的遊戲規則,是相同,還是有所區別呢?他們的生存競爭、人際關係,也像我們日常見到的那樣激烈、扭曲和醜陋嗎?
小說以主人公袁潤生、方正則的編輯記者生涯為線索,以某部所屬報社為舞台,生動刻畫了一群生存在新聞傳媒中的人物形象,對他們的獨特神貌,以及他們所遵循的新聞媒體的遊戲規則,都作了浮世繪似的傳神描寫,對傳統媒體中所存在的種種滯後於這個時代改革精神的古怪荒謬現象及其體制方面的根源,對報社與上級領導機關、下屬機構的關係,對傳統媒體在今天的困境,特別是對生存於其中的新聞從業人員生存競爭的殘酷,靈魂蛻變的煎熬,命運轉折的荒謬,人際關係的扭曲,美醜混淆的複雜,善惡搏擊的激烈,以及下級接待上級記者搞三陪,上級機關把報社當作小金庫,如何朝下邊攤派報紙訂數,賣刊號,等等發生在新聞媒體和新聞隊伍中的腐敗醜惡現象,都作了較為深刻的探索和揭示。
同時,也從一個側面,為正在進行的新聞體制改革,探尋了某些根據。
作者是一位資深記者,正是由於寫的是自己身邊的人和事,所以故事敘述起來從容不迫,駕輕就熟,真實、傳神的細節隨手拈來,本來很複雜的矛盾和人物關係,在他的筆下,變得非常清晰、真切,種種場景如在眼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敘述語言獨具特色,很得中國傳統小說——諸如三言二拍等的神韻,節奏明快,語言簡潔流暢,生動傳神,捨棄了作者過去常用的大段心理刻畫手法,大大加快了故事的演進。
內容節選
1
這是一棟獨立的別墅,藏在綠樹掩映之中。南國的樹葉子闊大,樹冠就顯得特別濃密,不是走到跟前,很難發現這片樹林之中還有一棟房子。
袁潤生推門進去。
一名武警正在對門的一張桌子後面坐著,見有人進來,“嚯”地站起,敬了一個禮,然後上前一步,擋住路,輕聲道:“首長在休息。”
袁潤生揚了揚手裡的一疊稿紙,也輕聲說:“我找蘇司長審稿子,剛才電話約好了。”
正說話間,旁邊一間房門開了,韓部長的秘書李一走出來,見是袁潤生,就對武警悄聲道:“是駐會記者,蘇司長等著呢。”說罷,招招手,領著袁潤生往裡走。
樓道里燈沒有開,就靠門口那盞燈的光線延伸過來,腳底下看不甚清楚,從腳感和聲音判斷,肯定是原木地板,而且有一定年數了。
倆人都不說話,只顧往前走。
昏暗的樓道里只有“咯吱咯吱”的腳步聲,顯得有些神秘。
在一扇門前,他們站住,李一轉頭小聲說:“蘇司長住這兒。”
李一敲門的時候,袁潤生想,蘇司長住一樓,那韓部長肯定是住樓上了。
隱約聽見裡面有人說:“請進。”
李一推開門,回頭又附在袁潤生耳旁,說:“抓緊點,別待太久了。”
李一領著袁潤生,一邊朝里走一邊說:“蘇司長,報社袁記者來了。”
蘇司長從沙發里站起來,伸手與袁潤生相握,熱情地說:“來,來,小袁,辛苦你了。”
這是一個身材高挑的女人,根據其職務推算,應該有40來歲了,但身材臉相又不像。
這女人的手真柔軟!兩隻手接觸的剎那,袁潤生有點心猿意馬。
“給蘇司長添麻煩了,這么晚來打擾您。”
袁潤生的手沒敢在蘇司長手裡多停,輕輕一碰,隨即逃開,嘴裡公式化地客氣著,把手中那疊紙遞過去。
袁潤生覺得,自己心中的慌亂並沒能逃過蘇司長的覺察,他看見蘇司長的眼神盯了自己一下,訝然一笑,接過袁潤生遞過來的文稿,在沙發上坐下,拉開旁邊的落地燈,一面示意袁潤生坐在另一隻沙發上。
袁潤生坐下,轉臉環顧,這才看見房間裡還有一個人,竟然是韓部長,高大的身軀正斜靠在床頭上,那張威嚴的臉,此時正笑眯眯地朝這邊看著。袁潤生嚇了一跳,連忙把剛剛挨著沙發的屁股重又抬起來,站直了,恭恭敬敬地叫了一聲:“韓部長好。”
“喔,喔,坐吧,坐吧。”
韓部長一臉的慈祥,朝袁潤生點了點頭,聲音很和藹。袁潤生這才穩住神,正準備重新在沙發上坐下來,又看見李一站著沒地兒坐,就謙讓道:“李秘書坐吧。”
李一說:“你坐,你坐。”
給袁潤生倒了杯水,又給韓部長、蘇司長打了招呼,李一才退出去。
這顯然是一間首長隨員的房間,沒有客廳,顯得有些擁擠。
全系統的體制改革工作會議,選在這座風景秀麗的南方城市召開。賓館是五十年代的建築,占的地盤很大,圈了半面山坡,除了進門處正中間的主樓,還有許多俄式風格的獨棟別墅,散落在濃陰密林之中,成了這家賓館獨具的特色。
袁潤生隨會議代表住在賓館主樓,和攝影記者大班住一屋,是個標準間,面積和這間房子差不多,可感覺比這裡寬鬆多了。
袁潤生欠著身子坐在沙發上,渾身不自在,好像沙發上長了刺,怎么坐都不舒服。他又不敢亂動,只能拿著一個架式坐在那裡。看看韓部長,韓部長還是剛才那樣斜靠在床頭上,臉上笑眯眯地朝這邊看著。
袁潤生的目光不敢在韓部長身上久留,連忙收回來,看著自己的腳底下。一會兒又忍不住抬頭看看蘇司長。蘇司長一手捏著那疊稿紙,一手拿著一支筆,正很認真地看著,兩隻圓潤光潔的長腿從裙子裡露出來,輕鬆優雅地交疊在一起,白得刺眼。
袁潤生心裡一盪,目光像觸了電似的,趕快閃開。他覺得這間屋裡的場景,不像是部長與下屬商量工作,倒像是旅途中和睦、默契的一對夫妻。心裡一陣後悔,怪自己不該這么不知深淺,冒冒失失地撞到這裡面來。
袁潤生剛來這家報社不久,眼前兩位領導,還是前一天在飛機上才頭一次見到。
當時,乘客們都已經放好自己的行李,在各自的座位上坐好,機艙的後門已經關閉,可機艙前門口的空姐們仍整整齊齊地站著,似乎在等什麼人。袁潤生聽見後排有人議論:“還不走,等誰呢?”另一個人道:“肯定是哪個大官搭這個航班。”不大會兒,果然見一男一女走進來,空姐們一起彎腰鞠躬道:“首長好!”男的是個高大威猛的老者,挺胸凸肚,目不斜視,對兩旁空姐的問候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徑直往前走。緊跟在他身後的女人個頭也不矮,卻不顯得高大,剪一個齊耳短髮,身著一身職業裙裝,裙下兩條腿又直又長,顯得體型裊娜,步履輕盈,乾淨利落。當她向空姐們微笑著致意時,袁潤生看見一道讓人眩目的光線從女人臉上射出來,心裡不由得讚嘆:“這女人真他媽的漂亮!”
身旁的攝影記者大班小聲告訴袁潤生:“這就是韓部長。”
袁潤生卻對那女人感興趣,問:“韓部長夫人挺有風度。”
“噓,別亂說,那是蘇司長。”
“蘇司長?”
就從那一刻,袁潤生的直覺告訴他,這倆人的關係不一般。現在這個場面更證實了他的那個印象,豈止不一般,看來他們的關係不是一天兩天了,而且在系統里幾乎到了不避人的地步。想到這裡,袁潤生坦然了許多:自己先在電話里約過了,既然他們大大方方地不在乎什麼,你瞎緊張什麼?心情一放鬆,臉色就自然了許多,也有了坐在沙發上的感覺,索性靠里挪動了一下屁股,讓自己坐得舒服些。
“我看行,稿子寫得不錯。”
蘇司長的話,打斷了袁潤生的遐想,他連忙把思緒拉回來。
蘇司長轉過臉去,一臉平靜地問韓部長:“你看看吧?”
韓部長輕輕擺著手:“不用了,你看了就行了。”
蘇司長上下打量了一番袁潤生,笑吟吟地問:“這社論,也是你寫的?”
“嗯,是傳到北京改過的。”
“小袁筆頭子挺快呀!”
蘇司長誇了袁潤生一句,又轉頭對韓部長說:“我們司里,就缺這么一個能寫的。”
韓部長呵呵一笑,道:“那還不容易,回去給朱聰說說,把這小伙子調給你不就行了。”
“我可不敢開這個口,臨來時,朱聰打電話給我,說,這次給你派去的,可是報社的首席記者。我要是向他要人,他還不跟我翻臉!”
一旁的袁潤生,聽韓蘇兩人這樣議論自己,尷尬萬分,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好不容易聽蘇司長說了一句:“我看就這么發吧。”袁潤生這才接過稿子,對蘇司長說:“剛才,家裡打電話催這個稿子的時候,報社領導讓我把明天報紙版面安排向部領導匯報一下,看部領導有什麼指示。”
蘇司長轉頭看看韓部長,說:“韓部長在這裡,你就給韓部長匯報吧。”
韓部長還是笑眯眯的樣子,往起坐了坐,說:“好,好。”
“明天報紙版面是這樣:頭版頭條,是蘇司長剛剛審過的這條開幕式訊息,同時配發會場全景照片,二條是這篇社論,再就是韓部長今天在開幕式上的講話,在一版的下部,用通欄標題,我們想配上韓部長的特寫照片全文刊登。”
袁潤生說完,見韓部長若有所思,沒有馬上回答,就轉頭看蘇司長的反應,蘇司長把頭轉向韓部長,袁潤生也就又跟著把頭轉過去。
韓部長斜靠在床頭上,眼望著天花板,半晌才說:
“嗯,講話可以全文刊登,但是,我建議你們拆開,分成幾個部分,提煉出重點,給每個部分加上個小標題,就像人民日報那樣。你們可以找找人民日報,看看人家是怎么處理江主席講話的。”
2
“我今天是專門來接你的,你這次打了個大勝仗,為報社立了功。”
朱聰發動汽車,給自己繫上了安全帶,邊轉頭對袁潤生說了一句話。
為期五天的全國廳局長會議一結束,袁潤生沒直接回北京,而是奉命跟著莊副部長一行在下面轉了一圈,向家裡發了一些莊副部長到某某地區調研、做了什麼指示的訊息,一個多星期後,才回到北京。
袁潤生沒想到朱社長會親自駕車送他回家。雖然袁潤生心裡明白,朱聰是來接莊副部長的,可是朱聰並沒有像別人那樣,前呼後擁地尾隨莊副部長的車隊而去,而是留下來,讓袁潤生上了他的車,然後自己親自駕車,送袁潤生回家,這讓袁潤生受寵若驚。
“哪裡,都是您指揮得好,我只不過是認真地完成了您的意圖而已。”
袁潤生雖然有些得意,但嘴上卻不敢居功自傲,趕緊把高帽子給朱聰送了過去。
“報社需要的就是你這種能不走樣地完成領導意圖的人。”袁潤生的這頂高帽子,讓朱聰戴得非常舒服,也就越發為自己有如此能幹的一個部下而自豪起來,“我沒看錯你!”
像這種全系統各省(市、區)廳局一把手參加的重要會議,一般來說,報社應當派出一個記者組,由報社領導帶隊,現場協調指揮完成。可是由於會議地址選在南方,為了節省交通費用,部里只給了報社兩個駐會記者名額。社領導掂量來掂量去,一個攝影記者是萬不可少的,不然部領導的光輝形象就沒法上報了,文字記者最後選定了袁潤生。
以前在別的報社,袁潤生完成過多次這樣大型的會議報導,並不是什麼難事,但辛苦是肯定的,尤其是最後會議成果的述評、側記,必須把代表們分組討論的意見全面反映出來,各個小組都得跑,還生怕把重要的意見給遺漏了。聽完討論,別人都可以休息了,袁潤生還得忙著匯總、梳理,再連夜寫成稿子,請有關領導審了,再傳給報社的領導審。
這幾天,袁潤生幾乎是24小時連軸轉。夜裡實在熬不住了,就放上滿滿一浴缸熱水,泡在裡面睡一小會兒,起來再乾。
雖然袁潤生自信自己天生就是乾記者這一行的材料,也曾得過省級國家級的不少新聞獎,但來這家報社不久,就獨自承擔了這么重要的任務,他還是不敢有絲毫的馬虎。
袁潤生知道,這對自己是一次難得的機會,他只能幹好,不能出絲毫的失誤。現在,他的付出終於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他從心裡感謝朱聰,感謝報社給了他這個機會。
“奧迪”在機場高速路上平穩地行駛著,把路旁的綠化帶拉成了兩條逆向疾馳的綠色河流。朱聰一邊開著車,一邊和袁潤生聊著些會上的情況。
“會議代表對這次會議報導有什麼反應?”
袁潤生知道朱聰問這話的意思——他是問有關這次會議報導的報紙送到會上之後,代表們有何反應。
這家報社原來在外地,剛遷京不久,是第一次承擔這么重要的會議報導任務,第一次在各路諸侯面前直接亮相。為了充分顯示機關報的作用,讓全系統深刻認識到自己辦報的意義,開幕式的第二天上午,報社派了專人坐飛機送來了當天的報紙。報紙原來是四個版,臨時又增加了四個版,八個版全部是會議開幕式的內容,特別是那些照片,部長、副部長、各省市區廳局的一把手,都或大或小地以各種方式在報上露了臉。
那天是分組討論,帶著油墨特殊香味的報紙一發下去,人們的興趣就都到報紙上去了,都想看看自己在報紙上的模樣。
頭版上,韓部長頭部的大特寫氣宇軒昂,儼然一副領袖模樣。於是大家就討論起韓部長的臉相,說韓部長天庭鼓起來了,耳朵也垂下來了,濃濃的眉毛也挑起來了,這相貌,還得往上升。有的說,還是自己有張報紙好,你看,頭天的事,第二天就見了報,有訊息,有社論,有講話,有側記,還有花絮,方方面面都照顧到了,迅速、準確、全面、完整地放映了這次會議的實況和代表們的風貌,並且八個版都是會議報導,多有氣勢!對全系統是多么大的鼓舞,對下一步貫徹會議精神是多么大的促進,對增強全系統的凝聚力是多么大的力量,等等。反正是好評如潮,反響空前。
朱聰聽得非常興奮,不時哈哈大笑,說:“看來報社第一次亮相還是成功的。”
“應該說非常成功!這都是社長您的決策好,專門派人送來報紙。”
袁潤生不失時機地恭維了朱聰一句。
“有粉就得搽在臉上!”朱聰沒有掩飾自己的得意,說,“當時有人勸我,專門派人坐飛機送報紙,來回幾千塊錢,不合算,我就說,同志,要算政治帳!”
“是啊,這次給報社帶來的影響和形象,這都是無形資產,是花多少錢都買不來的。”袁潤生順著朱聰的興奮點使勁發揮。
“韓部長當天晚上就打電話給我,說報社這次配合得很好。”
“是嗎,部長評價這么高,真是難得!”
“蘇司長也很滿意,剛才在機場迎賓大廳,握著我的手不肯放,說了好幾聲謝謝,這也是從來沒有過的。”
朱聰此刻像打了勝仗的將軍,滿面春風,細細地回味著激戰中的每個細節。袁潤生也就知趣地不再說話,讓自己的領導盡情地享受此刻的陶醉。
朱聰忽然想起了什麼,用車載手機撥了個號碼,然後按下免提鍵:“我是朱聰,是許秘書吧,我找莊部長。”
一會兒莊副部長的聲音清晰地傳了過來:“朱聰啊,什麼事?”
朱聰道:“部長,剛才在機場人多,我沒說,晚上您有安排嗎?”
“呵呵,不用了,我想一個人休息一下。”
“嗯,也好。另外,那筆資金的事,您跟韓部長溝通了嗎?”
“會上我把你的想法跟韓部長說了,韓部長沒明確表態,我想,你可以在下邊先跟計財司嚴司長溝通一下,讓他把報社列進那個名單里去,這樣我就好給你說話了。”
朱聰滿臉感激的微笑,連連點頭道:“謝謝莊部長,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先和嚴司長溝通好。正想跟你匯報呢,我想請嚴司長吃個便飯,嚴司長這段時間工作很忙,一直沒約到,現在您回來了……”
“好吧,我來約他,剩下的工作你們來做。”
朱聰眉開眼笑:“好好,謝謝部長,他只要肯出來,事情就成了一半了。”
“老嚴歌唱得不錯。”
“謝謝部長提醒,你放心,我一定安排好。”
“喔,家裡這段怎么樣?”
“您是指……”
“康副部長那邊沒什麼新情況吧?”
“沒有新的動向。”
“喔,好吧,就這樣,我到機關了。”
“部長再見。”
關上電話,朱聰突然轉了話題:“聽說韓部長沒在會上呆多久,蘇司長陪著他到下面轉了幾天?”
這話讓袁潤生有點措手不及。
“這……可能……好像是吧。”
袁潤生沒想到朱聰會問自己這個問題,更沒想到朱聰在北京,能把會上的事了解得這么清楚。那天晚上,去蘇司長房間送審稿子時看到的情景,立即在袁潤生眼前浮動起來。袁潤生明白,朱聰肯定會對那天晚上自己看到的情景感興趣,但話到嘴邊他還是使勁又咽了回去,支吾道:“我光忙著聽小組討論了,沒太注意。”
朱聰一邊開車,一邊扭頭意味深長地看了袁潤生一眼,問:“沒找個機會跟蘇司長聊聊?”
這回袁潤生反應得很快:“不知多少人等著跟蘇司長談工作呢,我哪能挨得上?”
說完,想了想,又補充了一句:“再說,您不是說了嗎,讓我好好工作,我個人的事領導會替我考慮。”
“你能這樣想,很好。”
說到這裡,話題斷了,車裡一時有些發悶。
袁潤生靈機一動,想到了不錯的一個話題。
“韓部長講話真有水平!”袁潤生先讚嘆一句。
“喔?”
見朱聰顯然在認真聽,袁潤生這才說下去。
“最後會議總結,莊副部長主持,韓部長作總結報告,大家都以為韓部長對回去如何貫徹會議精神,提一些要求。不料韓部長卻拋開了會議內容,結合他自己多年做領導工作的體會,著重講了如何當好一把手。部長說,關於回去如何貫徹落實,我不說你們也都知道該怎么做,莊副部長一會兒也會講。這次會議,來的都是一把手,我知道大家會議期間都想找我談談心,我也很想與各位好好聊聊,可是時間太短暫,我想,我們就用這種方式聊,談談心。聊什麼呢,我是一把手,你們也都是一把手,咱們就聊聊怎么當好這個一把手。
我個人體會,要當好這個一把手,應該注意以下三點:
第一,一把手要出主意,在大政方針、巨觀管理和長遠戰略問題上,不是看一把手幹了幾件實事,而是看你出了什麼大主意;
第二,一把手要會用幹部;
第三,一把手對看準的問題,要敢做敢為,善做善為。
韓部長真有水平,他講話的時候,會場很靜,大家連咳嗽都使勁壓著,只聽得刷刷地記筆記的聲音,就像蠶吃桑葉一樣。社長,這些年,我報導過的會議也不少,但我從沒看見過這樣的會議場面,我真服了。講到用幹部,部長說了兩句順口溜,是從社會上流傳的順口溜變過來的,很有意味。”
“噢,是什麼順口溜?”
“前段時間,社會上不是流傳這么兩句話嗎,‘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韓部長來了個反其意而用之,稍加改動,用來說明他的用人理念,韓部長說,我用幹部,兩句話:行就是行,說不行也行;不行就是不行,說行也不行。”
其實袁潤生當時聽到的順口溜還有兩句,是韓部長說完這兩句之後,坐在袁潤生後面的兩個人私下議論說的。
一個人說:“哼,剛愎自用,蠻橫霸道!”
另一個說:“我看他這兩句開頭和結尾應各加兩個字,叫做‘我說行就是行,誰說不行也行;我說不行就是不行,誰說行也不行。’”
但是袁潤生沒說,他知道朱聰不喜歡聽。
兩人就此話題,大大讚揚了一番韓部長,把韓部長說得好像在現在的位置上還有點屈才,應該進入政治局或聯合國。
朱聰把袁潤生送到住的小區門口,臨告別時說:“潤生,你來報社時間雖然不長,表現很好,特別是通過這次全國廳局長會議的採訪報導,充分展示了你對重大事件的獨立採訪能力,特別是那篇社論,寫得很有力度,我很滿意。這次出差回來,你工作可能會有些變動,老桂會專門找你談,為了加強報紙的言論,報社要組建評論部,我想讓你去負責,你自己有什麼意見?”
“謝謝社長對我的信任,”袁潤生想了想,說:“有句話,我不知該不該說?”
“說!你對我,有什麼不能說的。”朱聰鼓勵道。
“方正則比我來得早,他的綜合能力也比我強,再說,我來這裡,還是他介紹的,組建評論部的任務,是不是讓他……”
“哈哈,潤生,你多慮了,小方的工作也有變動,總編室孟主任要回去探家,這幾天就走,我和老桂商量了一下,讓小方去總編室,把那一攤子先頂起來。”
袁潤生這才放下心,想了想,說:“謝謝社長的信任!有句話,‘進個好單位不如跟上個好領導’,我來這兒,就是奔您來的,您要是覺得我還行,今後我就跟著您幹了!”
“好!好!我要的就是你這句話。”
朱聰使勁拍了一下袁潤生的肩膀。
等袁潤生下了車,朱聰沒有馬上開車離開,他打開手機,撥了一組號碼,等電話接通,說道:“我是朱聰,莊部長回來了,看來那件事還是得找嚴司長,莊部長答應由他出面把嚴司長約出來,對對,你現在就給六藝度假村打電話,讓那邊做好準備。另外,你找一下孟春,他不是跟一些女歌手和女影星熟悉嗎,讓他想辦法找幾個來,出場費該給就給,不要怕花錢,捨不得孩子套不到狼,明白嗎?不過也不一定有多大名氣,演過電影就行,名氣太大了,咱也請不起。讓孟春去談,叫對方開個價。”
停了停,又囑咐道:“這件事,只你知道就行了,我誰都沒說,包括邵豐祿。嗯,對孟春也不要露實底,只叫他找人就行了。”
3
袁潤生進了屋,包還沒放下,屋裡電話就響了,是朱可可,袁潤生驚奇地問:“可可,怎么這么巧?我剛剛進了屋。”
朱可可在電話里格格笑著說:“我有望遠鏡,你的一舉一動都在我的視線里。”
袁潤生歪頭把聽筒夾在脖子裡,一邊從包里往外收拾隨身帶的衣物,一邊和朱可可逗樂:“那我以後可要小心了,別讓你抓住什麼把柄。”
朱可可說:“心虛了吧,快坦白,這次出去,你都乾什麼壞事了?”
袁潤生說:“我一個人跑這個會,都快累死了,哪有時間和精力幹壞事。”
朱可可說:“哈哈,終於露出狐狸尾巴了,這就是說,如果你有精力,也有時間的話,就會去幹壞事。”
袁潤生大呼冤枉,道:“我心裡想的都是你,哪有空間裝下別人?”
朱可可不依不饒地說:“我知道你哄我,你心裡哪裡有我啊!。”
袁潤生說:“你怎么知道我心裡沒你?”
朱可可說:“怎么證明?”
“知道你喜歡集郵,給你買了本越南的集郵冊。”
“真的?我要,我現在就要。”
“呵呵,看你猴急的小樣,你過來拿吧,我請你吃晚飯,老地方。”
袁潤生早就策劃好了,準備回來就跟朱可可打電話,朱可可肯定會立即過來拿集郵冊,就可以藉機跟朱可可溫存一番,解決一下身體的饑渴。誰知道,沒等他打電話,朱可可自己就把電話打過來了。
放下朱可可的電話,袁潤生撥通了方正則。
“正則兄吧,我是潤生,對,我回來了,剛到家放下行李,就趕緊打電話向你報到,呵呵,當然應該了,你是我的引路人嗎,這份恩情我什麼時候也不會忘的!聽說你去總編室了,祝賀你!那可是個要害位置,離副總編只有一步之遙了,哈哈,我那是個閒差,哪能和你老兄相比?是啊,我盼著你有機會再‘恩’我一次呢。”
方正則在電話里告訴他,王國恩過幾天要來北京,打過電話來了,要方正則代他向袁潤生問好。
王國恩也曾經是某個縣委宣傳部的新聞幹事,但他很早就改行了,去他所在的那個縣的經委當了辦公室主任。這兩年不知是借了哪路的神力,在仕途上蹭蹭地往上竄,目前已經是一個地級市的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了。
袁潤生說:“好幾年沒見他了,到時候咱倆一起做個小東吧。”
方正則說:“他問我認不認識中組部的人,我哪認識什麼中組部的人呀,我對他說,我連中組部的大門在哪裡都不知道,他讓我轉告你,問你認不認識,或者朋友中有沒有認識的,。”
袁潤生問:“他說什麼事了嗎?”
方正則有些不屑,笑道:“還不是官迷心竅,竟然想著到中央機關來乾一段時間,說他在基層乾到副處級了,缺的就是在國家領導機關工作過的經歷,說下面現在競爭非常激烈,他不想和那些人在一條起跑線上競爭。潤生,你說現在人怎么都這樣了,對自己的欲望毫不掩飾。”
袁潤生說:“管他呢,等他來了,我倆一起做個小東吧。”
掛了電話,袁潤生拿了毛巾和替換的內衣,端著臉盆,到公共浴室洗澡。
袁潤生住的是一家招待所的一間地下室,北京有很多這種利用地下室改造的招待所。本來他可以住到報社去,跟大家去擠一擠,但是他沒有。他不想和那撥人把距離弄得太近。距離近了就沒有神秘感了,也就沒了應有的敬畏。他知道自己終究和那些人不是一類人。
袁潤生是個注重生活的人,雖然只是一間地下室,也被他收拾得很整潔,一張單人床、一隻小沙發、一隻書櫥、一張書桌、一隻椅子、一個簡易衣櫥,都是他從舊貨市場上淘回來的,價格低廉,卻很實用,而且讓他一搭配,還很像那么回事。書櫥里擠滿了書,色彩斑斕的書皮使這間屋子裡顯得內容豐富,書桌上桔黃色的檯燈,也給這間陰暗潮濕的屋子帶來了一些陽光的感覺。
洗了澡,換了一身休閒裝,袁潤生把換下來的那身給自己裝門面的西服拎在手裡,鑽出招待所,站到北京喧囂的地面上,停了片刻,讓自己的眼睛適應了刺眼的光線,然後來到小區裡的洗衣房,放下那身西服,朝小區門外走去。西裝必須是筆挺的,該化的錢就不能省。
5分鐘之後,袁潤生已經坐在了名叫“林間陽光”的茶餐廳里,和朱可可約會,他一般選在這裡。像朱可可這樣的女孩子,吃什麼倒是其次,反正不敢多吃,最講究的是情調和氛圍。這種茶餐廳都是套餐,每份30元到50元不等,雖然價格不菲,但上邊有封頂,不至於失去控制。袁潤生知道朱可可不會無緣無故地宰人,但是也不會替你考慮成本,去一般的餐廳,檔次低了她嫌髒亂差,去檔次高的,兩個人進去沒有幾百塊錢出不來,萬一她一高興點一份“龍蝦刺身”什麼的,他一個月的工資就沒有了。
朱可可來了,跳到他身邊,低頭在他的臉上啄了一下,然後坐在對面,大聲大氣地問:“今天請我吃什麼好吃的?”
袁潤生把桌上的選單推過去,道:“自己點,隨你。”
兩個人點了餐,邊聊邊吃,朱可可先問了會上的一些情況,袁潤生說了跟隨莊副部長下去沿途的一些見聞,再往後談到家裡時,基本上就是朱可可一個人在那裡獨唱了,袁潤生微微笑著,不時地“喔”一聲,表示在認真地聽。
聽了一會兒,袁潤生就把報社這一段的情況大致弄清楚了:
他和方正則升職的訊息,已經在報社傳得盡人皆知了,成了這幾天的熱門話題。據傳,老桂曾試圖阻止這件事,勸朱社長緩緩再說,但是沒能擋住。
大家分析,老桂可能要離開報社了,他也到了退休年齡。並且老桂已經在做離開的輿論準備了,閒聊天時說,自己年紀大了,不太適應北京的生活,老伴也不能來照顧他。
來自部機關的訊息說,為了應付中央清查各部門的小金庫,部里要把小金庫里的錢,分散存放到在京的一些直屬事業單位,對半分享利息,目前,十幾家事業單位都在全力爭取。
還有小道訊息說,下一步,報社的領導班子要正式組建了。於是大家猜測,除了朱聰當社長兼總編輯,馬家輝可能是副社長,孟春、方正則和袁潤生三人則是副總編輯的最有力人選。
報社這段時間最興奮的人是邵豐祿,因為方正則是他推薦給朱聰的,而方正則又帶進來袁潤生,並且方正則、袁潤生和馬家輝又是老朋友,邵豐祿當然希望看到這些人掌權。
等等。
“你要是當了副總編,可不許忘了我!”朱可可撅著小嘴撒嬌。
“怎么會,別說這事八字沒一撇,根本就是沒影的事,即便有那么一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讓我們可可做總編室主任。”
朱可可拍手笑道:“這話我可記住了,你不許食言!來,拉個鉤。”
朱可可伸出嫩蔥似的小手指頭,勾住袁潤生的手指頭,搖晃著:“拉鉤上吊,一百年不許變,誰變就是大壞蛋!”
和朱可可拉著鉤,袁潤生想,老桂會這么輕易地退出嗎?朱聰在車上給莊副部長打電話談到的那筆資金,也許就是部里小金庫里的資金,看來朱聰也在全力以赴爭取這筆資金;自己被大家看作是副總編輯的有力人選,固然說明自己這一段沒有白乾,但還是收斂些,免得招人妒忌……
袁潤生正這么想著,忽然聽到朱可可說:“哎,你給我買的集郵冊呢,快給我看看?”
袁潤生說:“在宿舍里呢,吃完飯跟我去拿。”
“為什麼不拿出來?”朱可可用手狠狠地點了一下袁潤生的額頭,說:“哼!我就知道你沒安好心,又想占我的便宜。上次喝了酒,我不清醒,這回我可不上你的當了!”
“嗨嗨!”袁潤生一臉壞笑,“別占了便宜賣乖,是誰喊著說的:哥哥,你真好!謝謝哥哥!”
朱可可的臉“騰”地紅了,連忙朝左右看看,低聲斥責道:“該死!這種話你也敢在這種場合說?”
見朱可可急赤白臉的樣子,袁潤生樂了,心想,你也有害羞害怕的時候啊,嘴裡說道“哈哈,在這裡說怎么啦,誰知道我們說什麼?”
倆人調著情,逗著嘴,心情愉快地吃完了飯,相跟著回到了袁潤生的住處。
袁潤生關好門,回身就把朱可可抱住了,沒頭沒臉地親起來。
朱可可被他弄得身上發癢,掙扎著叫道:“哎哎,你急什麼?先讓我看看那個集郵冊。”
創作背景
後記:寫作與尋找
亞子
我10多年沒動筆寫小說了,也基本沒發表小說,除了2001年在《中國作家》發的《五十年謀殺》,那是10多年前寫了半截撂下的一個中篇。這10多年我乾什麼去了?很簡單,兩個字:生存。想著先把生存的問題搞好,回過頭來再寫小說。結果10多年過去了,生存的問題還是沒搞好,小說也給耽誤了。回頭反思自己,生存問題沒搞好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大概是老忘不掉自己是一個作家,老是有另一雙眼睛盯著在現實生活中撲騰掙扎的自己,這使得自己在現實生活中一直不能全身投入,觀察思考者的我不停地干擾現實中的我,使現實中的我在關鍵時刻總是掉鏈子。而我恰恰又不是一個苦行僧,總是渴望得到和享受到現實生活中的那份溫情、親情和愛情,這又使得自己無法從現實中脫身出來,成為一個純粹的觀察思考者。
觀察的結果是我在現實生活中發現了兩類人:他們都清楚地知道光有良好的願望是無法使醜陋的現實有任何改變的。面對這樣的無奈,一種人選擇了撤退,從精神的防線上後撤,認可和遵循現實的運行規則,一舉由被動變為主動,成為在現實中遊刃有餘的人,成為強者和成功者;一種人不肯放棄,不肯承認現實的運行規則,堅持認為人類應該有一種理想的生活,有光明的存在。在這部小說中我就寫了這樣的兩個人,方正則和袁潤生,他們是性格、學識、教養都比較相近的兩個人,僅僅是由於對待生活的態度不同,結局卻截然相反。生活往往就是這么荒謬,我們從小所接受的一切教育,父母、老師、組織都想盡辦法使我們成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一個誠實的人,一個善良的人,可是這種人到了現實生活中卻總是處處碰壁,於是我們看到,面對殘酷的現實,這種好人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做好人,任憑被社會邊緣化被拋棄,或孤獨寂寞,或窮困潦倒;一是改變自己,使自己變壞,你變得壞一點也許就有房子住了,就升職了,就富貴了。在這部小說寫作之初,方正則和袁潤生這兩個人物我是平均用力的,可是寫著寫著,我意外地發現,方正則在小說中的分量逐漸減輕了,涉及到他的事情越來越少,逐漸被邊緣化了,最終袁潤生成了這個故事的主角。這大概就是生活的邏輯在起作用了。
每次抬頭看到頭頂浩渺的星空,就想到在以光年為基本計算單位的宇宙中,我們每個人100多厘米的身軀是多么微若浮塵,人類賴以存身的這個地球在宇宙中也只不過像是一個在顯微鏡下才能看到的細胞,人類身前身後是無邊的黑暗,即便窮盡人類的整個生命過程,也未必能走出這黑暗的籠罩。也許這個世界本來就是無意義的,是虛無的。為了擺脫這種恐慌,人類創造出了許多學說、各種宗教,把它們豎立在現實世界和黑暗世界之間,就像一道影壁,每個時代的人們都會把自己的理想、寄託投射在上面,建立起自己的價值體系,使人們在那裡看到生命和生活的意義,每當面臨時代交替,舊的價值體系面臨崩潰的時刻,人們總是要不懈地找尋和建立新的價值體系,人類的文明史正是在這樣的找尋和建立中得以形成,人類社會也正是這樣得以延續。
小說的寫作也許就是找尋和建立方式之一。
2004年10月24日星期日
(此文連同縮寫稿一起在2004年第6期當代長篇小說選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