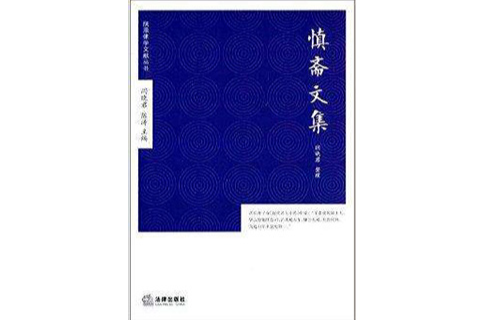本書主要內容是王步瀛所編訂的趙舒翹《慎齋文集》、《慎齋別集》及《慎齋年譜》,此次整理又附錄了趙舒翹《溫處鹽務紀要》及《清史稿》、《清史列傳》、《續修陝西通志稿》、《長安鹹寧兩縣誌》的趙舒翹本傳。
基本介紹
- 書名:陝派律學文獻叢書:慎齋文集
-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 頁數:393頁
- 開本:16
- 品牌:中國法律出版社
- 作者:閆曉君
- 出版日期:2014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1858795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陝派律學文獻叢書:慎齋文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圖書目錄
慎齋文集 〇〇一
慎齋別集 二五一
溫處鹽務紀要 三二三
附錄一 慎齋年譜 三五七
附錄二 《清史稿·趙舒翹傳》 三八一
附錄三 《清史列傳·趙舒翹傳》 三八五
附錄四 《續修陝西通志稿·趙舒翹傳》 三九一
附錄五 《長安鹹寧兩縣誌·趙舒翹傳》 三九五
慎齋別集 二五一
溫處鹽務紀要 三二三
附錄一 慎齋年譜 三五七
附錄二 《清史稿·趙舒翹傳》 三八一
附錄三 《清史列傳·趙舒翹傳》 三八五
附錄四 《續修陝西通志稿·趙舒翹傳》 三九一
附錄五 《長安鹹寧兩縣誌·趙舒翹傳》 三九五
序言
關於“陝派律學”
(代序)
閆曉君 陳 濤
吳建璠曾說,自“撥亂反正”以來,我們的法制史研究取得的成績不小,但也要看到,不足之處還很多。愛因斯坦以在木板上鑽窟窿來比喻搞科研,說人們喜歡在薄的一頭鑽許許多多窟窿,就是不敢碰厚的地方。他說的是自然科學,其實社會科學也一樣。請看法制史領域裡不也存在這種現象嗎?比較容易的題目,你寫,我寫,大家寫,可以寫上幾十上百篇論文;而難度比較大的問題無人問津,連一篇文章也沒有。大約十五年前,在一次法史界同人的聚會中,有人提出一個問題,沈家本在一篇文章中說,光緒初年律學家分豫、陝兩派,豫派以陳雅儂、田雨田為代表,陝派以薛允升、趙舒翹、張成勛為代表。他問,兩派除沈氏指明的律學家外還有哪些人,各有哪些代表作,兩派的分野何在,對清代法律發展有何影響。大家相顧茫然,答不上來,一致認為這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然而,十五年過去了,我還未見有哪位學者就這個問題提出過一篇論文。
吳建璠:“我的研究之路”,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吳建璠先生的這段話發人深省,迄今為止,有關“陝派律學”的研究仍未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陝派律學”的提出
在晚清同光之際,刑部作為當時“天下之刑名總匯”,由於司法審判等實際工作的需要,聚集了一批精通律例的法律人才,並逐漸在其內部形成了兩個律學學派,即“陝派律學”和“豫派律學”,這兩個律學學派分別以陝西、河南兩地研究律例之學的人為主,他們都在傳統的律例之學上卓然有成,且各具學術特點。“豫派律學”以“簡練”為主要特點,但光緒末年,豫派漸衰。陝派以“精核”為主,對傳統律學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成就,學術成就斐然,學術著作流傳於世,受到當時及後來學者的稱譽。
“陝派律學”和“豫派律學”的說法,首先是由沈家本提出來的。他在《大清律例講義》序中說:
“獨是《律例》為專門之學,人多憚其難,故雖著講讀之律,而世之從事斯學者實鮮。官西曹者,職守所關,尚多相與討論。當光緒之初,有豫、陝兩派,豫人以陳雅儂、田雨田為最著,陝則長安薛大司寇為一大家。余若故尚書趙公及張麟閣總廳丞,於《律例》一書,固皆讀之講之而會通之。余嘗周旋其間,自視弗如也。近年則豫派漸衰矣,陝則承其鄉先達之流風遺韻,猶多精此學者。韓城吉石生郎中同鈞,於《大清律例》一書,講之有素,考訂乎沿革,推闡於義例,其同異輕重之繁而難紀者,又嘗參稽而明辨之,博綜而審定之,余心折之久矣。”
(清)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4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232頁。
還有一位提到“陝派律學”和“豫派律學”的是董康,他在《清秋審條例》中講:“凡隸秋曹者爭自磨礪,且視為專門絕學。同光之際,分為陝、豫兩派,人才尤盛。如薛允升雲階、沈家本子惇、英瑞風岡皆一時已佼佼者。”
何勤華編:《董康法學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0頁。董康還在《我國法律教育之歷史譚》一文中指出了“陝派律學”和“豫派律學”形成的原因。他說,清代學校之科目“一以經義及策論為主,並缺律令一課,固無足稱為法律教育”。但在刑部,其官員大多為進士或拔貢出身,在簽分到部後,由於職責所在,這些官員“一方讀律,一方治事。部中向分陝豫兩系,豫主簡練,陝主精核。”
何勤華編:《董康法學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37頁。
沈家本、董康二人都曾長期在晚清的刑部供職,對於其中的情形稔熟,對秋曹掌故了如指掌,那么,晚清刑部分陝豫兩派的說法必確信無疑。
二、“陝派律學”之形成
“陝派律學”形成於同光時期,與薛允升密不可分。
自有清以來,陝籍人士任職刑部且有聲望和影響者,代不乏人。山陰吳懷清為鎮安晏安瀾作《家傳》云:“吾秦當近代京朝官著才望者以秋曹為最,論者多謂有秘授。”
參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整理:《近代人物年譜輯刊》(第4冊),《晏海澄先生年譜》,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版。
吉同鈞曾在《薛趙二大司寇合傳》中指出:
“秦人鐘西嶽秋肅之氣,性情多剛強嚴威,故出仕之後,其立功多在刑曹。前清入關之初,第一任刑部尚書則為寶雞黨崇雅,詰奸刑暴,頗立功業。然以明臣而仕清,入於《二臣》之傳,識者鄙之。康、雍之間,韓城張廷樞作大司寇,崇正除邪,發奸
伏,權幸為之斂跡,天下想望丰采,然太剛則折,卒罹破家亡身之禍。後雖昭雪,追諡文端,然律以明哲保身之道,未免過於戇直也。”乾隆朝又有王土棻,嘉慶朝有王灃中,道光朝有王鼎。
關於黨崇雅的生平事跡見於《清史稿》、《清史列傳》、《續修陝西通志稿》和清人的筆記中。
但“陝派律學”的形成卻在同光時期,而且與薛允升這個人有著莫大的關係。換句話說,沒有薛允升,就不可能有“陝派律學”。薛允升是“陝派律學”的創始人。作為“陝派”創始人,薛允升具備三個條件:(1)本人有不凡的律學成就和學術造詣;(2)其學術成就和人格魅力產生了巨大影響;(3)受其影響律學家以“陝籍”人士為主。
自1856年考中進士就分在刑部,從此他的一生就和法律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且他本人似乎對法律有著天然的興趣。吉同鈞在《薛趙二大司寇合傳》中說:
“允升字雲階,鹹豐丙辰科進士,以主事分刑部,念刑法關係人命,精研法律,自清律而上,凡漢唐宋元明律書,無不博覽貫通,故斷獄平允,各上憲倚如左右手,謂刑部不可一日無此人。不數年,升郎中,外放江西饒州知府,七年五遷,由知府升至漕運總督,以刑部需才,內調刑部侍郎,當時歷任刑尚者,如張之萬、潘祖蔭、剛毅、孫毓汶等,名位聲望加於一時,然皆推重薛侍郎。凡各司呈劃稿件或請派差,先讓薛堂主持先劃,俗謂之開堂。如薛堂末劃稿,諸公不肯先署,固由諸公虛心讓賢,而雲階之法律精通,動[令]人佩服,亦可見矣。後升尚書,凡外省巨案疑獄不能決者,或派雲階往鞫,或提京審訊。先後平反冤獄,不可枚舉。”
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說:“其律學之精,殆集古今之大成,秦漢至今,一人而已。”
如果說薛允升僅僅是自己對法律產生極大的興趣,那么,在清代的歷史上,最多再出現一位偉大的律學家。但薛允升偏偏是這樣一個人,他不但對法律有著超乎尋常的理解,而且非常重視“鄉誼”,對刑部中初來乍到者往往給予不憚其煩的指導和幫助,尤其是新分部的陝西鄉黨。他性格上的這個特點使得刑部內逐漸形成了一個以陝西人為主的學術團體,即“陝派律學”。當然,重視“鄉誼”也成了他被人譏諷的把柄。《近代名人小傳》就這樣說:
薛允升“長身瘦削而意氣勤懇,有關中故家之風,掌秋曹日,所屬多以律書求解,輒為解導,不憚煩也。然俗學無識,立朝未嘗有建白,復私鄉誼,卒被彈去。”
《續修陝西通志稿》謂薛允升“尤好誘掖後進,成就頗多,如趙舒翹、沈家本、黨蒙、吉同鈞輩,乃門生故吏中之傑出者,其它不可枚舉”。
俗話說,獨木不成林。在刑部,在薛允升的周圍,還有很多以陝籍人士為主的律學家。吉同鈞在《薛趙二大司寇合傳》說:“陝派律學”繼起者為趙舒翹。
趙舒翹“同治聯捷成進士,以主事分刑部,潛心法律,博通古今,《大清律例》全部口能背誦,凡遇大小案無不迎刃而解。十年升郎中,任提牢、秋審處坐辦、律例館提調。蓋律例館為刑部至高機關,雖堂官亦待如幕友,不以屬員相視。展如任提牢時,適遇河南王樹汶呼冤一案,時雲階為尚書,主持平反以總其成,其累次承審及訊囚、取供、定罪,皆展如一手辦理。案結後所存爰書奏稿不下數十件,各處傳播奉為司法圭臬。”
“陝派律學”的出現,在當時的刑部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當時人們就有各種解釋。曹允源在《慎齋文集》序中說:
“國家政事分掌於六曹,而秋官一職關人生命,視它曹尤重。為之長者類多擢自曹司重望,諳習法令。即敘勞外簡,往往不數年驟躋右職,入掌部綱。故它部長官遷調不常,而秋官任獨久,蓋非精研其學者不能盡職也。陝西人士講求刑法若有神解夙悟。自康熙間韓城張文端公為刑部尚書,天下想望風采。厥後釋褐刑部者,多本所心得以著績效,如為學之有專家,如漢儒之有師法。同治間,長安有薛公雲階,聲望與文端埒。越十數年,光緒中葉,趙公展如繼薛公而起,由刑部郎中出典大郡,洊膺疆寄,內召為侍郎,旋擢尚書,決疑平法有張釋之、於定國之風。薛公平反冤獄,嘖嘖人口,視刑律為身心性命之學,嘗以律例分類編訂,手錄積百數十冊,又著《漢律輯存》、《唐明律合刻》、《讀律存疑》等書。公亦采古人有關刑政嘉言懿行,成《象刑錄》。任提牢廳時,輯《提牢備考》,皆足為後世法。然薛公在刑部先後垂四十年,年逾八秩,雖間關行在,卒以壽終。而公則以尚書兼軍機大臣,值拳匪構亂,為外人所持,竟不得其死。其學同,其名位同,乃其所遭懸絕如此,得不謂之命也邪。”
刑部作為天下之刑名總匯,關乎人的生殺大事。在某種程度上,刑部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部門,在刑部任職者必須是專業技術人員,這在客觀上為律學的繁榮提供了前提條件。但說“陝西人士講求刑法若有神解夙悟”,這僅僅只是一種溢美之辭。當時的清政府中央有六部,在刑部當差被視為最苦的差事,而陝西僻處西北邊陲,地瘠民貧,因此陝籍人士在通籍後往往能吃苦耐勞,更加勵志。如《舊京瑣記》云:
“刑曹於六部中最為清苦,然例案山積,動關人命,朝廷亦重視之。故六堂官中,例必有一熟手主稿,余各堂但畫黑稿耳。薛尚書允升既卒,蘇撫趙舒翹內用繼之。趙誅,直臬沈家本內調為侍郎,皆秋審舊人。凡稿須經沈畫方定。余在刑曹時,見滿左右堂既不常到,到則各司捧稿,送畫輒須立一二小時,故視為畏途,而愈不敢至。其庸沓可笑,然尚虛心,蓋每畫必視主稿一堂畫畢否,既畫則放筆書行。若間見有未畫者,則曰‘先送某堂,看後再送’雲。”
其他文獻亦有類似說法,如《國乘備聞》:“部務之不振也,曹郎積資十餘年,甫諳部章,京察保一等,即簡放道府以去。侍郎多起家翰林,初膺部務,臨事漫不訾省,司員擬稿進,涉筆占位署名,時人謂之‘畫黑稿’。尚書稍諳練,或一人兼數差,年又耄老,且視六部繁簡次序,以調任為升遷(舊例由工調兵、刑,轉禮,轉戶,至吏部,則侍郎可升總憲,尚書可升協辦),勢不得不委權司曹。司曹好逸惡勞,委之胥吏,遂子孫窟穴其中,倒持之漸,有自來矣。唯刑部法律精,例案山積,舉筆一誤,關係人生死。歷朝重獄恤刑,必簡一曾任刑曹、熟秋審者為尚、侍。薛允升薨,江蘇巡撫趙舒翹內用為尚書。舒翹誅,直隸臬司沈家本內用為侍郎,皆刑部秋審處舊僚也。薛、趙、沈之治刑部也,薛主嚴,趙、沈主寬。”
同光時期在刑部形成了以薛允升為中心,以陝籍人士為主的“陝派律學”,其人員有雷榜榮、吉同鈞、黨蒙、張成勛、段燮、蕭之葆、武瀛、段維、高祖培等。當然,“陝派律學”不純粹都是由陝籍人士組成,如從學術關係上看,沈家本的學術成就與“陝派律學”在某種程度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學術淵源上講,沈家本當屬於“陝派律學”。
甚至有些學者認為,“正式的經歷及非正式的贊助是仕途當中最明顯的部分,但是加入一個律學博士學會也是相當重要的,這類學會同時具有學派以及地方派系的特色。當沈家本被允許加入當時主控刑部的兩個學派之一陝派(陝西)之後(另一個是豫派),他自1875年起就開始攀升。”儘管沈家本祖籍非陝西,他與民國時期主持法務部、大理院的著名法律人物許世英、董康等皆為“陝派律學”的門生。參見鞏濤(Jérme BOURGON):“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林惠娥譯,載《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法國漢學》(第8輯),中華書局2003年版。徐忠明也在“中國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超越西方,回歸本土?”一文中“順便指出,雖然沈家本是浙江歸安人氏,但是他的律學研究屬於陝派範圍”。參見徐忠明著:《案例、故事與明清時期的司法文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頁。
三、“陝派律學”的衰落
庚辛(1902年)之後,“陝派律學”漸趨衰落。
辛丑年(1901年),趙舒翹、薛允升先後死去。吉同鈞、張成勛、蕭之葆在清亡後亦陸續辭官。
吉同鈞《送蕭小梅郎中歸田序》:“小梅仕秋曹十餘年,以廉隅氣節期許,不屑於法律,而法律知識自非同列所及,事長官羞作婀態,亦非故以崖岸自高,太史公所謂‘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者,殆兼有之。當民國建設之初,眾人戀戀官職,首鼠兩端,甚者多方奔求,惟患失之。小梅獨決然捨去,如棄敝屣,寧終老於鄉閭,而不貪非分之爵祿;寧力農以食苦,而不作伴食員,誠士大夫中之鴻鵠、驊騮也。世俗不察,或目為迂腐不識時勢,或嗤為矯激不近人情,是亦燕雀不知天地之高,駑駘不知宇宙之大也,何足怪哉?”
四、“陝派律學”的學術成就
薛允升是清末著名的法學家,是沈家本一生都極為敬重的前輩和老師,其學術成就尤為沈家本所推崇。沈氏在為薛允升的名著《讀例存疑》作序時寫道:“國朝之講求律學者,惟乾隆間海豐吳紫峰中丞壇《通考》一書,於例文之增刪修改,甄核精詳。其書迄於乾隆四十四年。自是以後,未有留心斯事者。長安薛雲階大司寇,自官西曹,即研精律學,於歷代之沿革,窮源竟委,觀其會通,凡今律、今例之可疑者,逐條為之考論,其彼此抵捂及先後歧異者,言之尤詳,積成巨冊百餘。家本嘗與編纂之役,爬羅剔抉,參訂再三。司寇復以卷帙繁重,手自芟削,勒成定本,編為《漢律輯存》、《唐明律合編》、《讀例存疑》、《服製備考》各若干卷,洵律學之大成而讀律者之圭臬也。”
(清)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4冊),《寄簃文存》卷六,鄧經元、駢宇騫點校,中華書局1985年版。
沈家本在《薛大司寇遺稿序》中說:“大司寇長安薛公,自釋褐即為理官,講求法家之學,生平精力,畢瘁此事。所著有《唐明律合編》、《服製備考》、《讀例存疑》、《漢律輯存》諸書。”
(清)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4冊),《寄簃文存》卷六,鄧經元、駢宇騫點校,中華書局1985年版。
薛允升的律學研究成就對後來的清末法律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曾參預修訂《大清現行刑律》的董康說:“《現行刑律》大致采長安薛允升《讀律(例)存疑》之說。”
董康:《中國修訂法律的經過》。沈家本在《故殺胞弟二命現行例部院解釋不同說》中指出:“原任刑部尚書薛允升,近世號稱專精刑律者,其所著《讀例存疑》一書,於此條頗有微詞。大致謂,爭奪財產、官職謀殺弟侄分別年歲問擬斬絞辦理,尚無歧誤。至‘讎隙不睦’一層,是否專指胞弟及胞侄之年未及歲者而言,礙難懸擬。蓋非素有嫌隙,決不致蓄謀致死。……上年法律館修改現行刑律,於《讀例存疑》之說,採取獨多。”
(清)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4冊),《寄簃文存》卷三,鄧經元、駢宇騫點校,中華書局1985年版。華友根通過詳細地研究,認為《讀例存疑》為中國近代修訂新律的先導。
華友根:《薛允升的古律研究與改革——中國近代修訂新律的先導》,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薛趙二大司寇合傳》:
“至於著書共分四種:嘗謂刑法雖起於李悝,至漢始完全,大儒鄭康成為之注釋。乾嘉以來,俗儒多講漢學,不知漢律為漢學中一大部分,讀律而不通漢律,是數典而忘祖,因著《漢律輯存》;又謂漢律經六朝北魏改革失真,主唐兩次修正,始復其舊,明律雖本於唐,其中多參用金遼酷刑,又經明太祖修改,已非唐律真面目,因糾其繆戾,著《唐明律合編》;又刑律所以補助禮教之窮。禮為刑之本,而服制尤為禮之綱目,未有服制不明而用刑能允當者。當時歐風東扇,逆料後來新學變法,必將舍禮教而定刑法,故預著《服製備考》一書以備後世修復禮教之根據,庶國粹不終於湮歿矣。”
薛允升逝世後,沈家本奏請清廷,刊刻其名著《讀例存疑》,並對《讀例存疑》予以高度評價:
《薛趙二大司寇合傳》:
趙舒翹任提牢時,適遇河南王樹汶呼冤一案,時雲階為尚書,主持平反以總其成,其累次承審及訊囚、取供、定罪,皆展如一手辦理。案結後所存爰書奏稿不下數十件,各處傳播奉為司法圭臬。主要著作如下:
1.《提牢備考》,曹允源在《慎齋遺集序》中說:“公采古人有關刑政嘉言懿行,成《象刑錄》。任提牢廳時輯《提牢備考》,皆足為後世法。”《慎齋別集》卷一中載有《提牢備考序》:“光緒乙酉五月長安趙舒翹識於宣武城南寓齋。”
2.《慎齋文集》,原名《映灃山房文集》十四卷,由眉縣王仙洲先生編訂。後改名《慎齋文集》十卷,長安沈幼如先生校字,民國十三年(1924年)酉山書局印刷。
3.《慎齋別集》四卷,由《映灃山房文集》十四卷分出。眉縣王仙洲先生編訂,長安沈幼如先生校字,民國十三年(1924年)酉山書局印刷。
4.《象刑錄》。《慎齋別集》卷一中載有《象刑錄序》。
5.《雪堂存稿》。
6.《豫案存稿》。
吉同鈞,字石笙(石生),陝西韓城人。在其所著的《審判要略》的跋中又有關於其生平的記述:“石笙先生本文章巨手。其治律也,直登其鄉先生薛雲階尚書之堂而胾其醢。西曹中久推老宿,比年名益隆,以法部正郎承政廳會辦兼光法律館總纂,並分主吾律學館及法律、法政兩學堂、大理院講司所四處講習,一時執弟子禮者千數百人。所著法律書稿綦富,而《大清律例講義》一種乃至風行半天下。”
清末,沈家本、伍廷芳主持變法修律,修訂《大清現行刑律》的五位總纂官中吉同鈞名列首位。沈家本、伍廷芳奏請專設法律學堂,開設的課程有《大清律例》,請吉同鈞主講。後來,將吉同鈞的講義編成《大清律例講義》一書,由當時的法部核定出版,沈家本欣然為之作序,弁諸卷首,此書在當時風行全國。在《大清律例講義序》中,沈家本對吉同鈞的學術成就予以高度評價,他說:“韓城吉石生郎中同鈞,於《大清律例》一書,講之有素,考訂乎沿革,推闡乎義例,其同異重輕之繁而難紀者,又嘗參稽而明辨之,博綜而審定之,余心折之久矣。”沈家本又說:“其於沿革之源流,義例之本末,同異之比較,重輕之等差,悉本其所學引伸而發明之,辭無弗達,義無弗宣,洵足啟法家之秘鑰而為初學者之津梁矣。”
《寄簃文存》。
五、“陝派”的司法審判
“陝派律學”的代表人物皆熟讀律例,有很高的從事司法審判的能力,這表現在他們對疑難重大刑獄的審判上。
薛允升執掌刑部數四十年,執法不阿,甚有政聲。薛允升一生審理了許多大案,其中太監李萇材一案,能夠秉公執法,堅決頂住來自慈禧及李蓮英等的壓力,將罪犯正法,顯示其剛正不阿之風骨,並以此被排擠。
“李萇材、張受山等愈無忌憚,竟敢於輦轂之下明目張胆糾眾打鬧娼遼[寮],行兇毆殺捕人。拿交部問,雲階時為尚書,以此案關係重大,若非嚴加懲辦,涓涓不滅將成江河,前朝劉魏之禍將復起矣,前後分三折大放厥詞,痛苦上陳,謂:‘皇上開一面之網,不妨量從末減。臣等為執法之吏,不敢稍為寬縱,且從犯或可稍輕,而首犯斷不容免死。’其意以為寧可違皇上之命、致一己獲咎戾,不能變祖宗之法令、國家受後患也。折上,皇上大為感動,寧可違慈命,而不敢違祖法,降旨依議,李萇材著即處斬,張受山斬監候,秋後處決。當時行刑,民間同聲稱快。”
薛允升對權貴剛正不阿,但也絕不冤枉任何一個人,“江寧案”即周五殺朱彪案,在他的主持下最終平反冤枉。
《清稗類鈔》“江寧三牌樓枉殺二命案”:
光緒辛巳(1881年),沈文肅公葆楨督兩江,江寧有三牌樓(在儀鳳門內)命案,輕率定讞,枉殺無辜,世多冤之。時陳伯潛閣學寶琛方為翰林院侍講學士,以參將胡金傳承緝謀殺朱彪之命盜,妄拿教供,刑逼定案,業將曲學如、僧紹宗處決。雖已由繼任總督劉忠誠公坤一另獲兇犯周步畛、沈鮑洪供認殺彪,並訊出金傳嚇賄眼線教串各節,旋奉旨令忠誠嚴行刑訊,以成信讞,即疑竇孔多,猶待澈究,遂具疏以上聞。
此案真相,實為步畛挾仇起意殺彪,商同鮑洪潛攜篾刀遇彪,以糾邀行竊為名,至三牌樓竹園旁,將彪砍斃,三人同逃,固未移屍,嗣經地保報縣驗詳。文肅遂飭會辦營務處洪汝奎懸賞購線,並派金傳密訪。蓋金傳時為緝捕委員也,先後拿獲學如、紹宗及張克友三人,並賄教方小庚作證,金傳與間官候補縣嚴堃同訊,喝令用刑,威逼成招。初供殺死謝某,旋供為薛泳全,繼復稱為薛春芳。金傳輾轉誘令改供,汝奎於覆審後,以案情重大,稟請派員覆訊。文肅以為此乃會匪之自相殘殺也,即批飭將學如、紹宗正法。及辛巳拿獲竊犯李大鳳,供出步畛、鮑洪殺彪,與辦結前案地方時日相符。當將步畛、鮑洪訊供,不稍諱。
壬午(1882年),德宗以寶琛具疏上聞,遂派麟相國書、薛尚書允升前往查辦,時麟為刑部尚書,薛為刑部侍郎也。既至江寧,反覆推勘,步畛、鮑洪均各供認商同殺彪不諱,金傳亦以刑訊教供各情,據實供吐,小庚、克友等俱各脗合,於是步畛、金傳皆論斬,鮑洪論絞,汝奎、堃均革職,發往軍台效力贖罪,文肅以已薨免議。
徐珂:《清稗類鈔》(第3冊),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154頁。
清末,“不肖州縣玩視民命,多爾草率從事。該管上司不肯認真詳細推勘,非巧為彌縫,即多方掩飾。其能平反更正者,百無一二。而固執原擬者,則比比皆是。推原其故,總由各該督撫徇庇屬員,回護原審。其尤甚者,明知案情實有冤抑,即據實更正處分,亦輕以為與全省局面有礙,終不肯自認錯誤。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即如河南鎮平縣王樹汶呼冤一案,始而迭經御史參奏,該省仍敢飾詞入奏,入人死罪。繼而奉特旨提交臣部審辦,該前撫李鶴年猶復強詞,嘵嘵置辨,希圖搖惑眾聽,顛倒是非,在已發覺者平反尚如此其難,其餘未經發覺者更必任意消弭,安望其自行更正耶。”
“河南司議覆光祿寺少卿延茂失入案件寬免處方奏稿”,見《慎齋文集》卷三。而審理河南王樹汶臨刑呼冤一案的,正是“陝派律學”的第二號重要人物趙舒翹。
〇
《清稗類鈔》“王樹汶為頂兇案”:
王樹汶,鄧州人,幼以被掠為鎮平盜魁胡體安執爨役,體安,鎮平胥也。河南多盜,州縣故廣置胥役以捕盜,有多至數千人者,實則大盜即窟穴其中,時遣其徒黨出劫,捕之急,即賄買貧民為頂兇以銷案。體安尤凶猾,一日,使其徒劫某邑巨室,巨室廉知體安所為,乃上控。時塗制軍宗瀛方撫汴,檄所司名捕之。鎮平令捕體安急,則賄役,以樹汶偽為之,俾役執之去。樹汶初不承,役以非刑酷之,且謂即定案必不死,始諾。樹汶年十五,尫羸弱小,人固知其非真盜也。縣令馬翥聞體安就獲,狂喜,不暇審真偽,遽稟大府,草草定案。既定讞,當樹汶大辟,時體安已更姓名,充他已胥矣,樹汶未知也。刑之日,樹汶始知之,呼曰:“我鄧州王樹汶,非胡體安,若輩許我不死,今乃戮我乎!”監斬官白宗瀛,大駭,命停刑,下所司覆鞫,卒未得要領。樹汶自言父名季福,居鄧州,業農,乃檄鄧州牧朱杏簪刺史光第逮季福為驗,未至而宗瀛督兩湖去。繼任者為河督李鶴年。開歸陳許道任愷者,先守南陽,嘗讞是獄,又與鶴年有連,於是飛羽書,阻光第,令毋逮季福,且百端誘怵之。光第不為動,慨然曰:“民命至重,吾安能顧惜此官以陷無辜耶!”竟以季福上,則樹汶果其子,愷乃大戚,鶴年以袒愷故,持初讞益堅,豫人之官科道者,遂交章論是獄。
鶴年恚言路之持之急也,遂力反宗瀛前議,而益傅會律文,謂樹汶雖非體安,亦從盜,在律盜不分首從,皆立斬,原讞者無罪。然樹汶初止為體安司炊,亦有謂其為孌童者,而實非盜,讞者必欲坐以把風接贓之律,樹汶至是遂為正凶。而官吏之誤捕,體安之在逃,悉置不問。諫臣益大,劾鶴年庇愷,於是朝延有派河督梅啟照覆訊之命。河工諸僚佐,率鶴年故吏,不敢違鶴年恉,啟照亦不欲顯樹同異,竟以樹汶為從盜,當立斬。獄成,言者爭益力。
時潘文勤公方長秋官,廉知其概,提部研鞫,而趙舒翹方以郎中總辦秋審,因以是獄屬之。閱數月,乃得實,將上奏矣,而鶴年使故為文勤門生之某道員入都遊說,文勤入其說,遽中變。舒翹方力爭,文勤忽以父喪去官,南皮張文達公之萬繼其任,文勤亦知為某道員所賣,貽書文達,亟自引咎。疏上,奉旨釋樹汶歸,戍翥及知府馬承脩極邊,鶴年啟照及臬司以下並承審各官皆降革有差。
而光第已先以他事劾罷,則愷嗾鶴年為之也。有以持愷羽書直揭部科諷者,光第笑謝之,貧不能歸,竟卒於豫,年五十五。光第去官二十年,鄧人謀以其治狀上於朝,請祀名宦,以其子祖謀時官禮部侍郎,格於例,不果行。祖謀,字古微,以道德文章著稱於時,更名孝臧,學者稱漚尹先生者是也。
《清稗類鈔》(第3冊),第1133頁。
六、研究“陝派律學”的意義
“陝派律學”出現在中國法律古今交替的時候,其代表人物具有較高的傳統文化素養,出身科舉,且長期在刑部供職,具有豐富的司法實踐經驗和精湛的傳統律學知識,既有“理論”又有“經驗”。
但是,迄今為止,學術界對“陝派律學”還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進行系統的研究。因此,研究“陝派律學”有著重大的學術意義。幾年前,俞江在《傾聽保守者的聲音》一文中介紹了“陝派律學”一個代表人物吉同鈞及其學術成就,最後他對眼下的法學研究提出批評說:“沒有參照系,連經驗積累也不系統;沒有思想淵源,連方法論傳統也被丟棄,法律和法學在虛假繁榮里高歌猛進。”
俞江:“傾聽保守者的聲音”,載《讀書》2002年第4期。我們認為,研究“陝派律學”至少有以下學術價值:
首先,“陝派律學”對傳統法律做了一個完美的總結。其所取得的傳統律學成就無疑是相當高超的,代表著幾千年傳統律學的最高水平。“陝派律學”的奠基者薛允升對歷代刑法的淵源《漢律》有精深研究,著有《漢律輯存》、《漢律決事比》,其中的《漢律輯存》直接對沈家本的《漢律摭遺》產生了學術影響;薛允升還對《唐律》、《明律》進行了比較研究;其《讀例存疑》更是集中在長達幾十年的司法實踐和學術研究中對清代律例的獨到見解,被視為第一部“例學”著作。而趙舒翹的《提牢備考》則是反映古代監獄制度的珍稀資料。因此,研究“陝派律學”對於了解傳統法律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其次,“陝派律學”的代表人物在晚清已提出了一些法律改革的建議。雖然這些建議仍跳不出傳統法律文化的樊籬,但都是針對清代法律實施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實際問題而提出的,這些正是中國法律近代化的基礎。正如沈家本所說,“不深究夫中律之本原而考其得失,而遽以西法雜糅之,正如枘鑿之不相入”。例如,吉同鈞《上修律大臣酌除重法說帖》比沈家本著名的《刪除律例內重法折》還要早,薛允升、趙舒翹也都曾上過諸如此類建議改進法律制度的奏摺,研究這些資料無疑對了解清代法律存在的問題、清末法律改革的歷史背景以及清末修律的內容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再次,“陝派律學”中代表人物參與晚清的變法修律活動。例如,吉同鈞不但親自編纂《大清現行刑律》,而且在《大清新刑律》出台後,對修律的工作不斷地予以關注和評論,他曾對《大清新刑律》發表這樣的看法,“新訂之律,表面僅四百餘條,初閱似覺簡捷,而不知一條之中,實蘊含數條或數十條,將來判決成例,仍當取現行律之一千餘條,而一一分寄與各條之內,不過體裁名詞稍有不同耳”。
《律學館第四集課藝序》,見《樂素堂文集》。清末變法,力主“會通”中西法律,研究“陝派律學”可以了解到傳統法律與現代法律之間如何衝突,又如何進行調整並整合的,也可以了解傳統的法律人如何面對幾千年以來首次出現的法律大變局,這樣可以使我們能對中國法律的近代化會有進一步的認識,對今天的法律改革也能提供有益的借鑑。
又次,“陝派律學”的代表人物在長期的司法審判歷史中表現出了良好的司法官素質,他們一般都能夠嚴格執法,不畏權勢。例如,大司寇薛允升寧肯丟官,也要將太監李萇材等繩之以法。在司法審判中,一絲不苟,認真負責,“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例如,趙舒翹審理的河南王樹汶臨刑呼冤一案,最終水落石出,將庇護地方、草菅人命的河南巡撫等一乾官員參劾奪職。研究“陝派律學”中這些剛直不阿的代表人物,繼承和發揚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精華,無疑對構建我們今天的法治文明不無裨益。
最後,“陝派律學”除了薛允升、趙舒翹在清末去世以外,吉同均、張麟閣等一直生活到民國時期,他們的著作一般在民國時期都刊刻印行,但以後就默默無聞,似乎被人們遺忘了。我們今天研究“陝派律學”,除了回顧中國法律近百年走過的這段曲折歷史,汲取歷史的經驗與智慧,還可以重新評估陝西人對中國傳統法律的繼承和發展,對中國法律近代化所做的準備與貢獻,振奮我們的學術信心,使陝西乃至西北的法學研究和法律教育在今天取得更大的發展。
七、研究的難點
就目前掌握的資料看,除沈家本、董康二人之外,其他人提到“陝派律學”和“豫派律學”的似乎就沒有,因此,研究“陝派律學”首先遇到的難題是史料問題。關於史料的蒐集,特別是有關近代歷史人物史料的收集,有著其特殊性。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分論——《人的專史》第二章“人的專史的對相”中指出:
“研究近代的歷史人物,我們很感苦痛,本來應該多知道一點,而資料反而異常缺乏。我們應該盡我們的力量,蒐集資料,作一篇,算一篇。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經死去,蓋棺定論,應有好傳述其生平。……此時不作,將來更感困難。此時作,雖不免雜點偏見,然多少尚有真實資料可憑。此時不作,往後連這一點資料都沒有了。”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頁。
徐一士在《一士譚薈》中也講:
“史料為治史者所注重,近代史料為時未遠,關係尤切,更應特加之[注]意。從事收集保存,以供鏡覽,而資史家之要刪。乃往往徒知古昔史料之可貴,於近者則忽之。或知其足重矣,而以為得之可不甚廢力,未若古昔史料之難於發見,因之不肯亟亟訪求,孜孜輯錄,不知斯固有稍縱即逝者,久且放失淹沒,不易復睹。蓋史料緣是而沈冥不彰者甚夥,可喟也。……此種感覺,當不僅梁氏一人為然,其過要在從事蒐集之不早耳。”
徐一士:《一士譚薈》,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11頁。
徐一士熟悉近代掌故,長期從事近代歷史資料的蒐集整理與研究,他是有感而發。為了不使“陝派律學”的資料“放失淹沒”,為後人不易復睹,本書將對“陝派律學”的史料“亟亟訪求,孜孜輯錄”。
(代序)
閆曉君 陳 濤
吳建璠曾說,自“撥亂反正”以來,我們的法制史研究取得的成績不小,但也要看到,不足之處還很多。愛因斯坦以在木板上鑽窟窿來比喻搞科研,說人們喜歡在薄的一頭鑽許許多多窟窿,就是不敢碰厚的地方。他說的是自然科學,其實社會科學也一樣。請看法制史領域裡不也存在這種現象嗎?比較容易的題目,你寫,我寫,大家寫,可以寫上幾十上百篇論文;而難度比較大的問題無人問津,連一篇文章也沒有。大約十五年前,在一次法史界同人的聚會中,有人提出一個問題,沈家本在一篇文章中說,光緒初年律學家分豫、陝兩派,豫派以陳雅儂、田雨田為代表,陝派以薛允升、趙舒翹、張成勛為代表。他問,兩派除沈氏指明的律學家外還有哪些人,各有哪些代表作,兩派的分野何在,對清代法律發展有何影響。大家相顧茫然,答不上來,一致認為這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然而,十五年過去了,我還未見有哪位學者就這個問題提出過一篇論文。
吳建璠:“我的研究之路”,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吳建璠先生的這段話發人深省,迄今為止,有關“陝派律學”的研究仍未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陝派律學”的提出
在晚清同光之際,刑部作為當時“天下之刑名總匯”,由於司法審判等實際工作的需要,聚集了一批精通律例的法律人才,並逐漸在其內部形成了兩個律學學派,即“陝派律學”和“豫派律學”,這兩個律學學派分別以陝西、河南兩地研究律例之學的人為主,他們都在傳統的律例之學上卓然有成,且各具學術特點。“豫派律學”以“簡練”為主要特點,但光緒末年,豫派漸衰。陝派以“精核”為主,對傳統律學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成就,學術成就斐然,學術著作流傳於世,受到當時及後來學者的稱譽。
“陝派律學”和“豫派律學”的說法,首先是由沈家本提出來的。他在《大清律例講義》序中說:
“獨是《律例》為專門之學,人多憚其難,故雖著講讀之律,而世之從事斯學者實鮮。官西曹者,職守所關,尚多相與討論。當光緒之初,有豫、陝兩派,豫人以陳雅儂、田雨田為最著,陝則長安薛大司寇為一大家。余若故尚書趙公及張麟閣總廳丞,於《律例》一書,固皆讀之講之而會通之。余嘗周旋其間,自視弗如也。近年則豫派漸衰矣,陝則承其鄉先達之流風遺韻,猶多精此學者。韓城吉石生郎中同鈞,於《大清律例》一書,講之有素,考訂乎沿革,推闡於義例,其同異輕重之繁而難紀者,又嘗參稽而明辨之,博綜而審定之,余心折之久矣。”
(清)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4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232頁。
還有一位提到“陝派律學”和“豫派律學”的是董康,他在《清秋審條例》中講:“凡隸秋曹者爭自磨礪,且視為專門絕學。同光之際,分為陝、豫兩派,人才尤盛。如薛允升雲階、沈家本子惇、英瑞風岡皆一時已佼佼者。”
何勤華編:《董康法學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0頁。董康還在《我國法律教育之歷史譚》一文中指出了“陝派律學”和“豫派律學”形成的原因。他說,清代學校之科目“一以經義及策論為主,並缺律令一課,固無足稱為法律教育”。但在刑部,其官員大多為進士或拔貢出身,在簽分到部後,由於職責所在,這些官員“一方讀律,一方治事。部中向分陝豫兩系,豫主簡練,陝主精核。”
何勤華編:《董康法學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37頁。
沈家本、董康二人都曾長期在晚清的刑部供職,對於其中的情形稔熟,對秋曹掌故了如指掌,那么,晚清刑部分陝豫兩派的說法必確信無疑。
二、“陝派律學”之形成
“陝派律學”形成於同光時期,與薛允升密不可分。
自有清以來,陝籍人士任職刑部且有聲望和影響者,代不乏人。山陰吳懷清為鎮安晏安瀾作《家傳》云:“吾秦當近代京朝官著才望者以秋曹為最,論者多謂有秘授。”
參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整理:《近代人物年譜輯刊》(第4冊),《晏海澄先生年譜》,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版。
吉同鈞曾在《薛趙二大司寇合傳》中指出:
“秦人鐘西嶽秋肅之氣,性情多剛強嚴威,故出仕之後,其立功多在刑曹。前清入關之初,第一任刑部尚書則為寶雞黨崇雅,詰奸刑暴,頗立功業。然以明臣而仕清,入於《二臣》之傳,識者鄙之。康、雍之間,韓城張廷樞作大司寇,崇正除邪,發奸
伏,權幸為之斂跡,天下想望丰采,然太剛則折,卒罹破家亡身之禍。後雖昭雪,追諡文端,然律以明哲保身之道,未免過於戇直也。”乾隆朝又有王土棻,嘉慶朝有王灃中,道光朝有王鼎。
關於黨崇雅的生平事跡見於《清史稿》、《清史列傳》、《續修陝西通志稿》和清人的筆記中。
但“陝派律學”的形成卻在同光時期,而且與薛允升這個人有著莫大的關係。換句話說,沒有薛允升,就不可能有“陝派律學”。薛允升是“陝派律學”的創始人。作為“陝派”創始人,薛允升具備三個條件:(1)本人有不凡的律學成就和學術造詣;(2)其學術成就和人格魅力產生了巨大影響;(3)受其影響律學家以“陝籍”人士為主。
自1856年考中進士就分在刑部,從此他的一生就和法律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且他本人似乎對法律有著天然的興趣。吉同鈞在《薛趙二大司寇合傳》中說:
“允升字雲階,鹹豐丙辰科進士,以主事分刑部,念刑法關係人命,精研法律,自清律而上,凡漢唐宋元明律書,無不博覽貫通,故斷獄平允,各上憲倚如左右手,謂刑部不可一日無此人。不數年,升郎中,外放江西饒州知府,七年五遷,由知府升至漕運總督,以刑部需才,內調刑部侍郎,當時歷任刑尚者,如張之萬、潘祖蔭、剛毅、孫毓汶等,名位聲望加於一時,然皆推重薛侍郎。凡各司呈劃稿件或請派差,先讓薛堂主持先劃,俗謂之開堂。如薛堂末劃稿,諸公不肯先署,固由諸公虛心讓賢,而雲階之法律精通,動[令]人佩服,亦可見矣。後升尚書,凡外省巨案疑獄不能決者,或派雲階往鞫,或提京審訊。先後平反冤獄,不可枚舉。”
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說:“其律學之精,殆集古今之大成,秦漢至今,一人而已。”
如果說薛允升僅僅是自己對法律產生極大的興趣,那么,在清代的歷史上,最多再出現一位偉大的律學家。但薛允升偏偏是這樣一個人,他不但對法律有著超乎尋常的理解,而且非常重視“鄉誼”,對刑部中初來乍到者往往給予不憚其煩的指導和幫助,尤其是新分部的陝西鄉黨。他性格上的這個特點使得刑部內逐漸形成了一個以陝西人為主的學術團體,即“陝派律學”。當然,重視“鄉誼”也成了他被人譏諷的把柄。《近代名人小傳》就這樣說:
薛允升“長身瘦削而意氣勤懇,有關中故家之風,掌秋曹日,所屬多以律書求解,輒為解導,不憚煩也。然俗學無識,立朝未嘗有建白,復私鄉誼,卒被彈去。”
《續修陝西通志稿》謂薛允升“尤好誘掖後進,成就頗多,如趙舒翹、沈家本、黨蒙、吉同鈞輩,乃門生故吏中之傑出者,其它不可枚舉”。
俗話說,獨木不成林。在刑部,在薛允升的周圍,還有很多以陝籍人士為主的律學家。吉同鈞在《薛趙二大司寇合傳》說:“陝派律學”繼起者為趙舒翹。
趙舒翹“同治聯捷成進士,以主事分刑部,潛心法律,博通古今,《大清律例》全部口能背誦,凡遇大小案無不迎刃而解。十年升郎中,任提牢、秋審處坐辦、律例館提調。蓋律例館為刑部至高機關,雖堂官亦待如幕友,不以屬員相視。展如任提牢時,適遇河南王樹汶呼冤一案,時雲階為尚書,主持平反以總其成,其累次承審及訊囚、取供、定罪,皆展如一手辦理。案結後所存爰書奏稿不下數十件,各處傳播奉為司法圭臬。”
“陝派律學”的出現,在當時的刑部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當時人們就有各種解釋。曹允源在《慎齋文集》序中說:
“國家政事分掌於六曹,而秋官一職關人生命,視它曹尤重。為之長者類多擢自曹司重望,諳習法令。即敘勞外簡,往往不數年驟躋右職,入掌部綱。故它部長官遷調不常,而秋官任獨久,蓋非精研其學者不能盡職也。陝西人士講求刑法若有神解夙悟。自康熙間韓城張文端公為刑部尚書,天下想望風采。厥後釋褐刑部者,多本所心得以著績效,如為學之有專家,如漢儒之有師法。同治間,長安有薛公雲階,聲望與文端埒。越十數年,光緒中葉,趙公展如繼薛公而起,由刑部郎中出典大郡,洊膺疆寄,內召為侍郎,旋擢尚書,決疑平法有張釋之、於定國之風。薛公平反冤獄,嘖嘖人口,視刑律為身心性命之學,嘗以律例分類編訂,手錄積百數十冊,又著《漢律輯存》、《唐明律合刻》、《讀律存疑》等書。公亦采古人有關刑政嘉言懿行,成《象刑錄》。任提牢廳時,輯《提牢備考》,皆足為後世法。然薛公在刑部先後垂四十年,年逾八秩,雖間關行在,卒以壽終。而公則以尚書兼軍機大臣,值拳匪構亂,為外人所持,竟不得其死。其學同,其名位同,乃其所遭懸絕如此,得不謂之命也邪。”
刑部作為天下之刑名總匯,關乎人的生殺大事。在某種程度上,刑部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部門,在刑部任職者必須是專業技術人員,這在客觀上為律學的繁榮提供了前提條件。但說“陝西人士講求刑法若有神解夙悟”,這僅僅只是一種溢美之辭。當時的清政府中央有六部,在刑部當差被視為最苦的差事,而陝西僻處西北邊陲,地瘠民貧,因此陝籍人士在通籍後往往能吃苦耐勞,更加勵志。如《舊京瑣記》云:
“刑曹於六部中最為清苦,然例案山積,動關人命,朝廷亦重視之。故六堂官中,例必有一熟手主稿,余各堂但畫黑稿耳。薛尚書允升既卒,蘇撫趙舒翹內用繼之。趙誅,直臬沈家本內調為侍郎,皆秋審舊人。凡稿須經沈畫方定。余在刑曹時,見滿左右堂既不常到,到則各司捧稿,送畫輒須立一二小時,故視為畏途,而愈不敢至。其庸沓可笑,然尚虛心,蓋每畫必視主稿一堂畫畢否,既畫則放筆書行。若間見有未畫者,則曰‘先送某堂,看後再送’雲。”
其他文獻亦有類似說法,如《國乘備聞》:“部務之不振也,曹郎積資十餘年,甫諳部章,京察保一等,即簡放道府以去。侍郎多起家翰林,初膺部務,臨事漫不訾省,司員擬稿進,涉筆占位署名,時人謂之‘畫黑稿’。尚書稍諳練,或一人兼數差,年又耄老,且視六部繁簡次序,以調任為升遷(舊例由工調兵、刑,轉禮,轉戶,至吏部,則侍郎可升總憲,尚書可升協辦),勢不得不委權司曹。司曹好逸惡勞,委之胥吏,遂子孫窟穴其中,倒持之漸,有自來矣。唯刑部法律精,例案山積,舉筆一誤,關係人生死。歷朝重獄恤刑,必簡一曾任刑曹、熟秋審者為尚、侍。薛允升薨,江蘇巡撫趙舒翹內用為尚書。舒翹誅,直隸臬司沈家本內用為侍郎,皆刑部秋審處舊僚也。薛、趙、沈之治刑部也,薛主嚴,趙、沈主寬。”
同光時期在刑部形成了以薛允升為中心,以陝籍人士為主的“陝派律學”,其人員有雷榜榮、吉同鈞、黨蒙、張成勛、段燮、蕭之葆、武瀛、段維、高祖培等。當然,“陝派律學”不純粹都是由陝籍人士組成,如從學術關係上看,沈家本的學術成就與“陝派律學”在某種程度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學術淵源上講,沈家本當屬於“陝派律學”。
甚至有些學者認為,“正式的經歷及非正式的贊助是仕途當中最明顯的部分,但是加入一個律學博士學會也是相當重要的,這類學會同時具有學派以及地方派系的特色。當沈家本被允許加入當時主控刑部的兩個學派之一陝派(陝西)之後(另一個是豫派),他自1875年起就開始攀升。”儘管沈家本祖籍非陝西,他與民國時期主持法務部、大理院的著名法律人物許世英、董康等皆為“陝派律學”的門生。參見鞏濤(Jérme BOURGON):“西方法律引進之前的中國法學”,林惠娥譯,載《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法國漢學》(第8輯),中華書局2003年版。徐忠明也在“中國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超越西方,回歸本土?”一文中“順便指出,雖然沈家本是浙江歸安人氏,但是他的律學研究屬於陝派範圍”。參見徐忠明著:《案例、故事與明清時期的司法文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頁。
三、“陝派律學”的衰落
庚辛(1902年)之後,“陝派律學”漸趨衰落。
辛丑年(1901年),趙舒翹、薛允升先後死去。吉同鈞、張成勛、蕭之葆在清亡後亦陸續辭官。
吉同鈞《送蕭小梅郎中歸田序》:“小梅仕秋曹十餘年,以廉隅氣節期許,不屑於法律,而法律知識自非同列所及,事長官羞作婀態,亦非故以崖岸自高,太史公所謂‘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者,殆兼有之。當民國建設之初,眾人戀戀官職,首鼠兩端,甚者多方奔求,惟患失之。小梅獨決然捨去,如棄敝屣,寧終老於鄉閭,而不貪非分之爵祿;寧力農以食苦,而不作伴食員,誠士大夫中之鴻鵠、驊騮也。世俗不察,或目為迂腐不識時勢,或嗤為矯激不近人情,是亦燕雀不知天地之高,駑駘不知宇宙之大也,何足怪哉?”
四、“陝派律學”的學術成就
薛允升是清末著名的法學家,是沈家本一生都極為敬重的前輩和老師,其學術成就尤為沈家本所推崇。沈氏在為薛允升的名著《讀例存疑》作序時寫道:“國朝之講求律學者,惟乾隆間海豐吳紫峰中丞壇《通考》一書,於例文之增刪修改,甄核精詳。其書迄於乾隆四十四年。自是以後,未有留心斯事者。長安薛雲階大司寇,自官西曹,即研精律學,於歷代之沿革,窮源竟委,觀其會通,凡今律、今例之可疑者,逐條為之考論,其彼此抵捂及先後歧異者,言之尤詳,積成巨冊百餘。家本嘗與編纂之役,爬羅剔抉,參訂再三。司寇復以卷帙繁重,手自芟削,勒成定本,編為《漢律輯存》、《唐明律合編》、《讀例存疑》、《服製備考》各若干卷,洵律學之大成而讀律者之圭臬也。”
(清)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4冊),《寄簃文存》卷六,鄧經元、駢宇騫點校,中華書局1985年版。
沈家本在《薛大司寇遺稿序》中說:“大司寇長安薛公,自釋褐即為理官,講求法家之學,生平精力,畢瘁此事。所著有《唐明律合編》、《服製備考》、《讀例存疑》、《漢律輯存》諸書。”
(清)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4冊),《寄簃文存》卷六,鄧經元、駢宇騫點校,中華書局1985年版。
薛允升的律學研究成就對後來的清末法律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曾參預修訂《大清現行刑律》的董康說:“《現行刑律》大致采長安薛允升《讀律(例)存疑》之說。”
董康:《中國修訂法律的經過》。沈家本在《故殺胞弟二命現行例部院解釋不同說》中指出:“原任刑部尚書薛允升,近世號稱專精刑律者,其所著《讀例存疑》一書,於此條頗有微詞。大致謂,爭奪財產、官職謀殺弟侄分別年歲問擬斬絞辦理,尚無歧誤。至‘讎隙不睦’一層,是否專指胞弟及胞侄之年未及歲者而言,礙難懸擬。蓋非素有嫌隙,決不致蓄謀致死。……上年法律館修改現行刑律,於《讀例存疑》之說,採取獨多。”
(清)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4冊),《寄簃文存》卷三,鄧經元、駢宇騫點校,中華書局1985年版。華友根通過詳細地研究,認為《讀例存疑》為中國近代修訂新律的先導。
華友根:《薛允升的古律研究與改革——中國近代修訂新律的先導》,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薛趙二大司寇合傳》:
“至於著書共分四種:嘗謂刑法雖起於李悝,至漢始完全,大儒鄭康成為之注釋。乾嘉以來,俗儒多講漢學,不知漢律為漢學中一大部分,讀律而不通漢律,是數典而忘祖,因著《漢律輯存》;又謂漢律經六朝北魏改革失真,主唐兩次修正,始復其舊,明律雖本於唐,其中多參用金遼酷刑,又經明太祖修改,已非唐律真面目,因糾其繆戾,著《唐明律合編》;又刑律所以補助禮教之窮。禮為刑之本,而服制尤為禮之綱目,未有服制不明而用刑能允當者。當時歐風東扇,逆料後來新學變法,必將舍禮教而定刑法,故預著《服製備考》一書以備後世修復禮教之根據,庶國粹不終於湮歿矣。”
薛允升逝世後,沈家本奏請清廷,刊刻其名著《讀例存疑》,並對《讀例存疑》予以高度評價:
《薛趙二大司寇合傳》:
趙舒翹任提牢時,適遇河南王樹汶呼冤一案,時雲階為尚書,主持平反以總其成,其累次承審及訊囚、取供、定罪,皆展如一手辦理。案結後所存爰書奏稿不下數十件,各處傳播奉為司法圭臬。主要著作如下:
1.《提牢備考》,曹允源在《慎齋遺集序》中說:“公采古人有關刑政嘉言懿行,成《象刑錄》。任提牢廳時輯《提牢備考》,皆足為後世法。”《慎齋別集》卷一中載有《提牢備考序》:“光緒乙酉五月長安趙舒翹識於宣武城南寓齋。”
2.《慎齋文集》,原名《映灃山房文集》十四卷,由眉縣王仙洲先生編訂。後改名《慎齋文集》十卷,長安沈幼如先生校字,民國十三年(1924年)酉山書局印刷。
3.《慎齋別集》四卷,由《映灃山房文集》十四卷分出。眉縣王仙洲先生編訂,長安沈幼如先生校字,民國十三年(1924年)酉山書局印刷。
4.《象刑錄》。《慎齋別集》卷一中載有《象刑錄序》。
5.《雪堂存稿》。
6.《豫案存稿》。
吉同鈞,字石笙(石生),陝西韓城人。在其所著的《審判要略》的跋中又有關於其生平的記述:“石笙先生本文章巨手。其治律也,直登其鄉先生薛雲階尚書之堂而胾其醢。西曹中久推老宿,比年名益隆,以法部正郎承政廳會辦兼光法律館總纂,並分主吾律學館及法律、法政兩學堂、大理院講司所四處講習,一時執弟子禮者千數百人。所著法律書稿綦富,而《大清律例講義》一種乃至風行半天下。”
清末,沈家本、伍廷芳主持變法修律,修訂《大清現行刑律》的五位總纂官中吉同鈞名列首位。沈家本、伍廷芳奏請專設法律學堂,開設的課程有《大清律例》,請吉同鈞主講。後來,將吉同鈞的講義編成《大清律例講義》一書,由當時的法部核定出版,沈家本欣然為之作序,弁諸卷首,此書在當時風行全國。在《大清律例講義序》中,沈家本對吉同鈞的學術成就予以高度評價,他說:“韓城吉石生郎中同鈞,於《大清律例》一書,講之有素,考訂乎沿革,推闡乎義例,其同異重輕之繁而難紀者,又嘗參稽而明辨之,博綜而審定之,余心折之久矣。”沈家本又說:“其於沿革之源流,義例之本末,同異之比較,重輕之等差,悉本其所學引伸而發明之,辭無弗達,義無弗宣,洵足啟法家之秘鑰而為初學者之津梁矣。”
《寄簃文存》。
五、“陝派”的司法審判
“陝派律學”的代表人物皆熟讀律例,有很高的從事司法審判的能力,這表現在他們對疑難重大刑獄的審判上。
薛允升執掌刑部數四十年,執法不阿,甚有政聲。薛允升一生審理了許多大案,其中太監李萇材一案,能夠秉公執法,堅決頂住來自慈禧及李蓮英等的壓力,將罪犯正法,顯示其剛正不阿之風骨,並以此被排擠。
“李萇材、張受山等愈無忌憚,竟敢於輦轂之下明目張胆糾眾打鬧娼遼[寮],行兇毆殺捕人。拿交部問,雲階時為尚書,以此案關係重大,若非嚴加懲辦,涓涓不滅將成江河,前朝劉魏之禍將復起矣,前後分三折大放厥詞,痛苦上陳,謂:‘皇上開一面之網,不妨量從末減。臣等為執法之吏,不敢稍為寬縱,且從犯或可稍輕,而首犯斷不容免死。’其意以為寧可違皇上之命、致一己獲咎戾,不能變祖宗之法令、國家受後患也。折上,皇上大為感動,寧可違慈命,而不敢違祖法,降旨依議,李萇材著即處斬,張受山斬監候,秋後處決。當時行刑,民間同聲稱快。”
薛允升對權貴剛正不阿,但也絕不冤枉任何一個人,“江寧案”即周五殺朱彪案,在他的主持下最終平反冤枉。
《清稗類鈔》“江寧三牌樓枉殺二命案”:
光緒辛巳(1881年),沈文肅公葆楨督兩江,江寧有三牌樓(在儀鳳門內)命案,輕率定讞,枉殺無辜,世多冤之。時陳伯潛閣學寶琛方為翰林院侍講學士,以參將胡金傳承緝謀殺朱彪之命盜,妄拿教供,刑逼定案,業將曲學如、僧紹宗處決。雖已由繼任總督劉忠誠公坤一另獲兇犯周步畛、沈鮑洪供認殺彪,並訊出金傳嚇賄眼線教串各節,旋奉旨令忠誠嚴行刑訊,以成信讞,即疑竇孔多,猶待澈究,遂具疏以上聞。
此案真相,實為步畛挾仇起意殺彪,商同鮑洪潛攜篾刀遇彪,以糾邀行竊為名,至三牌樓竹園旁,將彪砍斃,三人同逃,固未移屍,嗣經地保報縣驗詳。文肅遂飭會辦營務處洪汝奎懸賞購線,並派金傳密訪。蓋金傳時為緝捕委員也,先後拿獲學如、紹宗及張克友三人,並賄教方小庚作證,金傳與間官候補縣嚴堃同訊,喝令用刑,威逼成招。初供殺死謝某,旋供為薛泳全,繼復稱為薛春芳。金傳輾轉誘令改供,汝奎於覆審後,以案情重大,稟請派員覆訊。文肅以為此乃會匪之自相殘殺也,即批飭將學如、紹宗正法。及辛巳拿獲竊犯李大鳳,供出步畛、鮑洪殺彪,與辦結前案地方時日相符。當將步畛、鮑洪訊供,不稍諱。
壬午(1882年),德宗以寶琛具疏上聞,遂派麟相國書、薛尚書允升前往查辦,時麟為刑部尚書,薛為刑部侍郎也。既至江寧,反覆推勘,步畛、鮑洪均各供認商同殺彪不諱,金傳亦以刑訊教供各情,據實供吐,小庚、克友等俱各脗合,於是步畛、金傳皆論斬,鮑洪論絞,汝奎、堃均革職,發往軍台效力贖罪,文肅以已薨免議。
徐珂:《清稗類鈔》(第3冊),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154頁。
清末,“不肖州縣玩視民命,多爾草率從事。該管上司不肯認真詳細推勘,非巧為彌縫,即多方掩飾。其能平反更正者,百無一二。而固執原擬者,則比比皆是。推原其故,總由各該督撫徇庇屬員,回護原審。其尤甚者,明知案情實有冤抑,即據實更正處分,亦輕以為與全省局面有礙,終不肯自認錯誤。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即如河南鎮平縣王樹汶呼冤一案,始而迭經御史參奏,該省仍敢飾詞入奏,入人死罪。繼而奉特旨提交臣部審辦,該前撫李鶴年猶復強詞,嘵嘵置辨,希圖搖惑眾聽,顛倒是非,在已發覺者平反尚如此其難,其餘未經發覺者更必任意消弭,安望其自行更正耶。”
“河南司議覆光祿寺少卿延茂失入案件寬免處方奏稿”,見《慎齋文集》卷三。而審理河南王樹汶臨刑呼冤一案的,正是“陝派律學”的第二號重要人物趙舒翹。
〇
《清稗類鈔》“王樹汶為頂兇案”:
王樹汶,鄧州人,幼以被掠為鎮平盜魁胡體安執爨役,體安,鎮平胥也。河南多盜,州縣故廣置胥役以捕盜,有多至數千人者,實則大盜即窟穴其中,時遣其徒黨出劫,捕之急,即賄買貧民為頂兇以銷案。體安尤凶猾,一日,使其徒劫某邑巨室,巨室廉知體安所為,乃上控。時塗制軍宗瀛方撫汴,檄所司名捕之。鎮平令捕體安急,則賄役,以樹汶偽為之,俾役執之去。樹汶初不承,役以非刑酷之,且謂即定案必不死,始諾。樹汶年十五,尫羸弱小,人固知其非真盜也。縣令馬翥聞體安就獲,狂喜,不暇審真偽,遽稟大府,草草定案。既定讞,當樹汶大辟,時體安已更姓名,充他已胥矣,樹汶未知也。刑之日,樹汶始知之,呼曰:“我鄧州王樹汶,非胡體安,若輩許我不死,今乃戮我乎!”監斬官白宗瀛,大駭,命停刑,下所司覆鞫,卒未得要領。樹汶自言父名季福,居鄧州,業農,乃檄鄧州牧朱杏簪刺史光第逮季福為驗,未至而宗瀛督兩湖去。繼任者為河督李鶴年。開歸陳許道任愷者,先守南陽,嘗讞是獄,又與鶴年有連,於是飛羽書,阻光第,令毋逮季福,且百端誘怵之。光第不為動,慨然曰:“民命至重,吾安能顧惜此官以陷無辜耶!”竟以季福上,則樹汶果其子,愷乃大戚,鶴年以袒愷故,持初讞益堅,豫人之官科道者,遂交章論是獄。
鶴年恚言路之持之急也,遂力反宗瀛前議,而益傅會律文,謂樹汶雖非體安,亦從盜,在律盜不分首從,皆立斬,原讞者無罪。然樹汶初止為體安司炊,亦有謂其為孌童者,而實非盜,讞者必欲坐以把風接贓之律,樹汶至是遂為正凶。而官吏之誤捕,體安之在逃,悉置不問。諫臣益大,劾鶴年庇愷,於是朝延有派河督梅啟照覆訊之命。河工諸僚佐,率鶴年故吏,不敢違鶴年恉,啟照亦不欲顯樹同異,竟以樹汶為從盜,當立斬。獄成,言者爭益力。
時潘文勤公方長秋官,廉知其概,提部研鞫,而趙舒翹方以郎中總辦秋審,因以是獄屬之。閱數月,乃得實,將上奏矣,而鶴年使故為文勤門生之某道員入都遊說,文勤入其說,遽中變。舒翹方力爭,文勤忽以父喪去官,南皮張文達公之萬繼其任,文勤亦知為某道員所賣,貽書文達,亟自引咎。疏上,奉旨釋樹汶歸,戍翥及知府馬承脩極邊,鶴年啟照及臬司以下並承審各官皆降革有差。
而光第已先以他事劾罷,則愷嗾鶴年為之也。有以持愷羽書直揭部科諷者,光第笑謝之,貧不能歸,竟卒於豫,年五十五。光第去官二十年,鄧人謀以其治狀上於朝,請祀名宦,以其子祖謀時官禮部侍郎,格於例,不果行。祖謀,字古微,以道德文章著稱於時,更名孝臧,學者稱漚尹先生者是也。
《清稗類鈔》(第3冊),第1133頁。
六、研究“陝派律學”的意義
“陝派律學”出現在中國法律古今交替的時候,其代表人物具有較高的傳統文化素養,出身科舉,且長期在刑部供職,具有豐富的司法實踐經驗和精湛的傳統律學知識,既有“理論”又有“經驗”。
但是,迄今為止,學術界對“陝派律學”還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進行系統的研究。因此,研究“陝派律學”有著重大的學術意義。幾年前,俞江在《傾聽保守者的聲音》一文中介紹了“陝派律學”一個代表人物吉同鈞及其學術成就,最後他對眼下的法學研究提出批評說:“沒有參照系,連經驗積累也不系統;沒有思想淵源,連方法論傳統也被丟棄,法律和法學在虛假繁榮里高歌猛進。”
俞江:“傾聽保守者的聲音”,載《讀書》2002年第4期。我們認為,研究“陝派律學”至少有以下學術價值:
首先,“陝派律學”對傳統法律做了一個完美的總結。其所取得的傳統律學成就無疑是相當高超的,代表著幾千年傳統律學的最高水平。“陝派律學”的奠基者薛允升對歷代刑法的淵源《漢律》有精深研究,著有《漢律輯存》、《漢律決事比》,其中的《漢律輯存》直接對沈家本的《漢律摭遺》產生了學術影響;薛允升還對《唐律》、《明律》進行了比較研究;其《讀例存疑》更是集中在長達幾十年的司法實踐和學術研究中對清代律例的獨到見解,被視為第一部“例學”著作。而趙舒翹的《提牢備考》則是反映古代監獄制度的珍稀資料。因此,研究“陝派律學”對於了解傳統法律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其次,“陝派律學”的代表人物在晚清已提出了一些法律改革的建議。雖然這些建議仍跳不出傳統法律文化的樊籬,但都是針對清代法律實施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實際問題而提出的,這些正是中國法律近代化的基礎。正如沈家本所說,“不深究夫中律之本原而考其得失,而遽以西法雜糅之,正如枘鑿之不相入”。例如,吉同鈞《上修律大臣酌除重法說帖》比沈家本著名的《刪除律例內重法折》還要早,薛允升、趙舒翹也都曾上過諸如此類建議改進法律制度的奏摺,研究這些資料無疑對了解清代法律存在的問題、清末法律改革的歷史背景以及清末修律的內容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再次,“陝派律學”中代表人物參與晚清的變法修律活動。例如,吉同鈞不但親自編纂《大清現行刑律》,而且在《大清新刑律》出台後,對修律的工作不斷地予以關注和評論,他曾對《大清新刑律》發表這樣的看法,“新訂之律,表面僅四百餘條,初閱似覺簡捷,而不知一條之中,實蘊含數條或數十條,將來判決成例,仍當取現行律之一千餘條,而一一分寄與各條之內,不過體裁名詞稍有不同耳”。
《律學館第四集課藝序》,見《樂素堂文集》。清末變法,力主“會通”中西法律,研究“陝派律學”可以了解到傳統法律與現代法律之間如何衝突,又如何進行調整並整合的,也可以了解傳統的法律人如何面對幾千年以來首次出現的法律大變局,這樣可以使我們能對中國法律的近代化會有進一步的認識,對今天的法律改革也能提供有益的借鑑。
又次,“陝派律學”的代表人物在長期的司法審判歷史中表現出了良好的司法官素質,他們一般都能夠嚴格執法,不畏權勢。例如,大司寇薛允升寧肯丟官,也要將太監李萇材等繩之以法。在司法審判中,一絲不苟,認真負責,“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例如,趙舒翹審理的河南王樹汶臨刑呼冤一案,最終水落石出,將庇護地方、草菅人命的河南巡撫等一乾官員參劾奪職。研究“陝派律學”中這些剛直不阿的代表人物,繼承和發揚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精華,無疑對構建我們今天的法治文明不無裨益。
最後,“陝派律學”除了薛允升、趙舒翹在清末去世以外,吉同均、張麟閣等一直生活到民國時期,他們的著作一般在民國時期都刊刻印行,但以後就默默無聞,似乎被人們遺忘了。我們今天研究“陝派律學”,除了回顧中國法律近百年走過的這段曲折歷史,汲取歷史的經驗與智慧,還可以重新評估陝西人對中國傳統法律的繼承和發展,對中國法律近代化所做的準備與貢獻,振奮我們的學術信心,使陝西乃至西北的法學研究和法律教育在今天取得更大的發展。
七、研究的難點
就目前掌握的資料看,除沈家本、董康二人之外,其他人提到“陝派律學”和“豫派律學”的似乎就沒有,因此,研究“陝派律學”首先遇到的難題是史料問題。關於史料的蒐集,特別是有關近代歷史人物史料的收集,有著其特殊性。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分論——《人的專史》第二章“人的專史的對相”中指出:
“研究近代的歷史人物,我們很感苦痛,本來應該多知道一點,而資料反而異常缺乏。我們應該盡我們的力量,蒐集資料,作一篇,算一篇。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經死去,蓋棺定論,應有好傳述其生平。……此時不作,將來更感困難。此時作,雖不免雜點偏見,然多少尚有真實資料可憑。此時不作,往後連這一點資料都沒有了。”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頁。
徐一士在《一士譚薈》中也講:
“史料為治史者所注重,近代史料為時未遠,關係尤切,更應特加之[注]意。從事收集保存,以供鏡覽,而資史家之要刪。乃往往徒知古昔史料之可貴,於近者則忽之。或知其足重矣,而以為得之可不甚廢力,未若古昔史料之難於發見,因之不肯亟亟訪求,孜孜輯錄,不知斯固有稍縱即逝者,久且放失淹沒,不易復睹。蓋史料緣是而沈冥不彰者甚夥,可喟也。……此種感覺,當不僅梁氏一人為然,其過要在從事蒐集之不早耳。”
徐一士:《一士譚薈》,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11頁。
徐一士熟悉近代掌故,長期從事近代歷史資料的蒐集整理與研究,他是有感而發。為了不使“陝派律學”的資料“放失淹沒”,為後人不易復睹,本書將對“陝派律學”的史料“亟亟訪求,孜孜輯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