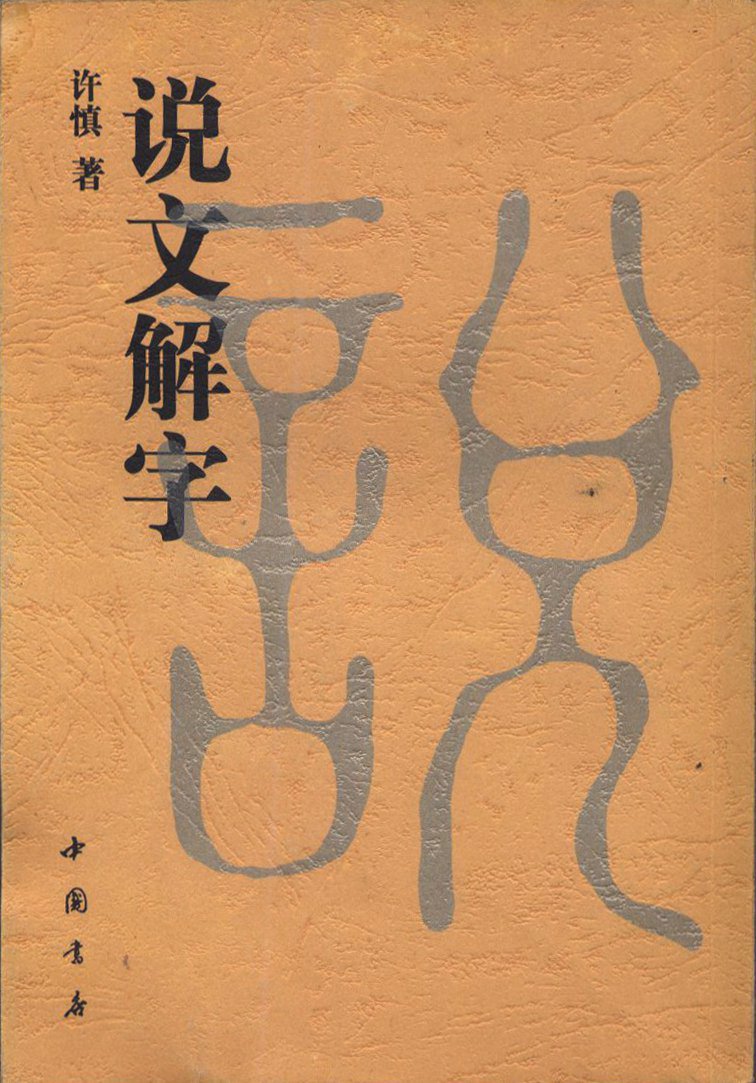基本介紹
- 書名:說文解字
- 又名:說文
- 作者:許慎
- 成書時間:公元100年~公元121年
分類歸納,解字方法,漢字規律,編排體例,說解方式,釋義原則,構形體系,綜合運用,吸收成果,
分類歸納
許慎根據文字的形體,創立540個部首,將9353字分別歸入540部。540部又據形系聯歸併為14大類。字典正文就按這14大類分為14篇,卷末敘目別為一篇,全書共有15篇,其中包括序目1卷。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系統地闡述了漢字的造字規律——六書。
解字方法
漢字規律
“漢文字的一切規律,全部表現在小篆形體之中,這是自繪畫文字進而為甲文金文以後的最後階段,它總結了漢字發展的全部趨向,全部規律,也體現了漢字結構的全部精神。”(姜亮夫《古文字學》59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因為有了《說文》,後人才得以認識秦漢的小篆,並進而辨認商代的甲骨文和商周的金文與戰國的古文。
利用《說文》考釋甲骨文金文的最基本的方法是“比較法”,即通過已識字和未識字的字形對比來考釋古文字。宋人釋讀金文就是從“比較法”開始的。“因為周代的銅器文字和小篆相近,所以宋人所釋的文字,普通一些的,大致不差,這種最簡易的對照,就是古文字學的起點。一直到現在,我們遇見一個新發現的古文字,第一步就得查《說文》,差不多是一定的手續。”(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增訂本,165至166頁,齊魯書社1981年版)
“比較法”在運用過程中被逐步發展完善,一開始只是籠統粗略地對照未識字和已識字的字形,以後認識到應該從文字可以分解為偏旁的角度去進行字形的分析比較。這種偏旁的比較不僅使字形的對比變得精密合理,而且在釋讀古文字時能夠起到舉一反三以簡馭繁的作用。如果要進行“偏旁分析”,就必須熟悉小篆的形體結構,就必須熟悉《說文》,因為《說文》的旨趣就在於“說文”、“解字”,即一方面闡述每個獨體字的字形的含義,一方面解析每個合體字的構成情況,指明合體字由哪些偏旁構成,以及第個偏旁在記錄語辭彙的音和義中起什麼作用。
在考釋古文字的時候,有《說文》的正篆或重文可資對照,那么釋讀起來就確鑿可信。如果是《說文》中沒有的字,哪怕已經認清了古文字的偏旁結構,甚至已經可以確定它的意義,比如說是人名、地名或祭名,但是音讀不明,還不能說完全認識了這些字。
如果說,小篆不如甲骨文金文更能體現原始的造字意圖,這是《說文》的劣勢的話,那么甲骨文金文缺乏大批有影響的文獻語言做根據,而《說文》的字義說解來自古代的經傳典籍,這又是《說文》的優勢。所以,如果要解釋古書上的疑難字詞或者進行古漢語辭彙研究,還要把《說文》作為主要依據。
《說文》之學是根柢之學,它在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詞典學以及文化史上都占有顯著的地位。它與詞義的關係尤其密切。我們解釋古書上的疑難字詞之所以離不開《說文》,因為《說文》訓釋的是詞的本義,而本義是詞義引申的起點。我們了解了詞的本義,就可以根據本義的特點進一步了解引申義、以及和本義毫無關係的假借義。我們了解了哪個字是本字,就可以進而確定通假字,並且掌握文字用法的古今之變。
編排體例
《說文解字》四個字告訴讀者,這部書由“文字”和“說解”兩部分組成。對於文字部分,我們需要了解兩個問題:一是《說文》收了哪些字,二是怎樣把這些字編排起來的。
許慎之所以把小篆作為收字和注釋的對象,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因為小篆是一種經過系統整理的文字,是“書同文”的產物,它比籀文和古文都規範、完備;因為小篆從籀文脫胎而來,與籀文大部相同,不同之處僅僅在於有些字在籀文基礎上稍加簡化;因為小篆同六國古文固然有不同的一面,但是也有相同的一面,拿出土的石刻儒家經典中的古文和《說文》中的小篆相對照,相同的占35%(曾憲通《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合證》,載《古文字研究》第七輯);所以把小篆作為字頭也就涵蓋了那些與小篆相同的古文和籀文。許慎在《說文·敘》中說:“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指明的是所收的正字,而非指重文。據統計,《說文》重文中指明古文的有500字出頭,指明籀文的有219字,遠遠少於許慎所能見到的古文和籀文。這說明和小篆相同的古文、籀文決不在少數。
把兩處(《說文·敘》、《漢書·藝文志》)記載參照起來看,可以肯定,許慎講的“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指的是漢初整理的《倉頡篇》(55章)及揚雄所作的《訓纂篇》(34章),共14篇,89章,每章60字,正5340字。如果再加上班固所作的《續訓纂篇》13章,總計102章6120字。那時六藝群書當中所能見到的文字大抵在這五六千字的範圍之內。
作為供人查檢的字典,《說文》收字全面、系統,不僅包括難懂的字詞,而且包括常見的字詞,《說文》收正字及重文共10516個,可謂集漢代文字之大成。《說文》也有一些常用字沒收,甚至在《說文》的說解中出現的一些字也不見於《說文》的正文。其中有些字沒收並非是由於疏忽,例如“劉、由、希、趾、銘、志”等字。當然,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要證明《說文》收字盡善盡美,而只是說明許慎的收字原則。事實上,由於許慎輕視後起的俗字,所以儘管在說解中隨俗,使用這些字,但是堅持不把這些字作為正字收進《說文》。另外,由於疏忽或見聞不及,《說文》也遺漏了一些字。
《說文》的重文即異體字,包括古文、籀文、篆文、秦刻石、或體、俗體、奇字、通人掌握的字、秘書中的字,共九類。《說文》以小篆作為字頭,與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則作為重文。這是正例。有時為了立部的需要,把古文作為字頭,把篆文列為重文。這是變例。秦刻石即秦朝時在石頭上刻的文字,也是小篆。或體指另外的形體,多為小篆。俗體指在民間流行的字型,限於小篆。奇字指古代某種特殊的字型,屬於古文。通人掌握的字,指來源於專家的特殊的字。秘書中的字,指那些講陰陽五行、秘密而不公開的書里所用的特殊的字。這兩類字也限於小篆。在以上九類重文中,古文、籀文、或體三類占了絕大部分,其他六類為數很少。
重文列在正字下面,不產生編排問題,而9353個形態各異的正篆怎么編排,確實是一個難題。人們在長期使用漢字的過程中已經對漢字的分部有了一定的認識。許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提出“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說文·敘》)的編排漢字的原則。
許慎把眾多的漢字按形體構造分成了540部,創造了一套成體系的“偏旁編字法”。
這540部又是怎樣編排起來的呢?據《說文後敘》,是“立一為專”、“畢終於亥”,“雜而不越,據形系聯”。540部按“始一終亥”編排,表現了許慎的哲學思想,這是時代風尚所致,不必苛求古人的。
“據形系聯”指的是根據字形相近來安排次序。
部首排列也有“以類相從”的情況。
除了“據形系聯”和“以類相從”之外,部首排列也有亳無道理可言的情況。南唐徐鍇曾專論《說文》“部敘”(《說文系傳》第三十一卷),試圖把每一部的次序都講出點道理。其實,在嚴格的檢字法部首問世之前,部首的排列不管從形體出發,還是從意義出發,必然具有不確定性,我們既不必苛求許慎,也不必強作解人。
每部當中列字的次第,大致來說是按照意義排列,把意義相關的字排在一起。按照《說文》列字的體例,凡是與部首形體重疊或相反的,都列於該部之末,所以“禁”、“禫”二字或者是被後人顛倒了次序,或是是後人附益的字。
許慎對於各部中字的排列都有一些安排,不過部與部之間因內容而異。
總而言之,《說文》的“部敘”和部內收字次第雖然有一定的安排,但是並沒有嚴密的體例。初學《說文》,要查檢某個字,往往不知道它屬於哪一部。《說文》的部首是文字學的部首,與後代的檢字法的部首不同。要想順利地翻檢《說文》,必須逐步熟悉《說文》的540部及漢字的構形。這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就連刊定《說文》的徐鉉也感嘆說:“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尋示一字,往往終卷。”(《說文解字篆韻譜》序)好在中華書局影印的大徐(鉉)本《說文》後邊附有部首檢字和正文的檢字,能夠幫助我們解決不少問題。還有一個辦法,就是通過《漢語大字典》來查檢《說文》。凡是《說文》所收的字、所作的說解,這部大型詞書都收錄了,並作了進一步的解釋,可供讀者參閱。
說解方式
《說文》說解文字的一般格式是:首先解釋字義,其次分析字形結構,然後根據情況補充其他方面的內容,如引經作為書證,用“讀若”標音,等等。對於部首,都要標明“凡某之屬皆從某”這樣一句話,而對於部首所轄的字都要標明“從某”來呼應。“從”表示在形體上和意義上的從屬關係。因為《說文》只解釋字的本義,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只列舉一個義項,如果有必要說明另外的意義,則用“一曰”表示。大致說來,說解的次序是先解釋字義,再分析字形,然後用說明形聲字聲旁及譬況讀音的方法說明字音。
《說文》的釋義方式,或者用詞釋詞,或者用短語釋詞。用詞釋詞,在訓詁學上稱作單字相訓,又稱直訓。以上直訓可分四種類型。第一種是甲詞釋為乙詞,而乙詞不採用直訓方式進行解釋。第二種類型是甲詞釋為乙詞,而乙詞又釋為甲詞,這在訓詁學上稱作互訓。第三種類型是甲詞、乙詞、丙詞同釋為丁詞,這在訓詁學上釋作同訓。第四種類型是甲詞釋為乙詞、乙詞釋為丁詞,丁詞又釋為甲詞,這在訓詁學上稱作遞訓。
以詞釋詞的優點在於簡潔明了,尤其是在溝通古今語言、對譯通語方言方面更是其他釋義方式所不能企及的。《說文》的用意在於把方言譯成通語。直訓的釋義方式重在以易釋難、以今釋古、以通釋別,系聯了相互訓釋的各詞之間的同義關係,展示了被釋詞所屬的義類。直訓的缺點是,對詞義缺乏細緻的分析,未能揭示出詞的內涵和外延,對同義詞只求其同,不求其異,不能使人了解到同義詞之間的區別。
用短語釋詞,或用一句話、幾句話來闡明詞義的界限,對詞所表示的概念的內涵作出闡述或定義,古人把這種訓釋詞義的方式叫下義界。《說文》給詞下義界,簡明扼要,準確生動,具備了現代字典的特點。
《說文》對於數目、度量衡、親屬稱謂的解釋和今天的解釋毫無二致,這是因為古今的認識一致。對於其他事物,例如對於動物、植物、昆蟲等等,許慎儘管缺乏現代的學科知識,但是也能夠從生活經驗出發指出被釋詞的屬別。比如“蚤”是一種昆蟲,“雀”是一種鳥,許慎根據它們的生活習性分別釋為“蹌人跳蟲”和“依人小鳥”。在《說文》中經常採用這種類別式的下定義的方式,也就是說,在大類名的前面加上適當的限制或修飾成分。這種界說,一方面能夠表現詞的特點,另一方面還能夠把這個詞和鄰近詞區別開來。類別式的義界在《說文》中占很大比例。有些形容詞沒有適當的同義詞不好互訓,但是有相應的反義詞,所以往往用否定語作註解。如“假”為“非真也”,“旱”釋為“不雨也”。這樣做既省事又明白。《說文》有時對詞進行描寫、比況式的說解。在《說文》中,對於實物、對於行為或狀態,都可以描寫或比況,至於對於歷史和地理的敘述,也是一種描寫,如釋“館”時敘述《周禮》,釋“河”時敘述黃河的發源和流向。
王力先生把《說文》用下義界說解字義的方概括為五種,即:天然定義、屬中求別、由反知正、描寫、譬況。(《理想的字典》,載《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一冊第350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從釋詞方式著眼,有直訓和義界之分;從釋詞目的著眼,有義訓和聲訓之分。如果釋詞的目的在於說明詞的含義,這是義訓。如果釋詞的目的在於說明詞義的來源,即選用與被訓釋詞音近義通的同源字來作訓釋詞或主訓詞,這就是聲訓。義訓可以選擇直訓和義界方式,如上文所述,聲訓也可以選擇直訓和義界方式。
以上情況是用訓釋詞說明被釋詞的語源,前人稱之為推因。還有一種情況,是用短語或一兩句話來說解被釋詞,並在說解中指明被釋辭彙的語源。如“韓”釋為“井垣也”,這是解釋詞義,而說解中的“垣”字與被釋詞“韓”在古音中既雙聲又疊韻(同屬迎母元部),意義也相通,所以實際上許慎是以“垣”釋“韓”的語源。我們把下義界時對被釋詞進行聲訓的訓釋字稱作主訓詞。讀《說文》的說解要特別留心找出主訓詞。有主訓詞而輕易放過,只能算讀懂了說解的皮毛;找出了主訓詞,才算懂得了說解的精髓。主訓詞都有實義,大都處於說解中的關鍵位置,只要從音義兩方面去和被釋詞比較,並不難找到。拿上述例子來說,“斐”釋為“分別文”,“文”是主訓詞。“娶”釋為“取婦也”,“取”是主訓詞。“潮”釋為“水朝宗于海”,“朝”是主訓詞。“婢”釋為“女之卑者也”,“卑”是主訓詞。這些主訓詞自然貼切地指明了被釋詞的語源。
有時《說文》的一條說解同時使用直訓和義界兩種形式,而目的都在於說明語源。如“媒”,釋為“謀也”,又進而說明“謀合二姓也”;“山”釋為“宣也”,又進而說明“宣氣散生萬物”。有時《說文》首先說明詞義,然後論述其得名的由來。
在現代一般的語詞詞典中不進行語源的解釋,這個任務由專門的語源學詞典承擔,而傳統的訓詁則既包括義訓又包括聲訓。儘管聲訓還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語源學的探討,但是它所反映的古人對詞義的語源學的解釋有一些是可取的,我們在讀《說文》的時候應該潛心體會,適當取捨。
《說文》分析字形結構有一套程式化的用語,簡而言之,對於象形字多使用“象形”、“象某形”、“象某某之形”、“從某,象某某”、“從某,象某某之形”這些用語。
《說文》中除了指明“上”、“下”二字為指事以外,對其他指事字的說解用語與對象形字的說解用語大致相同,多使用“象形”、“象某某”、“象某某之形”、“從某,象某某之形”等語。比較特殊的說解用語是“從某,某······”例如:“本,木下曰本。從木,一在其下。”(《木部》)“末,木上曰末。從木,一在其上。” (《木部》)說解中的“一”是指事符號。
《說文》對於會意字最經常使用的說解是“從某,從某”、“從某某”、“從······某”、“從某······某”;對於省形字使用“從某省,從某”、“從某,從某省”這些用語。《說文》中的異體會意字絕大多數是合二體會意,其中“從某某”及“從某······某”的形式可以連讀成文。
《說文》對於形聲字的說解,多使用“從某,某聲”、“從某從某,某亦聲”、“從某某,某亦聲”、“從某省,某聲”、“從某,某省聲”等用語。形聲字多為一形一聲,“從某,某聲”是形聲字最通常的形式。“亦聲”字是聲旁有顯示語源功能的形聲字,古人稱為會意兼形聲或形聲兼會意。“從某省,某聲”,說解的是形旁有所省略的形聲字。“從某,某省聲”,說解的是聲旁有所省略的形聲字。
六書反映在字的構形上只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前四書。轉注是給同義詞造字的一種方法,除了在《說文敘》中許慎舉出“考”、“老”為轉注字外,在正文中從未提及,我們初學《說文》可以不必深究。至於假借,因為是以不造字的方式來滿足記錄語言的需要,所以許慎不可能指明哪一個字是假借,但是許慎指出了一些字的假借用法。許慎用“故為”、“故以為”、“故藉以為”、“故因以為”等用語說明假借義與本義存在著引申關係。在《說文·敘》中,許慎說:“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也是把不給引申義造字仍用原字作為假借。後人講假借比許慎又前進了一步,不僅講引申本義的假借,而且講純粹借音的假借,而純粹借音的假借最能體現假借的本質。
《說文》解釋字音採用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對於形聲字都註明“某聲”、“某亦聲”、“某省聲”,從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形聲系統。把若干層次的主諧字和被諧字都系聯起來,這就是漢字的形聲系統。清代有很多人作過這種工作,其中嚴可均的《說文聲類》最完整、系統。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打破了《說文》原有的分部,按照形聲系統重新進行了編排。更值得提出的是段玉裁作《六書音韻表》,經過對《說文》形聲系統的研究,提出了“同聲必同部”的理論。比如上述從“工”得聲的字,以及從以“工”為聲旁的形聲字得聲的字,都屬於一個古韻部——東部(ong)。這個發現非常重要。從此研究古音不僅可以依靠《詩經》、《楚辭》等韻文,而且可以藉助於《說文》的形聲系統。
《說文》解釋字音的第二種方式是用讀若比擬漢代的音讀。許慎在世時還沒有發明反切,當時注音使用譬況法,有的用一字擬音,有的用俗語注音,有的用方言注音,有的用成詞、成語注音,還有的以義明音。在用譬況法擬音時大多用“讀若某”,有時也採用“讀與某同”的說法。
許慎著《說文》,多處引用孔子曰、韓非子曰、賈侍中(賈逵)說、劉向說、杜林說、揚雄說、司馬相如說、譚長說、官溥說、王育說······來說解字形、字義、字音,做到‘博採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說文·敘》),對於有些文字形音、義不清楚的地方,則標明一個“闕”字。
最後我們講一講《說文》注釋的三種特殊格式。一是合釋聯綿詞。對於聯綿詞,《說文》將構成聯綿詞的那兩個字放在一起解釋。這說明許慎已經初步有了詞的觀念。二是“連篆為釋”。《說文》的正篆是被注釋的對象,但是有時候正篆一身二用,既作為被注釋字,又作為注釋字,要跟注文中的字連讀。例如:“離,黃倉庚也”,“參,商星也”,要讀為“離黃,倉庚也”,“參商,星也”。本來,《說文》收字每個正篆後附列一個隸書,後來把隸書刪去了,又誤把與正篆相同的第一個說解字也刪去了,所以才造成這種費解的體例。三是“複句為釋”。《說文》的釋文一般是一個詞、一個短語或一句話,但是也有兩個詞、兩個短語的時候,我們把這種體例稱為“複句為釋”。《說文》在流傳過程中,有的“複句為釋”中間的“也”字被刪掉了,使說解變得晦澀難懂,如果補上“也”字,恢復成“複句為釋”,釋文就顯豁了。例如:“尋,繹(也)理也。”(《寸部》)“標,本杪(也)末也。”(《木部》)以上所講到的後兩個問題涉及到校勘。古書流傳過程中,不管是手抄還是刻版,都造成一些訛誤。如果我們能夠精心地體會《說文》的說解體例,自覺地訂正訛誤,不但可以大大提高我們的研讀水平,而且可以培養我們嚴謹的治學精神。
釋義原則
《說文》是一部古文字字典,它按照文字學的要求解釋本義,努力做到兩個統一,即:形和義的統一,文字和語言的統一。所謂形義統一,是說《說文》全面分析了小篆的構形體系,根據字形來解釋文字的本義。所謂文字和語言統一,是說《說文》的釋義是直接從文獻語言中概括出來的,是與文獻語言相符合的。
古人說:“許書之要,在明文字之本義而已。”(江沅《說文解字注後敘》)所謂本義,指的就是體現在文字字形上的字義,它一方面反映出表彰文字初期的造字意圖,另一方面又確實是在古代典籍中被使用過的詞義。
小篆的字形反映的是文字的造義,古籍中的用例反映的是詞的實義,在《說文》中二者大多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不一致的情況。
所以造成這種情況,是由於文字的造意和詞的實義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儘管造意是以實義為依據的,但是它有時僅僅是實義的具體化、形象化的說明,語言中被使用的實義要概括、抽象得多。因為《說文》要緊密結合字形說解字義,限於體例又只能用極簡單的話來訓釋,所以就難免遷就造意。我們在理解《說文》的這種訓釋時,只需要除去那些形象的具體因素而加以進一步的概括,就能把字的造意和詞的實義一致起來。
由於拘泥於字形,《說文》對造義也有解釋得不夠確切,甚至迂曲荒謬的時候。
總的來看,儘管《說文》對於字義的訓釋存在一些問題,但是絕大多數釋義是有文獻語言作為根據的,是可信的。《說文》雖然沒有自覺地在每個字下都引用書證,但是這並不是說對這些字的訓釋沒有文獻的根據。
由於《說文》的絕大多數訓釋是有文獻做根據的,所以對字義的解釋比對字形的解釋可靠性要大。往往有這種情況,《說文》把字形解釋錯了,但釋義並不錯。
我們說《說文》中的絕大多數訓釋有文獻根據,並不是說就可以迷信《說文》。由於時代的局限,《說文》的語言資料只能取自周秦文獻,所收的文字不過是晚周、秦皇以至漢代的字型綜匯。至於甲骨文,因為出土很晚,許慎當然無從看見,就是金文也見的極少。這些都限制了他的眼界,在寫作《說文》時遺漏和謬誤之處自不能免。
我們要在讀《說文》時堅持形義統一的原則,首先要了解、掌握小篆的構形體系及六書理論,此外還要注意學習一些古文字的知識,吸收古文字的研究成果,來補充、糾正《說文》。
我們要在讀《說文》時堅持《說文》與文獻相結合的原則,掌握古人提倡的“以字考經,以經考字”的訓詁方法(陳煥《說文解字注·跋》)。
我們要學會利用《說文》的材料去解決文獻閱讀中遇到的問題,更準確更深入地解釋詞義,這就是“以字考經”。
構形體系
漢字發展到小篆階段,其結構已經完全符號化了,這突出地體現在合體字上。在甲骨文中,圖畫性很強的會意字(唐蘭稱其為象意,姜亮夫稱其為象事),到了小篆,或者將其拆散分別變成有音有義的構件然後重新組合,或者廢棄不用另造形聲字。這些字的構形特點是“據事繪形”,即根據詞義以比形會意的方式分別造出一個個字來。這些字圖畫性強,符號性差;整體性強,分析性差;在字的內部,渾然一體,在字與字之間,缺乏整體的聯繫。這種造字方式是初級的,也是低能的。到了小篆,不僅已經完全拋棄了“據事繪形”的造字方式,而且對漢字型系中已經存在的這種字進行了改造。從甲骨文到小篆,這種圖畫性的合體字通過加強符號性,加強分析性,改造為由文字構件合成的會意字。這是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對甲骨文的形體進行更徹底的改造,變會意字為形聲字。“沬、何、隊、囿“等字就屬於這種情況。
漢字結構到小篆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定型化了的科學體系。這個體系經過許慎的分析綜合,體現在《說文》的分部及說解之中。我們要了解小篆字系,首先應該從《說文》540個部首入手、去研究、把握小篆構形的普遍規律。這540個部首三分之二以上是獨體的文,也是小篆字系的文字構件,將近三分之一的部首是合體的字,可以進一步分解為若干個文字構件的。《說文》之所以把包括同體會意的不少合體字作為部首,是因為《說文》遵循文字學的原則,按字的意義來歸部。
因為《說文》要嚴格貫徹文字學的原則,所以儘管有些部所統轄的字極少,甚至有些部連一個統轄字也沒有,也要設立這些部首。《說文》全書共有36個部首沒有統轄字,但是仍然在這些部首字下註明“凡某之屬皆從某”。《說文》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小篆構形體系的完整。既然這些字有音有義,是最小的形體單位,並且絕大多數字曾經作為文字構件進入合體字擔任形旁或聲旁,那么我們就應該承認它們的構字功能。有些沒有統轄字的部首字,即使只作過形聲字的聲旁,如“燕”字,也應該承認它具備潛在的作為漢字形旁的能力。有些人之所以產生沒有統轄字就不應該設立部首的想法,是因為拘守於檢字法的原則,不了解《說文》的構形體系的緣故。
《說文》分部從分不從合,只要形體有別,哪怕意義完全相同,也要分為不同的部首。
這個原則無疑是正確的。但是許慎由於拘於形體,也有分部不當的時候。也有分得過於瑣碎,把小於文字構件的筆畫作為部首的情況。
《說文》分部根據的是意義,所以在部首字下標明“凡某之屬皆從某”,540部基本上堅持了這個原則,可是也有自亂其例的情況。
在《說文》的構形體系中,每個部首都有形、有音、有義,每個文字構件都有形、有音、有義,這標誌著小篆字系已經發展為一個嚴整的、定型了的科學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小篆字系中,有時小於文字構件的筆畫與文字構件形體相同。例如“一”這個形體,作為文字構件,是數字,表示最小的正整數,讀yi1。同樣是“一”這個形體,如果並不表示最小的正整數,那么它就是小於文字構件的筆畫。許慎對這兩種情況基本上區分開了。試看以下說解:對於獨體的象形字,許慎有時也從正字法的角度去解釋字形。這僅僅是就小篆的形體而言,只要我們認真對照一下小篆的字形就不難明白許慎的用意。有的搞文字學的人,竟據此痛斥許慎缺乏起碼的常識。這真有點讓人哭笑不得。我們並不是要迷信《說文》,只是說應該尊重前賢,尊重民族的文化遺產,“使許氏說不可用亦必得其說然後駁正之”(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論國小書》)
近年來對《說文》構形體系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北京師範大學王寧教授主持完成了“《說文》小篆字系研究”,其中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對於“形位”和“形位生成法”的研究。所謂形位,指的是“從漢字字元系統中離析出來並納過的具有能生成新字元和區別造意功能的最小的構形功能客體。”它是組構漢字的基礎構件。
經過初步整理和歸納,他們得出了小篆字系的全部形位,共284個(其中成字形位284個,非字形位62個)
對《說文》小篆字系的研究對於我們學習《說文》的構形系統會有極大的幫助。
綜合運用
《說文》是一部供人查檢的字典,同是也是一部供人通讀的有理論有體系的文字學著作。讀《說文》貴在融會貫通,能夠綜合運用書中有關形、音、義的各種資料。這主要包括:一是綜合利用《說文》正篆下的說解及旁見的說解,二是綜合利用《說文》的被訓釋字及訓釋字,三是充分利用《說文》的重文、引經的異文以及讀者。要做到綜合運用,最基礎的工作是把散見的形、音、義的資料一一系聯起來,互相參見,其中有些資料要集中起來,抄在本篆的書頭上。
拿天干地支字來說,《說文》受漢代風尚的影響,在解釋這些字的專科義時,不免陰陽怪氣。但是在分析合體字涉及到天干地支字的語詞義時,有些見解非常精闢。
旁見的說解很寶貴,有的能夠糾正本篆下說解的謬誤,如上例所述;有的能夠對本篆的說解起補充說明的作用。
《說文》旁見的說解之所以重要:一是因為《說文》有的正篆下解釋有誤,而旁見的說解非常精闢;二是因為《說文》限於體例,在正篆下只能解釋字的本義,而旁見的說解可以解釋字的語源義、引申義、乃至假借義;三是因為造合體字時所用構件的取意不一定是字的本義,所以要另作說解。下面補充一例,說明如何利用《說文》旁見說解明假借。
《說文》在講到字的構意時,有時採取比附的方式,講“某與某同意”。段玉裁說:“凡言某與某同意者,皆謂字形之意有相似者。”(《說文解字·注》“工”字下說解)我們在讀《說文》的時候,要把這些構意相同的一組組字分別系聯起來,做到互見,從比較中深入了解這些字的形義關係。
下面我們講一講如何綜合利用《說文》的被訓釋字及訓釋字。一般來說,讀《說文》是要通過訓釋字來了解被訓釋字,但是有時候訓釋字的詞義不好把握,被訓釋字的詞義卻很明確。這時,我們不妨倒過來,通過被訓釋字來了解訓釋字。
《說文》9353個正篆都是被訓釋字,其中很多字還做過訓釋字。我們如果把這些做訓釋字的資料都抄錄在正篆的書頭上,可以互相參照,有利於我們更準確更全面地了解正篆的意義。
研究《說文》的訓釋字很有意義,因為訓釋字和被訓釋釋字之間的音義關係很密切,這裡所講的通過被訓釋字了解訓釋字以及綜合利用正篆作為被訓釋字和訓釋字的材料,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黃侃先生曾經把《說文》的所有說解字一個一個地研究過,《黃侃論學雜著》中所收的《說文說解常用字》就是當時蒐集的資料。我們應該借用前賢的方法,注重對《說文》訓釋字的研究。從辯證的觀點來看,同一個字可以處於被訓釋字的地位,也可以處於訓釋字的地位,並且在多數情況下是處於訓釋字的地位,那么要全面深刻地了解這個字的意義,當然應該把所有關於這個字的資料都集中運用起來。
《說文》有1163個重文,讀《說文》時千萬不能忽視這批資料。《說文》中有不少省聲、省形字令人懷疑,如果有不省的重文,那么對於字的省聲、省形就無可懷疑了。通過《說文》的重文,可以了解到文字向簡化、形聲化發展的趨勢。由此可知,《說文》中的重文具有歷史性,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通過重文的分化可以了解到文字的孳乳情況及字用的變化。重文中的古文、籀文對於我們識讀甲骨文金文,進而糾正正篆的訛誤的字形及說解極有幫助。
重文中還蘊藏著極為豐富的語音材料。清人錢大昕證明《古無輕唇音》、《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就大量徵引了形聲字的異文。形聲字由於聲旁不同而構成異體字,前人稱之為聲母互換,訓詁家通過聲母互換的事實來溝通音義联系的線索,找出造字時的通借字。
《說文》引經典1083條作為書證,對於這些材料也應該注意綜合運用。一方面要注意對《說文》所引經文的異文進行比較,另一方面要注意對《說文》所引經文與現今經典文本的比較。由此看來,通過《說文》引經的異文可以明通假,這對於渾入了解字義,正確地釋讀古籍大有幫助。
最後我們講一講如何利用《說文》的“讀若”。《說文》用“讀若”的辦法為800多個字注音,其中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讀若”專擬音讀,其他四分之三左右的“讀若”不僅注音,而且連帶解釋了古代典籍上的文字訓詁問題。我們在讀《說文》時應該從四個方面去注意領會“讀若”中蘊含著的文字訓詁材料。所以這一類“讀若”標明了通行的異體字。《說文》的這一類“讀若”標明了通行的後出字。標明了它們之間存在的同源通用的關係。《說文》用“讀若”的辦法標明了典籍中通行的通假字。這種情況在“讀若”中所占比重很大。如果我們能夠熟練地掌握這此通假用法,對於閱讀古籍會有很大的幫助。(參見陸宗達《〈說文〉“讀若”的訓詁意義》,載《訓詁學的研究與套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吸收成果
初讀《說文》,要藉助一本好的注釋。大徐本和小徐本《說文》只有簡單的校語或案語,對於初學者理解原著裨益不大。清人的注釋當首推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當年黃侃先生指導他的弟子學習《說文》就是從點讀段注開始的。點讀完第一遍以後,還要換一套書點讀第二遍(據陸宗達先生面述)。陸宗達先生指導他的研究生學習《說文》,仍然遵循這個傳統,一入學首先用兩個月時間點讀一遍段注,完成之後,再用一個月時間點讀第二遍,兩遍段注通讀之後,才開始進一步學習《說文》。《說文》博大精深,體例繁富,文字簡古。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是指點學習《說文》門徑的最好教材。
讀段注要注意幾個問題。要注意的第一個問題是,看段玉裁如何校訂《說文》傳本的訛誤。段氏非常擅長校書,他一方面以大小徐本《說文》作為底本,參閱眾多古籍,對《說文》進行嚴格的校勘;另一方面又根據《說文》通例,以本書證本書,決定今本的是非。儘管段玉裁的校勘也有過於自信,近於武斷的地方,但是總的來說,訂正了《說文》傳本的許多訛誤,對於我們正確地理解原文有很大幫助。
讀段注要注意的第二個問題是,看段玉裁如何闡發《說文》的體例。古人著書不明言凡例,但是實際上有統一看體例。段氏對於許慎著書的種種條例,寫作的旨意,融會貫通,所以能夠在注釋中發凡起例,詳加闡述。諸如此類有關《說文》體例的說明在段注中總計有五六十處之多,對於我們讀遍《說文》有極大的啟發和指導作用。
讀段注要注意的第三個問題是,看段玉裁如何把《說文》的注釋和群書的訓詁貫串起來,互相闡發。《說文》的訓釋大都是根據經籍訓詁而來的。書中原有例證1083條,段玉裁補充了大量的例證來推求《說文》的根據。段注引用的材料極廣,自先秦到唐宋,幾乎所有的重要的古書都涉獵到了。下面僅舉兩例:這種“以字考經,以經考字”的訓詁方法,能夠使《說文》的注釋和群書的訓詁相得益彰,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說文》,而且有助於提高我們閱讀古漢語的水平。
讀段注要注意的第四個問題是,看段玉裁如何疏通字義。這主要包括以下10方面的內容:一是指出本義,二是指出引申義,三是指出假借義,四是指出古今義的不同,五是辨析同義詞,六是指出俗語詞和方言詞,七是辨析名物詞,八是指出同源詞,九是辨析詞素義,十是指出用字的古今之變。
學習《說文》除了要藉助於段注外,還要注意吸收其他諸家的研究成果。與《說文解字·注》同列為《說文》四大家的,有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王筠的《說文句讀》、《說文釋例》、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的最大優點是材料豐富,經史子集無所不包,我們可以從中翻檢古書中的例證。王筠的《說文句讀》是作為初學者的普及讀物來寫作的,書中刪繁舉要的採用了段玉裁和桂馥兩家的注釋,又加上自己的心得。王筠研究《說文》的主要成果反映在《說文釋例》中。這部書對於了解《說文》體例、研究詞義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嚴格地說,並不是注釋《說文》的著作,其寫作的旨意在於闡述作者關於文字、音韻、訓詁的觀點。所謂“說文”,是疏證丁義,從字形來說,是講象形、指明事、會意、形聲。所謂“通訓”,講的是轉注、假借。朱駿聲把引申作為轉注,把定義改為“轉注者,體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長是也”。把通假作為假借,把定義改為“假借者,本無其意,依聲托字,朋來是也”。所謂“定聲”,指明的是把文字按古韻分類,打亂540部,綜合形聲體系,共得1137個聲符,歸納成為古韻18部。18部的名稱取自《周易》的卦名。這部書打破了《說文》專講本義模式,不僅解說文字的形體,而且通釋字詞的義訓,闡述詞義的系統,確定每個字在古音系統中的聲韻地位,是一部獨具特色的好書。其他有關《說文》的著作還有很多。例如:專門分析《說文》形聲字聲旁系統的著作,有姚文田的《說文聲系》;專門研究《說文》收字的著作,有鄭珍的《說文佚字》;專門研究《說文》各種版本差異的著作,有沈濤的《說文古本考》,等等。集《說文》注釋及研究成果之大成的,是近人丁福保於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編纂的《說文解字詁林》及《詁林補遺》。《說文》的最新注本,是張舜徽先生於1981年出版的《說文解字約注》。這部書綜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運用了不少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資料,對《說文》學有新的開拓。
最後我們講一講學習《說文》應該怎樣吸收古文字學的成果。《說文》學與古文字學的關係非常密切,二者互相補充,相得益彰。古文字學需要藉助《說文》來考釋出土古文字。學習研究《說文》的人需要藉助古文字學的研究成果來印正和糾正《說文》。陸宗達先生在指導他的研究生學習《說文》的時候非常重視引導學生自學古文字。他讓學生多準備幾部大徐本《說文》,其中有一部專門用來比較甲骨文、金文和小篆的字形。研究生們根據《古文字類編》(高明編,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徐中舒主編,四川辭書出版社1981年出版),及《甲骨文編》、《金文編》等古文字工具書,把已有定論的甲骨文、金文摹寫在相應的小篆的書頭或行間。如果對甲骨文金文的構形有疑問,再去查閱《甲骨文字集釋》(李孝定編述))和《金文詁林補》(周法高主編)。這樣做,既藉助《說文》學習了甲骨文金文,又藉助甲骨文金文促進了對《說文》的深入了解,可以說,是一箭雙鵰。下面我們著重舉例說明學習古文字學對於學習《說文》的幫助。
由於字形訛變或思想認識的局限,《說文》對相當一部分字的字形分析有錯誤,比如說省聲字,段玉裁曾經指出:“許書言省聲多有可疑者,取一偏旁,不載全字,指為某字之省。”(《說文解字注》“哭”字下說解)
利用甲骨文金文糾正《說文》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還可以印證《說文》,加深我們對小篆字系的了解。
用出土的古文字材料糾正、印正《說文》的字形只是利用古文字材料的一個方面。另外還可以用卜辭、銘文以及其他出土的古文字材料為《說文》補充例證。
近幾十年來,古文字學有了長足的進步,地下出土文物屢屢發現,往往為古文字學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考釋對象,這一切對於《說文》學的發展都具有直接的或間接的推動作用。所以我們學習《說文》時,要把眼光放得更開闊些,既不鄙薄《說文》,又不固守《說文》,要勇於並善於吸取古文字學的成果,來豐富和發展《說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