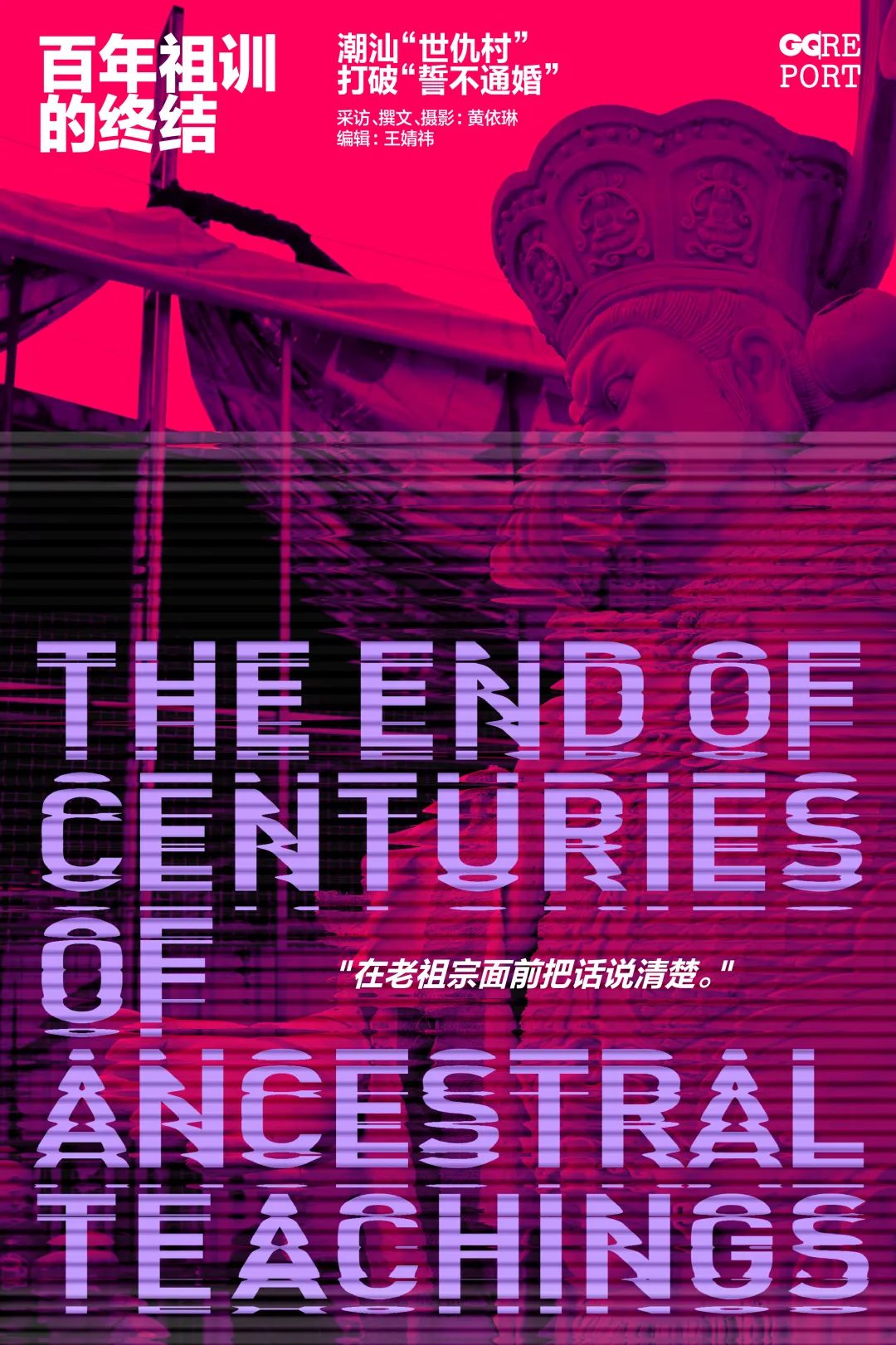
這是一個很久遠的仇,活著的人已經道不清細節。這又是一個難以擺脫的仇,就連第八代的子孫還在被祖先的恩怨所擾。
故事發生在廣東揭陽,潮汕地區一個宗族文化氛圍相當濃厚的地方。當地幾個村莊恪守著“誓不通婚”的祖訓,村民們深信,一旦違背,就會引來災禍。一個多世紀以來,舊恨疊加新仇,世仇像一道咒語,籠罩著村莊,只有寥寥數人敢頂著流言蜚語,打破禁忌。
近年來,冰封的河開始流動,一些“世仇村”陸續和解。我們記錄其中的一場,觀察現代化的觸角,如何潛移默化地作用於古老的宗族村莊,身處綿延的仇怨和變化的時代中的人們,又如何重新選擇他們的生活。
懇請祖先應允
上午9點多,供奉54尊祖先牌位的神龕被緩緩打開。
一位年輕禮生鞠著身子,恭敬地請出金漆木雕的祖先牌位,另有兩位禮生小心接住,擺在紅木供台上。
“凡物具備,祭儀如規”,主祭逐字念完,繞到香案前,先下左膝,再接右膝,一拜,緩慢起身,再拜。他穿著暗紅色傳統服裝,依次捧起茶、酒、飯等祭品,供奉到祖宗面前。
2023年10月1日,廣東揭陽榕江邊一座古村內正在舉辦慶典活動。地點在揭陽市仙橋街道槎橋村最大的祠堂楊氏宗祠,門前一對石獅石鼓,跨過三進廳,穿過天井,直達正堂。

楊氏宗祠
在主祭身後,齊齊跪著50多位輩分及年齡較長的村民。雖已到10月,潮汕天氣還如盛夏,幾位年輕人不停從紙箱裡掏出礦泉水,挨個遞給長輩。
司儀念著一張粉色的紙,內容大意是,百年前槎橋村與鄰鄉有矛盾,祖宗立下不能通婚的訓示。如今應當破解誓約,懇請祖先應允。
紙上提到的鄰鄉,指的是周邊美東、美西、下六村,此時這三個村中祠堂也在舉辦同樣的儀式。上百年來,這四個“世仇村”的年輕人從小就被叮囑一道祖訓——誓不通婚。
即便在宗族氣氛最為濃厚的潮汕地區,“世仇”“誓不通婚”這樣的字眼聽起來也有些遙遠。代代相傳,最初到底是什麼樣的仇,只有槎橋村里年紀最大的老人楊祈對還了解幾分。
被詢問及此, 95歲的楊祈對拄著拐杖,一點一點挪到堂屋的觀音菩薩像邊,捧起一個紅木鑲邊的玻璃畫框,再慢慢挪回木椅坐下,鄭重地看了好一會兒。
畫中端坐一對夫妻,穿著清代的衣服,因年代久遠,早已面目難辨。玻璃上蒙了一層污垢,左下角裂開了一道半圓的縫,畫中央貼著歪歪扭扭的黃色膠帶。楊祈對用袖口擦了擦,泛黃的指甲指向那位女人,“自殺了”。
她姓黃,是原高美村(註:現已經被分為美西村、美東村)人。她的丈夫姓楊,是槎橋村的一名鄉紳。楊姓建村早,是附近村寨中人丁最興旺的一支。
約清朝中期,高美村的黃老虎和槎橋村的楊滂劍打了起來。打架的地方在兩村之間的小橋上。三條石板搭成,寬不過半米,一次只能過一人。兩人過橋時發生口角,互不相讓。黃老虎耍無賴,把楊滂劍拉下了水。
在宗族社會,哪怕極其微小的個人矛盾,也會迅速上升為家族衝突。有錯在先的高美村民反倒認為,他們黃家“小姓”被“大姓”楊家欺負了,是奇恥大辱。他們來到兩村接壤的番薯地,殺害了18個正在勞作的槎橋村民。
槎橋村楊家因為娶了高美村黃家的媳婦,而成為村人的眼中釘。一日,黃氏的弟弟從高美村來槎橋村做客,被憤怒的村民綁在樹下,說是要砍了人頭,交換被扣押的宗親屍體。
黃氏求情無果,悲憤自殺。自此,兩個村莊結下深仇,族長在各自祖先牌位前發誓,後代永不通婚。農耕時代的村莊,誓不通婚幾乎等同於絕交。從此兩村交界處的田地無人敢種,十八年來日漸荒廢,鳥嘴無意間掉下的番石榴籽,長成大樹。
“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整整一代人活在仇恨里吶。”楊祈對念叨著,他是畫像中夫妻的第五代孫。

楊祈對
仇恨就這樣代代傳下來,尤其在潮汕揭陽這樣宗族文化保存最為完整、歷史淵源最為深遠的地方,上百年來不曾被忘卻。在這裡,村民們敬畏祖先,依賴宗族,槎橋村的一位村民告訴我,一年中,村里大大小小和祭祖拜神有關的事近70件。他們從懂事開始,就會被帶到祠堂里叩拜。即便經歷過上世紀50年代的土改、公社化,祠堂大多被沒收改為他用,但宗族文化從未從當地人的生活中消失。1985年,槎橋楊氏宗祠重修,族人專門托人從外地運來上等杉木。
直到現在,槎橋村中最氣派的建築,仍是楊氏宗祠。祠堂在村中池塘的正對面,是全村風水最佳的地方,兩旁是村廟、祖祠、公祠。一入夜,這裡彩燈高懸,如白晝般明亮。晚上11點,有婦女騎著腳踏車,掏出紅色塑膠袋里的紙錢和香火,挨個拜拜。這是幾乎每個村民從小開始養成的習慣,一個村民說,即使有時出去玩忘記了,還會記得繞路回去上個香。
除了血仇,數百年來,其他的仇恨也在這片土地上盤根錯節。槎橋村楊姓來得早,占據了最好的風水。隨著周圍不斷有新的姓氏加入,人地關係變得緊張,資源爭奪也應運而生。在清朝中後期,周邊村莊開始與槎橋村結仇,除了仇家高美村,還有下六村,各村不同姓氏之間也有齟齬,矛盾彎彎轉轉,連成一片,牽扯14個自然村。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分析,潮汕地區多為山地丘陵,生態穩定、定居時間長,血緣和地緣關係高度重合,導致村莊的社會內聚力比較強。隨著人口增加,因為資源搶奪面臨家族之爭的事時有發生。在某一特定的時間節點競爭到白熱化時,幾個家族便會絕交。
側廳的鑼鼓響起,三塊扎著繡球的紅木牌匾被抬進正廳,匾上刻著金字“睦鄰友好”,三塊牌匾的贈予者分別是西洋郭氏、高美黃氏、泰洞邱氏。看見自家村子送來的牌匾擺在正廳,來自這些村莊的老人們上前合影。
“解除舊約,締結婚姻。祈祖笑允,四姓俱興。”主祭剛剛念完了祝文的最後一段,隨主祭跪拜的老人們起身,互相贈送伴手禮,八個橘子,還有四包旺旺糖,寓意“大吉大利”。
謄寫祝文的粉紅紙被折成三折,在香火上點燃,繞香爐一圈,菸灰一溜煙散開。有人說,那是天地神明聽見了子孫的願望。
失敗的嘗試
儀式的最後,出現了一個小插曲。
伴手禮贈送完畢後,槎橋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又從袋子裡掏出兩隻橘子。這個額外的贈禮讓其他三個村的老人有點慌,因為沒有準備回禮。禮尚往來,有來有往,在潮汕,這很重要。
求助電話打到楊繼波那裡,他是仙橋街道的文化站站長,也是這次活動的策劃者之一。此時,他正在祠堂外面控場。國慶放假,又至晌午時分,許多水果攤關門,需要回禮的老人有30位,要買60個橘子,楊繼波和其他幾個村幹部四處求人。這是禮節,不能失禮。剛剛把矛盾平息,他不想又生間隙。
楊繼波今年58,體格清瘦,眼神機敏,煙不離手,此前的30餘年,他在仙橋街道的很多部門都當過幹部,其中有7年在槎橋村當村支書。楊繼波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母親是民國時期村里第一批女學生,他本人也進修過勞動經濟學。作為本地人,他同樣在宗族文化的浸淫下長大,但在他的觀念里,宗族文化還需要現代秩序的引導。
早在9年前,楊繼波剛從街道下來槎橋村當村支書,就動過化解“世仇”的念頭。那是2014年,附近的揭西縣搞了一次宗族和解活動,促成了當地楊、林、侯三姓和解,儀式上來了2萬多人。楊繼波看見這一幕,心裡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他之所以生出這種想法,責任之外,還有人情。楊繼波當時有兩個朋友的孩子,都處了“世仇村”的對象,正苦於打破“禁忌”。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了這位剛上任的村支書身上。
剛開始,楊繼波很有信心,在過去工作的30多年裡,他與“世仇村”之一美東村的老書記黃建喜成了密友。他和夫人常與黃書記夫婦一起郊遊喝茶。關於和解,他們也想到了一處去。
然而,第一次嘗試就出師不利,最大的問題,就出在“老人頭”那裡。
“老人頭”是當地宗祠理事會的會長,對應著傳統宗族社會裡的族長,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長輩。在潮汕地區,修祠堂、修族譜、舉辦祭祖活動,哪件都離不開“老人頭”的張羅。“世仇”發生在宗族之間,要解決繞不開宗祠理事會,自然也要先取得“老人頭”的同意。

宗祠修建募捐芳名錄
但在楊繼波開始推動和解後的4年裡,接連幾任“老人頭”身體欠佳,相繼去世。每次事情剛有點眉目,就打回原地。2018年一位退休教師當上了“老人頭”,但他來自人口較少的自然村,說話“分量”不夠。
2019年,槎橋村現任宗祠理事會會長楊東河上任。一次會上,楊繼波重提和解,被楊東河一句話懟了回來。楊東河說,家裡的事都搞不明白,還怎么搞跟外面的事?
“家裡的事”,說的是槎橋村內部的“仇”。斗門和東光,是槎橋村下轄的兩個自然村。雖然都姓楊,但屬於不同支系,是不同房的“兄弟”。多年以前,斗門村的祭祖大事“迎老爺”經過東光村時,被一位東光村民阻攔。斗門村以賭氣的方式反制,不讓東光村的送殯隊伍經過斗門村。自此,兩頭辦事都要繞5公里以上的路。
楊繼波是斗門村人,楊東河是東光村人,正處在“世仇”微妙的對角線上。話說不到一起,楊繼波覺得堵得慌。
因為他知道,舊怨不解,大大小小的新仇就會不斷疊加。在村里採訪期間,我了解到1965年發生在“世仇村”東洋村(原槎橋村下轄自然村)和新泰村(下六村下轄自然村)之間的一場械鬥,就是舊恨上的傷口上撒的新鹽,不斷觸痛村民關於仇恨的記憶。
當年,同樣在10月,下午2點不到,熱浪在南方的田埂上翻滾。100多個青壯年站在田裡,手裡拿著傢伙,除了竹竿,還有鐮刀、鋤頭和棍棒。
隔著一條不到半米的小溪,對面的田裡也站著100多個怒氣沖沖的漢子。起因很簡單,一個村的鴨子游到了對面的“世仇村”吃稻穀。一言不合,人越聚越多,一位村民被刺傷後倒地不起,斷了氣。槎橋村有個22歲的楊姓年輕人被判了5年,因為械鬥工具是他買的。
如今,楊姓青年成了楊伯,他已經79歲,出獄後去過惠州搬磚頭、拉水泥,在汕頭賣水果,打了一輩子光棍。他有心臟病,現在歲數大了,大部分時間臥病在床。家中前廳的牌匾上寫著“光宗耀祖”四個大字,“楊伯年輕時也是有文化的”,同去的村幹部沒把話說下去。
隨著時代的發展,從前這些“田頭水尾”的恩怨,變成了屬於新時代的矛盾。1991年,揭陽建市,一些村莊變成了城市的一部分。一位在上世紀90年代上任的村書記說,他那時處理的大部分矛盾因分房和宅基地引起。在新時代的爭奪中,大到宗族之間,小到房頭之間,對外的利益紛爭不斷,人們進一步向宗族內部尋求確認。
2003年,建設槎橋路徵用了美東村的田地,兩村產生了口角,揚言要打一架;一處工業區征地,和宗族矛盾交織在一起,前後持續七年,直至帶頭“鬧事”的人被關進監獄……
如今的矛盾雖然不會再引發大規模的械鬥,但新仇舊恨,千頭萬緒,何時能了?楊繼波希望看到斬斷的那一天。
等待轉機
美西村的黃鳳霞也期待那一天,她已經在痛苦中等待了10多年。
2007年,黃鳳霞17歲,在鞋廠打工,認識了槎橋村的同事楊彬華,彼此間有說不完的話。兩人小心地互訴好感,又不敢輕易說“愛”。“世仇”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們說不明白。每逢過節,楊彬華都硬著頭皮去她家拜訪,同黃父喝茶。他們都清楚,黃父沒有把這個來自“世仇村”的小伙拒之門外,只是出於禮貌。
宗族觀念里注重禮教,敬重長輩。在黃鳳霞看來,只有得到父母真心的祝福,她才有底氣對抗流言蜚語。僵持的日子裡,他們從未與父母發生正面衝突,卻也暗自較勁,拒絕見家族介紹的相親對象。
父母終於同意的那一天,離兩人相識已過了六年。正式戀愛一年後,兩個“世仇村”的年輕人結了婚。頂著違背祖訓的壓力,他們的喜事沒怎么操辦,只在男方家裡請長輩湊了兩桌,簡單吃了頓飯。和許多當地的年輕人一樣,婚後,這對小夫妻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黃鳳霞至今保留著婚後不久買的粉色十字繡底面時鐘,上面有蝴蝶和閃閃的粉色玫瑰。上面“真愛永恆”四個字,襯著她當時的心情——夢想成真。在深圳的頭幾年,夫妻倆過著甜蜜的生活,一度忘記了祖訓。

黃鳳霞家中的“真愛永恆”時鐘
再次想起的時候,是老家的公公得了重病。二人辭掉了深圳的工作,回家照顧。公公的病把全家的錢差不多都散盡了,一年後丈夫也病倒,進了ICU。到處籌措來10萬塊錢,還是沒能改變結局。在他們結婚的第7個年頭,楊彬華走了。
在沒有秘密的熟人社會,黃鳳霞開始被周圍關於“詛咒”的流言折磨。“誰讓她不聽話”“害死了家公(公公),又害死了老公”“都是她的錯”。丈夫去世後,流言更加兇猛地刺向黃鳳霞,她自責又害怕。
住在村里,每次去祠堂,黃鳳霞總是像犯了錯的人一樣,點上香火就走。她不喜歡被指指點點,只有“誓不通婚”的祖訓被破除,壓在她頭上的這座大山才能被搬開。
終於,又一次契機到來,去年7月,上級巡查組下鄉調查農村問題,提出和解“世仇”問題。2023年是廣東省“百千萬工程”的第二年,省內的“百縣千鎮萬村”謀求發展,而對於潮汕地區的村莊來說,對於像黃鳳霞這樣的村民來說,“世仇”是必須搬開的石頭。
此時,楊繼波已經卸任村支書,又回到了仙橋街道,在人大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工作。時隔幾年,這次重啟調解工作,楊繼波感覺到,事情好像容易了些。在調解會上,許多老人不再像過去那么“嘴硬”,“99%的老人早就盼著這一天了。”
實際上,在過去的這些年裡,很多事都在悄然發生著變化。就拿婚戀來說,雖然頂著“誓不通婚”的祖訓,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有了自己的主意。
槎橋村的楊選珊就嫁給了“世仇村”的丈夫。15歲時楊選珊外出打工,一去11年,愛上了吃辣,潮汕話也說不溜了。她周圍的朋友來自海南、廣西、江西、四川,沒有同鄉宗親。她認定自己將來也會嫁到外地,但有一年回家,她和少女時的夥伴重逢,相愛了。為了避嫌,她和丈夫只領了證,沒辦儀式。她總說,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
“你能保證你的後代不會談那邊的對象嗎?”調解會上,幹部們拋出這句話,老人們往往沉默,他們心裡也清楚,時代變了,對著幹沒什麼好處。
變了的不僅是婚戀觀念。改革開放後,幾個“世仇村”即便仍不通婚,但陸續開始有了經濟往來。
1980年代中後期,鋼材、塑膠、五金,開始成為揭陽的三大支柱產業。在美西村書記黃潮明的記憶里,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高美村(註:雖然高美村已不存在,但當地人仍習慣性將美東村、美西村合稱“高美村”)和槎橋村有了頻繁的商業往來。以前他做過五金生意,承包景點,結識不少“世仇村”的商業夥伴。合作一直延續到現在,他的兩個兒子一個做電商,一個做塑膠鞋生意,原料大多來自槎橋村。祖訓也擋不住金錢的流動。

揭陽騎樓老街一家老牌五金店
楊繼波勸過一位“不開竅”的村支書,“睦鄰友好是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腔調板正,但道理是實實在在的,大家整天搞世仇,哪有精力搞發展呢?
這句話西洋村(美西村下轄的自然村)的村支書郭奕輝深有體會。這些年他心裡一直有個疙瘩。美西、美東、槎橋三個村之間,有一條約2公里長的河道,名叫外溪渠。這條河常年堵塞,郭奕輝的手機里存著一個視頻:一個村民走過漲水的村道,污水漫過他的小腿肚子,水面上飄著可樂瓶子、塑膠泡沫、缺了腿的木凳子……
“這還是不嚴重的時候”,原來郭奕輝家住在一樓,一下大雨,河道垃圾堵塞,造成內澇,水漫到村子裡,把他家樓下淹掉半層。
很難想像,以前,這條河寬得可以賽龍舟,清得可以舀水直接喝。但隨著人們在河邊建廠房、修道路,河道一天天變窄。工業污水和建築垃圾,讓河水再也不能作為生活用水了。由於無人清淤,水草長得野蠻,仿佛叢林般掩蓋了河道。
7年前,郭奕輝想過清理河道,鄉賢們湊了一千萬,給西洋村建了一座生態公園,按照城市的標準,修得漂亮大氣。美中不足的是裡頭有一灘死水,又髒又臭。
河道是幾個村公用的,要想徹底清理,需要“世仇村”槎橋下轄的斗門村出面,管理私搭工棚的工廠,還要允許挖掘機進來清淤。
“他們沒說拒絕,但很敷衍”,郭奕輝很無奈。斗門村人不住河邊,河道淤堵對生活影響小。既然兩村有“世仇”,村幹部便沒什麼動力得罪村裡的工廠,更不積極。在郭奕輝看來,不解的“世仇”,就像河道里的這灘死水,到了必須要清的時候了。
磕下“老人頭”
最新這次調解開始後,第一個贊成和解的,就是郭奕輝所在的西洋村。因為人口少,又有迫在眉睫的需求,村里一個“反對派”也沒有。
接下來是槎橋村和高美村。槎橋有1.1萬人口,下轄七個自然村,各村之間內部有矛盾。已經分成美東村、美西村的高美村,人口加起來也過萬,雖然都姓黃,彼此之間也不那么和諧。
要把這些彎彎繞繞、深入到毛細血管的恩怨釐清、抹除,在依賴宗族文化的鄉村,解鈴還須系鈴人,即便有了上級部門的支持,也還是要藉助傳統宗族力量。哪裡跌倒就在哪裡爬起來,楊繼波打算繼續死磕“老人頭”。
究竟為什麼“老人頭”這么重要?我打算舉兩個例子說明。
第一個例子是,去年12月,槎橋村獲批廣東省第八批古村落之一,大部分花銷是“老人頭”找來的。他們有號召力,能“搞錢”,村里張羅任何大事離不開他們。而古村落稱號之所以能獲批,老人們操持的古村廟、楊氏宗祠和每年的傳統宗族活動,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一位村支書向我略帶炫耀地提起,他平時如何努力搞好與“老人頭”的關係——一起喝茶吃飯,帶他們去參加“見世面”的活動,原則範圍內有求必應。關係搞好的話,村支書能省下不少力氣。如果把和解比作一齣戲,政府是導演,民眾是演員,“老人頭”才是主角。
第二個例子來自我在槎橋村結識的一個年輕人楊彬如。他是傳統習俗的忠實擁躉,熟讀楊氏族譜,只要說出個姓名,他能迅速定位出在族譜中的位置。跟著他,我進槎橋村任何一家的門,都不會被拒絕。與宗親初次見面,他會以“我是誰誰的什麼人”開啟話匣子,有了這層遠親的關係,信任會悄然建立。至於有“世仇”的美東村和美西村,他也有辦法,我姓黃,和這兩村人同姓,他認為這是優勢,只要報上本姓,都是江夏黃氏的宗親,如果能背上幾句認祖詩“內外八字”,不但能聊得愉快,還能蹭頓飯。
人、宗族,織成了一張網,誰也離不開誰。即便是嫁了“世仇村”丈夫的楊選珊,回到村里也免不了要去祠堂燒柱香,即便她總是分不清“這個神”和“那個神”的區別。
因此,對於化解“世仇”這種大事,是絕對繞不開傳統宗族力量的話事人“老人頭”的。
好在,剩下那1%“老頑固”,似乎也沒那么頑固了,雖然最初,他們不是藉故缺席開會,就是默不作聲,不說支持,也說不反對。就拿槎橋村宗祠理事會會長楊東河來說,剛聽到這次“和解”的訊息,他就在宗祠聯繫群里反對,又翻出些陳芝麻爛穀子的舊賬。
但當楊繼波請了楊少育出山,楊東河這塊硬石頭也沒費多大力氣就搬開了。楊少育是村里鄉賢、當地公益組織的會長,還是榕城區人大代表。他熱心,有影響力,又肩負責任,最關鍵的是楊東河是他的叔父。
楊繼波找他合計,請他勸楊東河,只有解決了外族和解的大事,才有餘地化解同村兄弟之間的矛盾。如果楊東河還猶豫,就給一點壓力——如果卡在你這裡,村民會怪罪你們家族的。
楊少育依言去做工作,楊東河就這樣被說服了,兩人碰頭的當晚,楊少育就給楊繼波發微信,勸成了。或許,時代的洪流襲來時,即便最頑固的人也不得不抬腳讓路。
至於其他底下村寨難搞的“老人頭”,他們也採取類似策略,聊得差不多了,就組個飯局,把兩邊的“老人頭”拉到一起,陪幾杯酒下肚,空氣開始流動起來。

三位宗祠理事會成員聚在槎橋仙槎古廟門口
或許,在一些老人心裡,他們無法立即徹底拋棄前嫌,只是放在一邊,期冀維持著表面的和平。在仙橋街道的幾個村莊走訪時,我每天都會路過大大小小的祠堂。同一個祖先下有不同分支,正如槎橋村下有七個自然村,每個自然村都有宗祠理事會和“老人頭”。大宗祠下面還有祖祠、公祠,代表著更細分的家族脈絡。這些盤根錯節、細枝末節的前塵往事,並不會因為一餐飯、幾杯酒就徹底抹去。他們的沉默或許迫於某種難以言表的壓力,從前宗族社會所賦予的權力,在新的社會秩序下已然失勢,“點頭”也是“低頭”,是宗族適應現代社會不得不完成的過渡。
8月下旬,離提出和解過去了一個半月,14個村寨的“老人頭”坐在了一起。9月1日,一封由楊繼波撰寫的“倡議書”發到了各村各戶。但這還不夠,“解鈴還須系鈴人”,要解開老祖宗的“詛咒”,還需要最後一道“解咒語”——辦一個莊嚴的儀式,在老祖宗面前把話說清楚。
為了平衡各個宗族不同的祭祀方式和吉日良辰,各村統一了叩首、跪拜、鞠躬的次數,把日子選在了10月1日“舉國同慶”的這天。
儀式舉辦的地點在各村宗祠,但美西村的黃氏宗祠曾被改成學校,有近40年沒有拜過祖先了。學校停辦後,裡面空空如也,沒有香爐、靈牌、神龕,飛檐上的彩漆已褪色,進門左手邊的半邊牆也在颱風中倒塌了。
村委找到禮儀公司,利用視覺錯覺,按照完好一側牆的樣子,列印了一張逼真的裸眼3D畫布,貼在塌掉的半邊牆上,用金箔紙包在堂柱上,再把祭拜用具置辦齊全。
還有一點不完美,宗祠缺祭拜的祖先。黃氏宗祠是四個村子的黃姓宗親共有的,美東村和美西村雖是同宗,但拜的是不一樣的祖先。要講和,舉辦儀式,就要在族譜上又往上追,把江夏黃氏的老祖宗抬出來。
活動開始前一個月,美西村支書黃潮明去了一趟80公里以外的潮州饒平,那裡供奉著江夏黃氏的老祖宗。他用紅紙包著那裡的香灰,請回村里祠堂的香爐里。根據古老的說法,香灰可以傳達願望並得到回應。
2023年10月1日這天,40年來,黃氏宗祠第一次在破敗中重生。
鑼鼓聲中,儀式完成。“沒想到還能活著看到這一天”,一位老人對“世仇村”的另一個老人說,他的兒女早已完婚,如今孫輩的婚事可以沒有“禁忌”了。說笑間,越來越多的老人湊了過來,交換彼此知道的未婚男女信息。
尾聲
喜訊很快傳來。
9月中旬,槎橋村和美西村的一對新人舉辦了訂婚宴。新娘挽著新郎的胳膊,笑得甜美,五彩的禮花撒在他們身上。兩人相戀三年,在外地打工,如果沒有和解,雙方父母本打算低調辦喜事,連男方的舅舅都沒敢告訴。看到倡議書後,他們立即通知了所有親友。
終於與斗門村和解後,西洋村支書郭奕輝心裡的疙瘩解開了。兩個月來,斗門村已經說服工廠拆掉了工棚,西洋村的鄉賢們湊了一百萬,淤泥和雜草裝了200車。在西洋村一側,調節水閥幾近完工。
“現在是一家人了”,鄉賢郭奕群是去年剛上任的的西洋村郭氏宗祠理事長,平時做鋼材生意,這次清理河道工程捐了4萬元。這是30年來外溪渠最乾淨的一次。

和解這天,黃鳳霞也站在人群里。看到“睦鄰友好”牌匾被送進祠堂,她的眼淚止不住地往下落。如今她知道,自己可以堂堂正正去祠堂燒香,再也不用怕了。
(應受訪者要求,黃鳳霞、楊彬華、楊彬如為化名)
採訪、撰文、攝影:黃依琳編輯:王婧禕運營編輯:溫溫
通婚